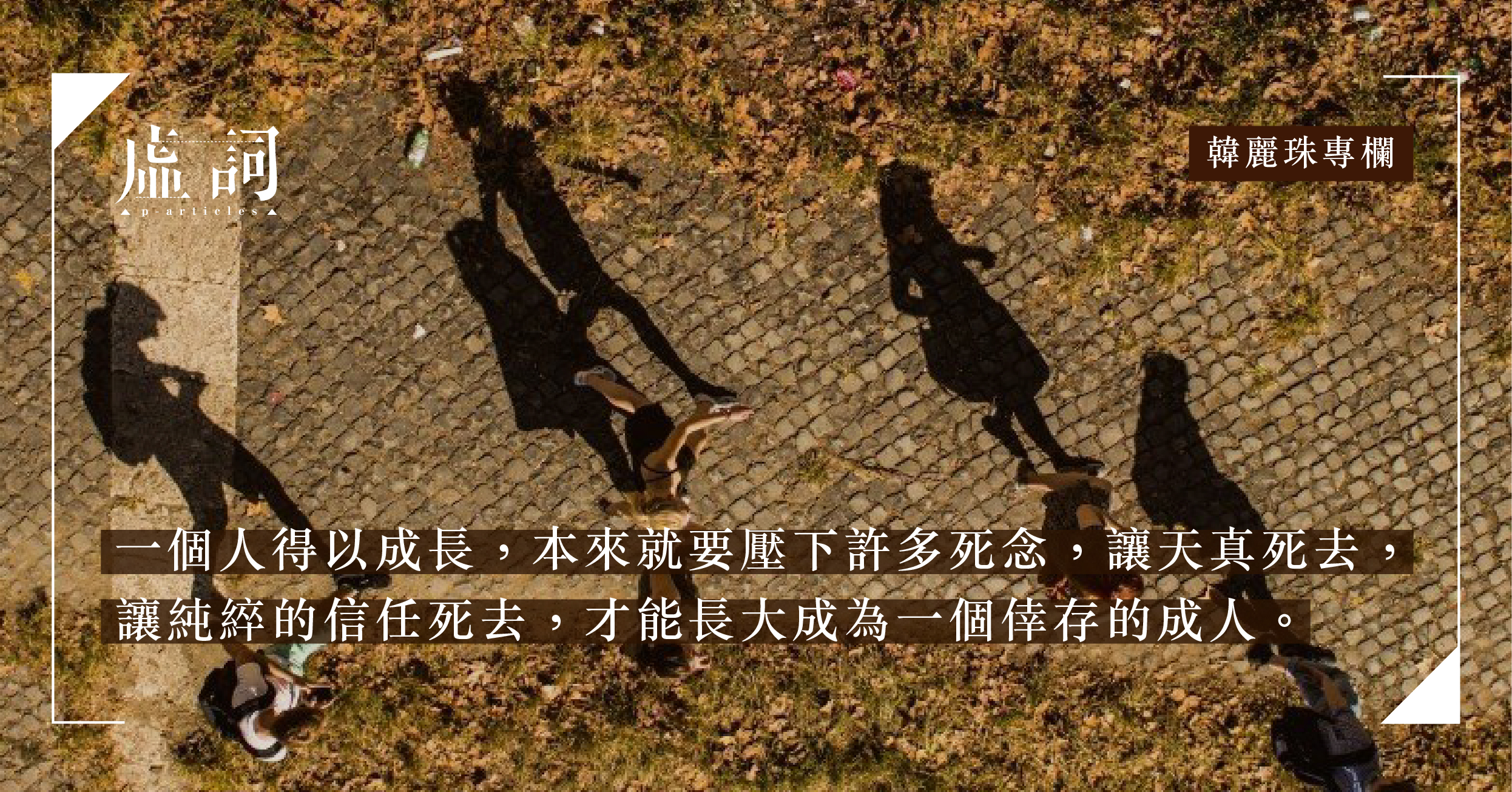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與獸共生
讀了一則關於中學裡的欺凌事件的新聞報導後,我點開另一個視窗,看了日劇《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第一集,那一集快要結束之時,新垣結衣飾演的深海晶加班至深宵後,被客戶性騷擾和上司催迫踐踏之後,在地鐵月台上呆呆看著一輛剛駛進站的列車。她想跳下路軌。
學校從來都不是社會的縮影,而是社會的一部份,以教育之名,分明的階層,清晰的規訓,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無法逾越的位置,同時也無處可逃。
青春期的人身上都有一股獸的羶氣,他們還沒有學會加以掩飾,而成人則已慣熟地披上人皮,遮蔽獸的面目。在那裡,每一個受害者也可能是加害者,而旁觀者則同時是施虐者和受虐者,沒有任何人能獨善其身。成年後,當我和親近的朋友或伴侶談及求學時期的生活,他們所吐出的字詞、片段和事件,即使無法說得上是美好,即使是渾沌、蒼白或無聊,聽起來也是一個正常的軌道,重複行進。我卻無法找到任何合適的名詞或形容詞,去指出那種接近失序的狀況,以致我常常懷疑,那是只有我才經歷過的事情。別人必定也有別人無法宣之於口的苦難,而每個人在自身的地獄之中都是孤獨的。
小四那一年,班主任是個皮膚白晳,戴著圓形眼鏡,身形面目皆圓潤可親的女人。在她選擇了我作為欺侮對象之前,或許有那麼一刻,我曾經把對母親的依戀投射在她身上。直至她時常無故在早會排隊時要我在一旁罰站,在家長日對我的母親投訴我在課上常常發呆,聯同班上幾個同學對我進行排擠。或許並不是那些言行,而是空氣中那種濃稠的恨意和惡意,把我推進了成長的分界線。孩童和成人的分水嶺就是,渡過一條河,在那裡,沒有任何一個人相信我(包括母親),而我再也無法信任身旁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一個人得以成長,本來就要壓下許多死念,讓天真死去,讓純綷的信任死去,才能長大成為一個倖存的成人。
在學校裡,學生可能會欺凌老師,學生可能會欺凌同學,老師可能會欺凌學生,校長可能會欺凌老師,任何人都可能會欺凌另一個處於更弱勢的人。不是因為他們身處的環境,不是因為他們的身份,不是因為他們是他們,而是他們身上的獸。認清那人身上暴力的因子,而不要錯認是那個人所犯的罪。
老師在校園的建築物跳下來,學生從家裡的窗子跳下來。暴力卻非在今天才出現,獸的種子早在多年以前就種在人的心裡,只是現在紛紛茁壯成巨大的陰影,終於,無法忍受的人愈來愈多。如果制度容許暴力日益壯大,那是因為監管制度的人,背後的道德和文明,以及存在其中的一切最基本的善意正在日漸瓦解。
讀著關於學校的新聞報道,和《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的職場暴力,我好像在重溫一些早已發生過的回憶,讓藏在身體暗處的痛楚再次發作一遍。
我記得身體內的獸,青春期開始之後,牠就常常出現,而且總是在我非常虛弱時誘惑我:「真的不考慮殺掉你自己嗎?唯有這樣,你才能強起來。」那時候,獸看起來關切而充滿同情。
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經能確定,殺掉自己也不免是一種暴力,而死亡並非真正的終結,正如河流的水會蒸發成為雲,雲下雨又回復水的形態,獸會希望隨著我了結自己的生命而把暴力帶進另一種生命形式,但那卻非我的意願。
當獸又在我非常傷心的時候,走到我身旁虎視眈眈,我撫摸牠的額頭,但牠並不是貓,牠或許想要撕碎我,然而在牠這樣做之前,我們仍然可以安然共處的時候,世界突然非常平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