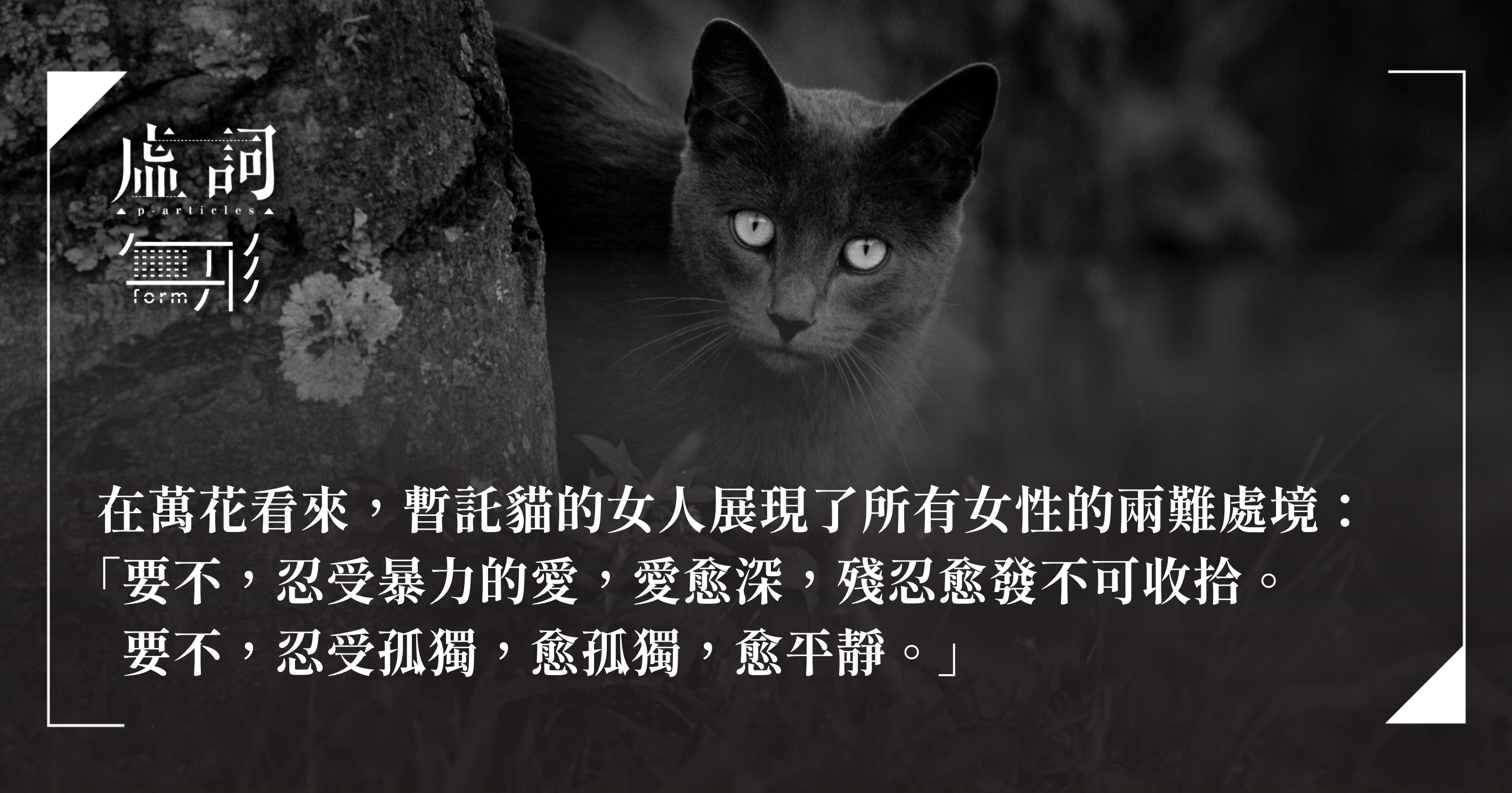【無形・那陣時不知道的滋味】吃黑
萬花被那片未知的黑吸引前去,但,黑色長在貓身上,是鐵一般無法改變的事實。
訥言從來沒有想過她會一口答應把貓領養。那天下班,他鼓起勇氣在辦公室向她提出請求,只是因為他的手機聯絡簿裡,幾乎每一個有可能對貓有興趣的人,都被他要求過養貓,或在他手上領養了貓。他只能接觸那些認識但不相熟,看來和善的人。
那天黃昏,他們在暫託人的房子門前脫鞋,走進屋內,觸目所及,先是掛在牆上的碧綠、翠綠、墨綠和灰青色盆栽,接著就是地上狼藉的玫瑰花、蘭花和彩色仙人掌。
屋子角落,有一個籠子,籠內有一雙眼睛,灼灼地注視萬花。她好像聽到那雙眼睛在說:「現在才來!我餓壞了。」
她忍不住一直看著牠,忘記了下班後還未進食的飢餓,就像在許多情緒不穩的日子,一直看著漆黑的夜空尋找月亮的蹤影。
貓的黑身,長滿了夜。她走近細看,發現貓毛很長,只是身上佈滿掉毛後灰色的圓塊,像落難的貴族。她立即明白牠的處境。牠對她也是暸如指掌,於是舔了舔掌心,目不轉晴地看著她,像盯著一頭肥美的獵物。
暫託的女人穿著寬鬆裙子,走到籠子附近,就像急於為自己辯護的嫌疑犯那樣:「我並不是故意把貓關起來。實在,如果環境許可,我希望可以一直照顧牠至終老。可是,貓有一個癖好。」她遲疑著,就像為了避免被貓聽到那樣,壓低聲線湊近萬花的耳畔說:「她會啃咬花朵和葉片,直至所有植物都佈滿被牠咬過的齒洞,牠才心滿意足地睡去。不,其實不止是植物,還有所有花葉形狀的東西,不管是蠟燭、陶瓷、杯盤,甚至印有花卉圖案的裙子、襯衣和圍裙,牠都要用牙齒在那裡留下記號。」暫托的女人經營網上花店,她的家就是工作室。根據女人的說法,貓會吃光她的貨物。女人說這句話的時候,萬花聽成了:「貓終究會吃光我。」那麼,貓也會一點一點地把我吃掉嗎?萬花忍不住這樣想。她並沒有被誰吃光過,也沒有慾望去吃任何活物,畢竟她已茹素多年,可是眼前的這一片黑夜,激活了她的好奇心,而她的好奇心又連繫著她的熱情和生存意慾。
「那麼我可以現在就把貓帶回家嗎?」萬花對女人說。
女人轉過頭去看訥言,就像為了從他的表情去檢視,她聽到的話並不是幻覺。
***
萬花給貓起名「莫黑」,就像在名字裡去除牠的利爪。她所認識的自己,並不是個殘忍的人,她對自己說,立即把貓帶走,是為了把牠自籠裡拯救出來。
她原以為,貓從手提籠裡解放出來後,就會愉快地在家裡各個角落奔跑。可是,牠只是像一根被發射的火箭,迅速鑽進床底。
空蕩蕩的房子,看起來還沒有貓的痕跡,這給予她足夠的時間構思貓的名字:把「摸黑」的「摸」那手部的動作自名字裡拔去,在文字裡閹割了貓的行動自由。
***
搏鬥是一件有禮溫柔,甚至優雅的事。起碼,在萬花和莫黑之間是如此。
最初,她在等待莫黑破壞甚麼。或許,她真正在等待的是看到莫黑猙獰著臉搗毀她的家時,她會出現的反應。她期待自己起碼能勇悍地保衛自己。(畢竟,房子就是她的另一個身體)她把貓帶回來,她把入侵者帶回來。引貓入室。
暫託貓的女人委屈的八字眉偶爾會浮現在萬花的腦海:「或許黑貓是因為太愛植物,才會忍不住把所有花和葉,葉連枝也咬碎。那是牠表達愛的方式。」女人以哀傷的語調表達她盡力而為的體諒:「可是植物是我賴以維生的職業。這陣子,我一直胃痛,彷彿牠在啃咬的是我的胃。若非如此,我才捨不得讓牠離開呢。」女人撫摸著籠子欄柵,就像在撫摸莫黑身上閃閃發亮的黑暗。
萬花微笑地看著她。每次當她心裡響起警報,嘴巴就會形成和諧的弧度,像在安慰自己:「別害怕。」在萬花看來,暫託貓的女人展現了所有女性的兩難處境:「要不,忍受暴力的愛,愛愈深,殘忍愈發不可收拾。要不,忍受孤獨,愈孤獨,愈平靜。」
萬花說:「把牠交給我。」她沒有說:「讓我替你承擔。」她們心照不宣。
莫黑從床㡳小心翼翼,躡手躡足地走出來時,是在萬花熟睡的深夜,她驚醒後看到,在如墨的漆黑中,有灼灼的眼睛盯著她,像狼。她無畏地回視,過了好一會,又覺得,在她眼前的,是兩個圓晃晃的飽滿的月亮。
清晨醒來時,她聽到客廳有悉窣之聲,赤足走出去察看,莫黑正在嚼咬她最心愛的一件羊絨圍巾。她本來打算,那天披著那圍巾上班,而貓在吃它,像羊在吃草。雖然乾糧在貓碗裡滿溢著,但莫黑有著的卻是貓糧無法填滿的飢餓。她記得自己的諾言,無論如何,不責罰、毆打或監禁莫黑,那是她跟自己之間的誓言。
她走上前,抓住莫黑,一把抱進懷裡,抵住她心臟至肚腹之間的位置,那裡可以容納一頭貓的體積。貓並不掙扎,在她胸前安靜了下來,呼吸均勻,不久就睡了過去。
她想到處置牠的方式。她想到處置自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