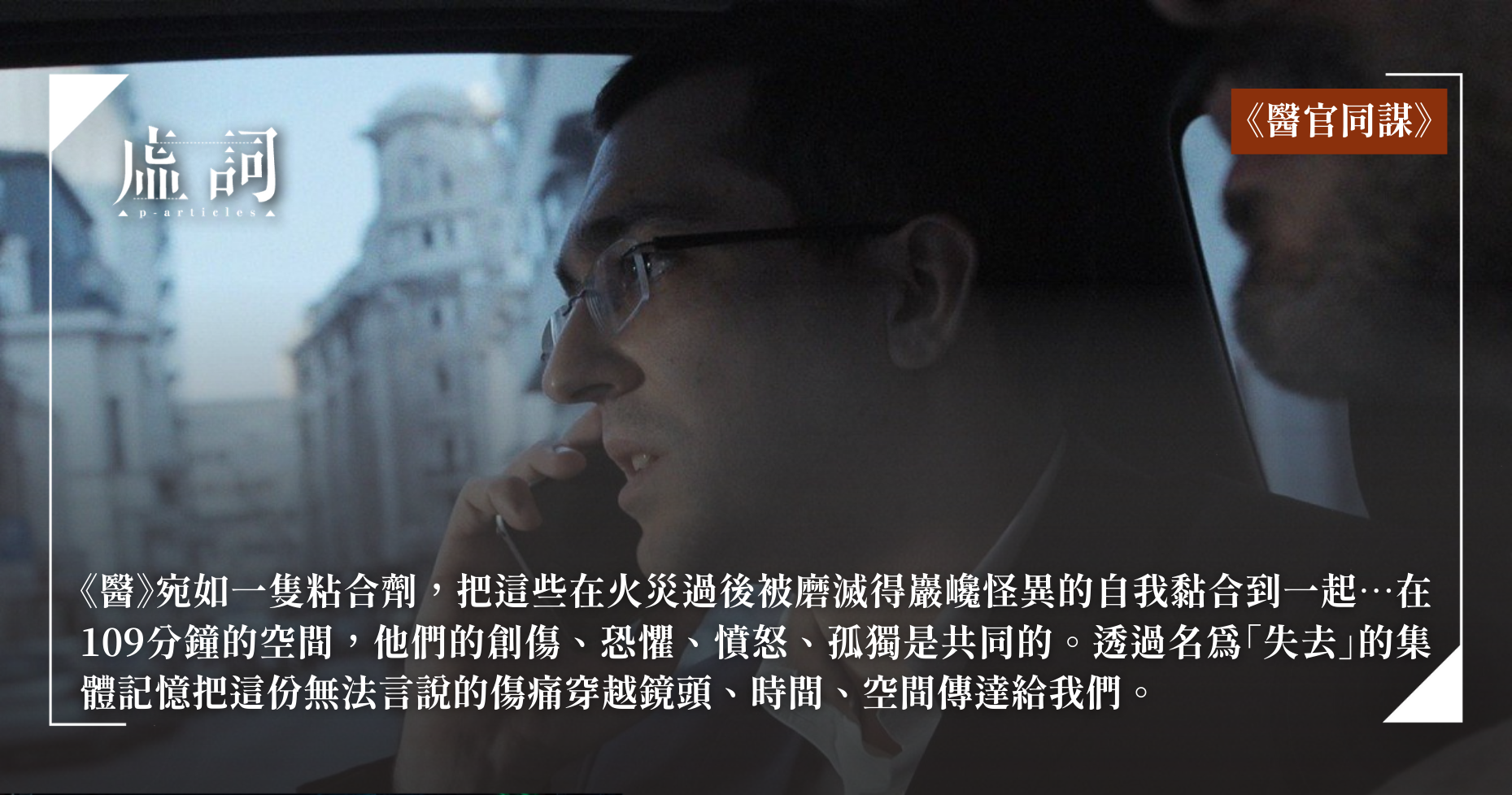《醫官同謀》:集體創傷與歷史書寫的距離
影評 | by 鄧皓天 | 2026-01-06
2015年10月,擅於以詞抨擊時弊的羅馬尼亞龐克樂隊Goodbye to Gravity在首都布加勒斯特一家名為「集體」(Colectiv)的俱樂部舉行了小型演唱會。當他們唱到《The Day We Die》中「We’ re not numbers, we’ re free, we’ re so alive, ‘Cause the day we give in is the day we die」時,迸出的煙火花點燃了黑漆漆的夜店天花板。隨著人們的歡呼轉為尖叫聲,大火已順著天花板蔓延至整間夜總會,瞬間吞噬了27條鮮活的生命。這無疑是自羅馬尼亞民主化後無法抹滅的一次集體創傷,只是,正如所有的創傷所指的並非災難發生的當刻,而是火災倖存者須在往後的日常一次次承受忽然侵襲的傷痛記憶碎片的無止盡的恐懼,紀錄片聚焦的也是火災事件後政府的處理失當,在揭露公營醫療系統背後根深蒂固的腐敗之餘,見證統治階層和整個社會是如何一步步讓這場火災淪為無法也難以言說的社會創傷。
雖然聚焦的是集體創傷,這並不是一齣典型的創傷敘事。在主角之一的記者卡塔利那·托隆坦(Cătălin Țepelin)誓必發掘悲劇真相的引領下,這更像一套借屍還魂——借集體創傷(屍)叩問國家制度(魂)的紀錄片。事件隨著托隆坦披露國家主要醫療用品供應商荷西製藥(Hexi Pharma)把醫院用的消毒藥水稀釋了十倍以賺取差價賄賂醫院高層,憤怒的民眾隨即上街要求執政內閣引咎辭職。只是,系統性的腐敗並沒有隨著執政內閣下台得以改善。在鏡頭對準致力改革醫療體制的新任衛生部長弗拉德·沃庫列斯庫(Vlad Voiculescu)後,觀眾會隨著發現弗拉德無力獨力解決系統性貪腐以及火災時任執政黨社會民主黨(PSD)在片尾的大選贏得前所未有的支持而感受到角色們的憤怒和無力感。然而,我感興趣的並不是羅馬尼亞政府腐敗的真相,亦不是這齣紀錄片是否道義地講述那場吞噬了64條生命的「人為災難」和倖存者的創傷經歷。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場109分鐘的鏡頭敘事中所呈現出個人創傷與集體創傷的距離,以及那些無法被主流歷史記載,消逝在時間洪流中的集體暴力和傷痛是如何在沈默的大多數的默許下構成的。換言之,我認為《醫》所呈現的不止是單純的集體創傷,更道出了歷史創傷書寫之不可能及其與創傷論述之間弔詭的辯證。
歷史的怪獸
《醫》採用了典型的線性敘事,以方便觀眾了解這場人為災難背後複雜的官僚腐敗問題,也由此暗示了導演紀錄片的目的——以紀念哀悼之名延續失敗改革之信念。只是,正如片尾弗拉德父親在得知涉事執政黨在選舉中大獲全勝後對兒子說的肺腑之言:「就像我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網上發表言論的人只是少數,只有百分之十到二十…你還在這裡做甚麼?這個國家三十年後也不會醒過來!他們沒希望了!這在五年至十年內都不會有改變,到你退休的時候,它依舊是如此。搬回維也納吧,我認真的。你的工作是徒勞的。在那裡你至少能幫助病人,以及有需要的人;在這裡,試圖喚醒人們,真讓人心碎。」這齣試圖為災難受難和倖存者討回公道的紀錄片竟以如此絕望的對白收尾,彷彿影片中角色們一年以來的努力都是徒勞無功。一套始於要為受災者討回公道的影片最終無奈承認了他們無力撼動高牆的事實,實在弔詭。
這讓我想起了王德威在回顧華語文學時提出的噬史的檮杌——一場圍繞現代性(modernity)和怪獸性(monstrosity),關於歷史和「再現歷史」的兩難。王指出無論在文學影視或非虛構寫作中,人們在書寫歷史時幾乎都無法迴避如何再現過去的暴力事件的破壞性的問題。若我們閱讀歷史的目的是為了不去重蹈前人的覆轍,那麼書寫歷史的人則該抱著貶惡揚善的態度來警醒後人暴力和災難的破壞力。然而,回顧二十世紀的歷史書寫,從西方到東方,大屠殺到六四天安門,旨於揚善的歷史幾乎都是由慘無人道的屠殺和對人類文明的失望拼湊而成。如此,紀錄暴力的怪獸本身即無法抑制暴行再現——甚至成為了暴力敘事的一部分,我們為甚麼還要繼續書寫、閱讀人類文明中發生過的暴行呢?此刻的我們到底是在改寫——還是重複——那充滿惡行惡狀的歷史(王,10)?
回到《醫》,我們不難發現整套紀錄片也以無奈的姿態詰問同一道問題:我們是在嘗試透過這隻影片改寫羅馬尼亞貪腐的過去,或只是單純把那讓無數羅馬尼亞人心碎的災難以影像的方式重現呢?事實擺在眼前的是有心人不僅無法撼動早已腐化入國家骨髓的貪官的一根寒毛,整個官僚系統還有隨著片尾的大選彷如吃人的怪獸般滋長茁大。這正是最讓片中角色心寒,也是現代國家政治架構下滋長出的駭人的怪獸。在影片中,整場災難超過一半的死者都是在入院後因細菌感染身亡,可是伴隨著荷西製藥負責人的「死因無可疑」,政府立即試圖為災難起因定案,結果除了那位致力改革的新衛生部長外,沒有一位官員或醫生就災難向受害者家屬道過歉。畢竟在這個名為集體官僚體系的制度中,除了那位被記者揪出來的製藥負責人外,其他既得利益者都並非造成病人死亡的直接肇事者,那只是一場由於「溝通錯誤」和製藥公司「欺詐」政府導致的不幸事故。這正是王所言的現代的歷史的怪獸,一種以國家體系和社會制度為主體,將惡更「瑣屑」和「人性」地融入我們日常生活的過程。在這個體系裡,每個沈默的人都將成為「惡」的幫兇,也正因如此,每個沈默的人都不能夠是「惡」的幫兇。換言之,在這個體系裡,「惡」的滲透將社會兩極化成「沈默的大多數」、「少數貫徹惡行的人」和「少數發聲的哨子」,所以「沈默的大多數」是注定不能也無法成為「少數發聲的哨子」口中的「惡」的幫兇。這種沈默造就「惡」更為猖狂的行徑讓民眾對災難後續發展的反應呈現出一種矛盾得幾乎滑稽的狀態:影片開首人們選擇相信政府因而沈默,換來了政府隨便應付的態度;在卡塔利那發表了那篇報導後憤怒的民眾走出街頭抗議,換來執政黨的「引咎辭職」,卡塔利那的抗爭似乎取得了勝利;持續爆出的貪污和新任衛生部長的改革宣言讓民眾漸漸習慣了這種「資訊性」的報導,絲毫不願相信整個政治和醫療制度已經腐爛到根部,為PSD換來了捲土重來的時間,最後選舉大獲全勝,彷彿那場一年前的大火和64條年輕生命從來未曾存在過。
民眾短暫的憤怒情緒和他們對制度性貪腐的沈默(或不察覺)似乎為六年後向媒體透露心聲的27歲的羅馬尼亞青年Theodor Vasilescu的話做了見證:「單靠示威抗議,你真的無法改變一個制度;日子久了,傷痛開始漸漸消失,人們就會忘記發生過的事(雪影劇場,2021)。」但我認為這卻是現代社會制度中幾乎無法迴避的系統陋性。我更願意用王的方式稱呼它:匿名存在於你我身邊的惡。在整場悲劇中,那些官僚和靠賄賂上位的醫生從來沒有害死那64條生命的想法,毋寧說他們在乎的只有一些蠅頭小利和自己的權位,充其量只是小貪小取,把這樣資質平庸的投機主義者稱為大奸大惡者似乎有點言過其實。這也是現代之「惡」的可怕之處,不同於大奸大惡者,由這些庸才和投機份子滲出的小貪小取的「卑劣」無孔不入,組成了一個以「國家體系」為名的匿名的巨大共同體,仗著「國家」名義和普通民眾對政治的漠然,以政治「機械」取代個人意志的行動,最終爆發出意想不到的破壞力。而在災難發生前一刻,身處其中的民眾都不會意識到這頭以國家體系為名的怪獸正如何悄無聲息地吞噬每個人,猶如一百年前魯迅筆下的吃人的社會,幽魂魅影似地穿越時間的迷霧和地域來到了2015年的羅馬尼亞。用卡塔利那記者同僚的話說,則是「這個故事太令人吃驚了,恐怕我們看起來都像瘋子一樣。」
創傷是書寫無法跨越的那些深淵
集體創傷之所以被稱為「創傷」,很大程度與這場悲劇無法透過歷史書寫的方式哀悼——被官方敘事足夠重視有關。自己的痛苦和意見不被官方重視,甚至打壓、竄改,這樣的經驗對倖存者而言無疑不是一種創傷的延續。心理學家蔣興儀在評論創傷理論時則把這種現在式的制度壓迫和現有的西方創傷理論分為「意外性質」(accident-based)和「壓迫性質」(oppression-based),而目前我們所有的創傷理論是建立於「意外性質」(accident-based)和大屠殺歷史論述之上,那些「壓迫性質」(oppression-based)的創傷我們幾乎無法用已有理論處理。不像已然成了歷史的納粹陰影,遭受「壓迫性」創傷的人至今依舊活在引致他們的創傷的體系中,他們居住在剝削了他們的生命的暴行的土地上,無時無刻不被某些殘存的事物喚醒那段痛苦恐怖的記憶。然而,只要實施暴行的當局一天還沒潰敗,這些發生過暴行的地點還是會被當局以一種似是而非的方式否認掉人們所遭受的傷害、痛苦和歷史。這也是上述Vasilescu那句話中弔詭之處:只要腐敗的政治和醫療系統一天還沒被重塑,集體俱樂部這場災難便無法被真正地銘記(如果銘記是為了不重複);然而一天集體俱樂部這場災難無法被真正地銘記,人們便永遠無法團結一心抗逆這個以國家為名的龐大而腐敗得官僚體制,除非有另一場更具破壞力的災難發生。
在人們終有一天會忘記傷痛,而引致悲劇的當局一天未倒台的前提下,這場導致64人喪命的創傷是注定無法被訴說,或以歷史的形式被記載。不過《醫》成功的位置在於它能融入典型的創傷敘事片段同時,把倖存者無法訴說的傷痛轉換成可言說的憤怒情緒,讓觀眾以另一個角度理解這場悲劇。首先,《醫》剪入了一段大火倖存女生泰迪(Tedy)出席她的個人攝影展的片段。片段中泰迪被大火燒傷全身一半的皮膚、肌肉,失去了所有頭髮和一隻手臂。在有心人的幫助和鼓勵下,她決定以模特的身分被攝影師拍攝一輯「火災倖存者」的寫真。在攝影展開幕時,一名記者與她展開了以下對話:
記:「集體俱樂部的那場大火後,你的生活有了什麼變化?」
泰迪:「我正為一個非政府組織工作,我正嘗試將我的精力放在我自己的復健和幫助他人上。」
記:「你是否對所發生的事情耿耿於懷?」
泰迪:「沒有,我沒能力耿耿於懷。」
記:「當你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知道這是別人的過失,而你本不會如此,你是怎樣找到力量繼續生存下去?」
泰迪:「我沒有選擇,僅有的路就是向前,向上。」
記:「怎麼可能那麼簡單?」
(泰迪微笑沈默以對。)
不少人會認為這位記者的發問不甚禮貌,被大火燒至面目全非,泰迪怎可能對火災不「耿耿於懷」呢?面對記者第二條問題,難道她要在自己的攝影展上說「不,其實我每天都很想死,但我不能死」嗎?這裏,面對記者針對性的提問,泰迪精簡的回答和最後的沈默道出了創傷之不可訴說(unspeakability)。在《釀電影》的一篇名為〈《一場大火之後》:大火之後,如何面對非人?〉評論中,筆名太空人的作者談論到泰迪的非人(non-human)身分是如何由個人和社會因素構成的。所謂的非人(non-human),是大屠殺論述中用來形容那些在集中營中喪失了人格的生存動力的倖存者,即便獲救了,他們在心靈和精神層面已經遭受到無法抹滅的傷害。他們像「活死人」般活著,無法向外人道出自己的經歷,也無法再對往後的人生燃起任何生存的動力。個人層面而言,造就他們「非人」身分的是來自火災侵入性的破壞力。超越言語和我們了解能力的痛苦和恐懼剝奪、麻痺了這些倖存者的情緒、表達和生理反應。他們被強行拋進了一個連他們自己也無法了解的狀態中,自我(ego)遭到撕裂性的破壞,創傷記憶宛如一個蠻橫的侵略者佔領了一部分的自我,和原先的自己一分為二(甚至更多),在倖存者體內形成了一個「陌生的我」(foreign-self)。而面對外界,他們沒辦法向旁人解釋這個異化了的自己,只能沈默以對。
社會層面,那名筆名「太空人」的作者提到影片中的政府和記者主動及被動地在社會層面排除這些火災倖存者。政府的推卸責任和謊言連篇,無疑是不把這些倖存者當「人」,而是「數字」和「麻煩」來看;就連想為倖存者「伸張正義」的記者,也因為自身的使命感而無可避免地把這些倖存者描述成「手無縛雞之力」的「受害者」,進一步削弱了他們在社會上的身分。這固然是我們老生常談的「不該將倖存者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的話題,我卻認為集體創傷中將倖存者「受害者化」是無可避免但也最有效的方式。這是由於在創傷中,當事人憂鬱、無法言說的各種消極情緒缺乏了政治能動力(political agency),而在任何改革性質的行動中,這些情緒都是無益於行動本身的(愛,362)。由於憂鬱和創傷所展現的情緒往往是虛無和矛盾的,當事人在承受這些情緒的同時不得不「內耗」來消化這些情緒,結果往往是在處理好情緒後當事人已經精疲力盡,無力再改變現實。因此,《醫》中透過訴說創傷和追尋真相的敘事營造的憤怒感是取代創傷後憂鬱情緒(emotion)的最佳情動(affect)。不同於創傷中那種「腳踏不到地」的虛無感和無限內耗,憤怒往往具有推動人們爭取、達至目標的動力。人固然會因為憤怒而衝動行事,但衝動的本質不正是基於「想改變現實」的想法產生出的情緒嗎?我們需要在意的似乎不是否認憤怒,而是如何利用憤怒的動力推動個人乃至集體達至目標。
我之所以以「創傷敘事」定義《醫》,很大程度是基於這部電影所營造出的「集體傷痕」的文化身分。白睿文(Micheal Berry)在《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中基於巴赫汀(Bakhtin)的理論提出了「向心創傷」和「離心創傷」兩種創傷敘事走向,前者善於把創傷事件轉換成團體內部的凝聚力,亦即是我們常聽的「南京大屠殺是全球中國同胞的傷痛」之說;後者則剛好相反,離心創傷事件往往由國家政權造成,民眾則因對國家失去信心而選擇轉身投向外界——國際。《醫》敘述的悲劇是典型的「離心創傷」:因政府和醫療系統腐敗而導致民眾對當局死心,不再信任國家和政府。惟片尾弗拉德對父親離開羅馬尼亞的勸告沈默以否定的形式把這場悲劇塑造成一場「向心創傷」:為了不讓集體俱樂部火災悲劇再現,我(弗拉德)決定留在這個國家繼續我的「醫衛革命」,同志們仍需努力。由此可見,即便結局讓人灰心,《醫》並不是一套呼籲羅馬尼亞民眾離開國家的「離心」敘事。透過把這場災難中不同的見證人、倖存者和罹難者連接起來,《醫》嘗試把這次的悲劇(或政府的暴行)改寫成一次民族性的創傷,只不過這次的敵人不是外部勢力,而是統治自己的當權者。
那麼,這齣以憤怒為調,訴說無法訴說的創痛的紀錄片最終成就了甚麼?我想以韓麗珠一次訪問的話作結:「有些人的失去是肉眼無法看見、肯定的,那其實才是最大的失去…但他(韓的外公)真正失去的東西,別人根本看不到。而小說不是跟現實生活對立,小說是一種我們在自身生活中發現的現實,所以我把這些寫進書裡,其實都是日常。」影片中無論是泰迪、那些罹難者家屬、塔利那還是弗拉德,他們都在這場悲劇的後續中各自失去了一些重要的東西,留下了斑駁殘缺的自我,但《醫》宛如一隻粘合劑,把這些在火災過後被磨滅得巖巉怪異的自我黏合到一起。儘管這些人都處於各自傷痛的孤獨中,但至少在這個109分鐘的空間中,他們的創傷、恐懼、憤怒、孤獨是共同的。透過名為「失去」的集體記憶把這份無法言說的傷痛穿越鏡頭、時間、空間傳達給了我們。
參考資料:
太空人. (2021). 《一場大火之後》:大火之後,如何面對非人?. 釀電影, 取自:https://filmaholic.tw/films/60827494fd897800010f3b96/。
王德威, 國立編譯館. (2004). 歷史與怪獸 : 歷史, 暴力, 敘事 / (初版). 麥田出版[社].
白睿文Berry, M. (2025). 痛史: 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 = A history of pain :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二版., Vol. 3). 麥田出版.
梁莉姿. (2025). 寫小說就像寫一隻貓在伸懶腰:訪韓麗珠《裸山》(下). Openbook閱讀誌,取自:https://bit.ly/3XIqWaV。
許寶強. (2018). 情感政治 / (初版.). 天窗出版社.
雪影劇場. (2021). 《醫官同謀》一場大火之後:貪腐體制政府殘民自肥,愚公應該移山還是移民?. 關鍵評論網, 取自: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5279。
劉人鵬., 鄭聖勳., & 宋玉雯. (2010). 憂鬱的文化政治 =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elancholia : selected essays /. 蜃樓股份有限公司.
蔣興儀Hsing-Yi Chiang. (2018). 不可能的見證:從「創傷的敘事」到「敘事的創傷化」.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64, 113–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