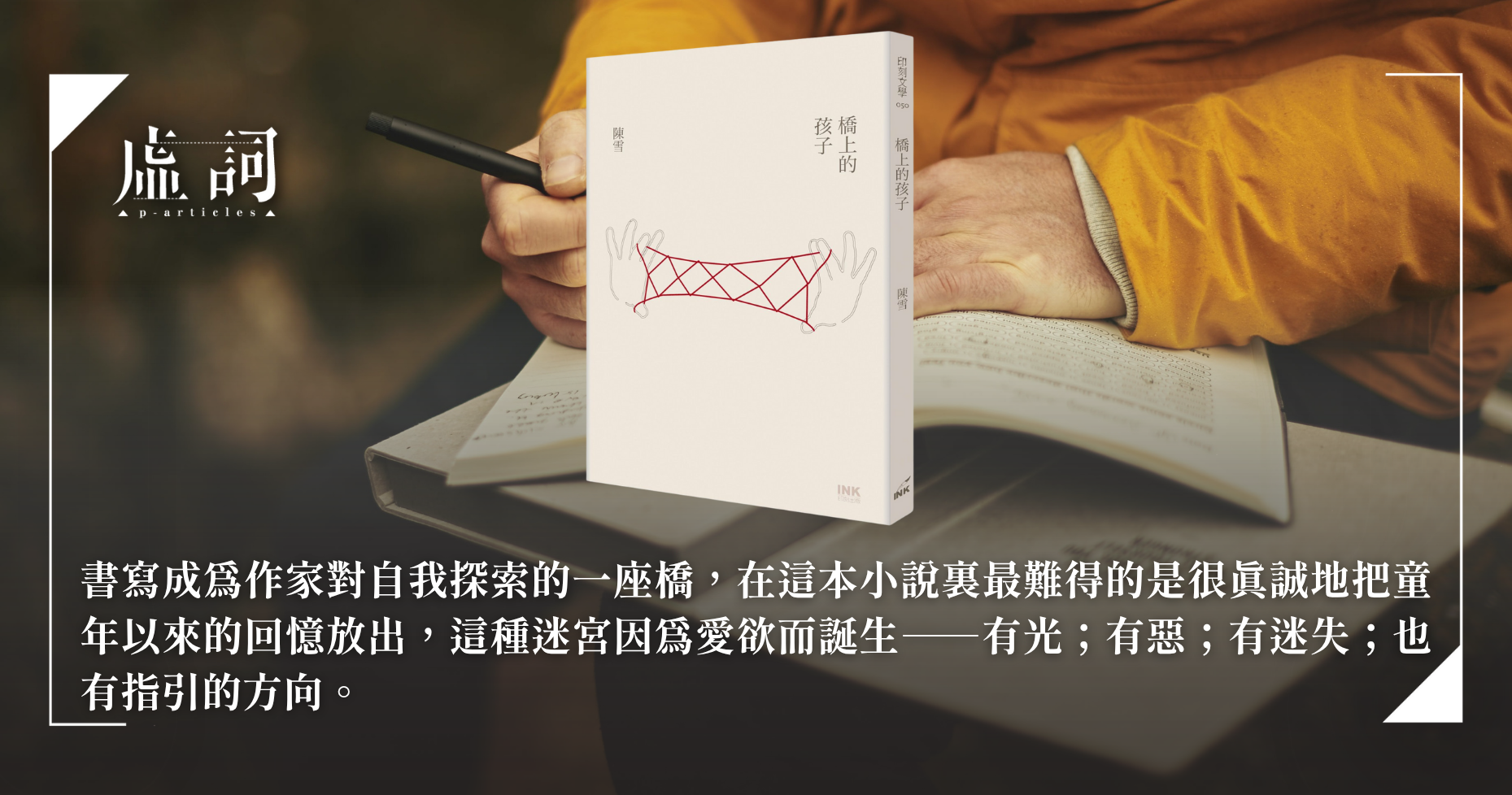邪火/(後)惡女的栽種與死亡——談《橋上的孩子》
書評 | by 雨曦 | 2025-10-09
《橋上的孩子》被賦予成小說家陳雪的自傳體小說,但我們能否撇除一切,如同進入她所構建的迷宮,最純粹的文字、情節是怎樣把惡女中入魔的「性」,變得通透是浮現仍活著的「她」在無數次破碎之後,形成的「愛」。允許我詮釋的不嚴謹,來深挖已經歷過一次的答案。其實以「生挖」或許更貼切,更容易實現一次又一次的創傷、又復原。
駱以軍在序中說:「我想到舞鶴的〈逃兵二哥〉或〈悲傷〉的結尾,夜市的漂遊場景,串接著城市書寫效力之外的另一個布景,俗穢與華麗,像人間失格的展場。」我腦海卻勾勒出另外一篇小說,七等生〈散步去黑橋〉駱看見的可能是城市中繁榮的嘌呤,掙扎與靠近之間,抵銷一些早該抵銷、被壓抑的情緒。我更看見作者在處理童年時,下筆的狠勁,在敘述之間:對話與情節的發展。怎樣延伸是讀者用怎樣的空間去閱讀,我會更貼切地形容閱讀小說,與呵護植物沒有差別,一段挺漫長且無聊的時間,但讀完的時候,或許就會開花了吧。
當然有些作品無法開花,就算小說裏有新的答案,但舊的答案早就隨著時間而封存。那作者去創造一個世界是為了什麼?像駱那般說追憶「市集的孩子」(不讓時間逐漸抹除記憶的緬懷)還是我思考的那座「橋」(只有這座橋通往過去與未來)創傷被小說家轉化成空間,我被不同小說中「橋」的隱喻所拉進,從城鄉遷徒、家庭與性別的割裂,翻開傷疤拼湊出來的事,是多麼沉溺其中才可以做得到。
在調度之後都是叩問。當讀者重新審視這三部曲《橋上的孩子》更像是她對童年的自救,要了解她佈置敘事才能了解她童年的困苦。
「女孩的父母在這條路上營生,從賣盜版錄音帶跑警察的流動攤販,後來轉賣過工廠倒閉廉價收購來的布鞋球鞋網球拍,賣過各式各樣四處找來的倒店貨,最後開始租一個固定地點賣女裝。……一開始在父親自己拼裝的三輪車後的平台上擺放堆積幾公尺高的衣服,女孩經常被淹沒在衣服裡假裝自己在游泳……」
這種極度克制的描述彷彿告訴我,那個暴烈與禁忌的女孩轉化成一縷煉獄誕生的邪火/幽靈。幽靈的通透讓橋的兩端看見彼此。陳雪曾說過:「偽裝,始終是我活命的伎倆。」當作者足夠孤獨,就會想把經歷重過一遍。(陳雪說:小說就像魔術,把生命不堪入目的回憶,淬煉成珍珠)但珍珠很多時候被譬喻成眼淚,重覆論證的情節,只為把叛逆逃離家裏的自己緊緊抱著。
書寫成為作家對自我探索的一座橋,在這本小說裏最難得的是很真誠地把童年以來的回憶放出,這種迷宮因為愛欲而誕生——有光;有惡;有迷失;也有指引的方向,從脈絡來看她揭開家庭與私密的傷口,對解讀小說的我添上一層「主體認同」的深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