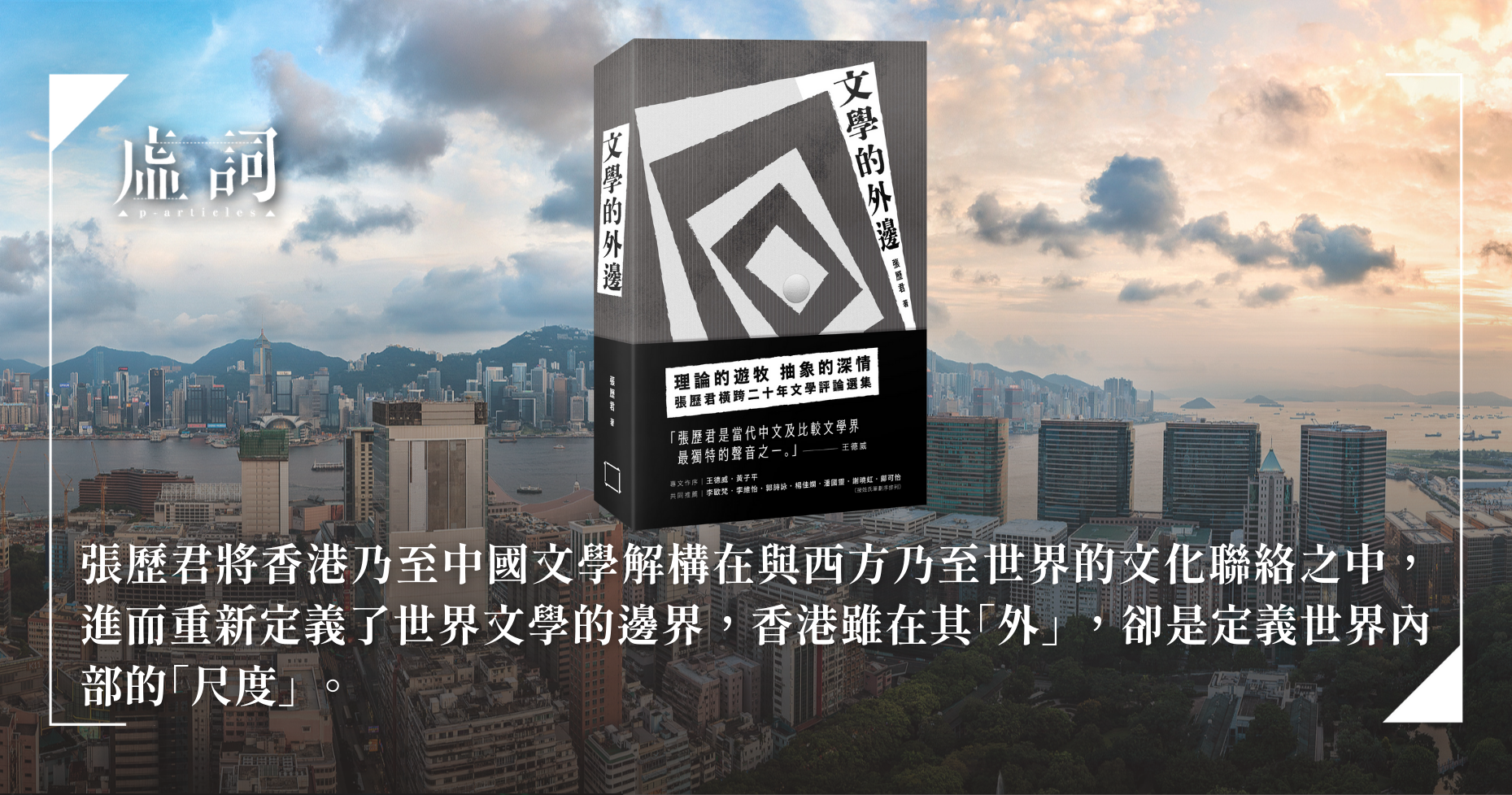批評,一種香港的姿態:讀張歷君《文學的外邊》
書評 | by 徐雨霽 | 2025-09-10
如何在南方邊陲小島,醞釀聯動世界、重理內外疆界的思想震動?如何在後殖民的都市,修築現代理論的話語系統,在業已逝去的文字檔案中,譬喻未來,重構當下?對於張歷君而言,文學批評是構成想象香港的一種姿態,更是指向了香港本身。他的新書《文學的外邊》與其說是一本關於文學批評的論文集,倒不如說是關於如何在香港書寫文學批評的實驗冊,更是關乎如何「作」香港(乃至中國)文學的評論、如何理解香港在地方與全球之間的文化指南書。此書是其多年來的批評文字之集錄,卻是體現出張氏對於香港和香港文學的念茲在茲之深情。
「外邊」:一個走向他者的行動
此書的題目「文學的外邊」具有多重意涵。「外邊」首先是一個關於香港及其文化可疑的、歧義的、流動的「身份定位」。無論是對於主流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敘事還是對於華語寫作的生成場域,香港始終沒有佔據「中心」之地位。但恰恰是其「外邊」性,香港構成了一種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筆下的匱乏(manque)、差異、雜亂。進而言之,作為本體解構的存在,香港及其書寫構成了一道「走向他者」的運動:「而他者則質疑它並不時地否定它,使得它只有在褫奪中才開始存在,這樣的褫奪讓它……意識到了自身是一個分離的個體:或許它將以此出存(ex-ister),將自身經驗為一種總是先行的外在性,或經驗為一種徹底破碎的生存,只有當它不斷地在沉默中猛烈地自我解體時,它才能整合自身。」(1)這種破碎的透明、這種不斷擁抱他者的行為,又奠定了在地香港、想象世界的開放性場域。
如果說布朗肖借由尚–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作品重返了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而後又影響了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外邊思維〉(“La Pensée du dehors”)的寫作,那麼張氏以「文學的外邊」為題恰恰是以書寫香港乃至中國文學文化的「他性」從而展開了召喚世界文學的龐大空間。故此,在他的文學批判之中,我們會發現,作家西西是以形式主義的眼光,在其小說〈肥土鎮灰闌記〉中,挪用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敘述體戲劇」(episches theater)模式重寫了元代劇作家李潛夫的《包待制智賺灰闌記》;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對「雙重性」(ambivalence)的思考本質上是內嵌在張東蓀對「相關律名學」(correlation logic)的探討;香港詩人馬覺或也與蘭波(Arthur Rimbaud)一樣,在「黑暗」的直觀中成為社會和時代的「通靈人」;李智良筆下的「少女顯靈」又在冥冥之中對照了德勒茲(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所刻畫的「女性寫作」(women’s writing)圖式……換而言之,張氏將香港乃至中國文學解構在與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聯絡之中,進而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的邊界,香港雖在其「外」,卻是定義世界內部的「尺度」。
「外邊」:一個作為方法的開端
其次,「外邊」也是將香港置於自身之外,解構自身的姿態,這成為張氏以之作為方法的起點。換而言之,張氏對香港及其文學文化的關注並不僅來自對香港本身,但它既源於也是內嵌在香港內部的情感與歷史的情境。但也正如最早提出「香港作為方法」這一修辭的陳冠中所強調的,不同於「亞洲作為方法」亦或者是「中國作為方法」,「……香港作為方法完全是指屬於全球化時代一種進行中的現代,但卻以強頑的本地性——這個本地本身又是個多元的中心——豐富了大家對全球化的理解。」(2)2016年,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的論文集中,編者朱耀偉談及了自1990年以來香港後殖民的論爭背後的「邊緣」焦慮,但也同時強調了香港(研究)作為範式即兼容世界和本土、駁雜東西的可能。(3)而對張歷君而言,香港以及香港文學的「外邊」之所以可以構成方法,恰與柄谷行人的「視差視野」(parallax view)形成了邏輯互動:香港意味著一種對於自身和世界/他者之間、彼此無法回到原初的「認識」。(4)也正是因為香港身處強烈的「視差」之內,它既構成了葉靈鳳對香港「似疏還密、似離還近」的歷史洞見,也使得冷戰香港內化成研究魯迅「人」之面向發現的機緣。
這樣看來,〈魯迅「內面」之發現:華語世界與「世間」的中國文學〉一章可謂是張氏之書的「文眼」。通過閱讀王德威的「『世界中』的中國文學(worlding literary China)」這一概念,作者重返了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術語「世界世界化」(the world worlds)以及和辻哲郎(Watsuji Tetsurō)有關「間柄」(あいだがら)和「人間」(にんげん)的闡釋,進而將現代中國與世界互為主客的辯證關係帶入了人之存在的個體性和社會性的相互建構性之中。以此為前提,張氏叩問了魯迅的「內面」發現即「人」的魯迅研究方向在冷戰香港展開的內在可能和精神脈絡。而能讓「內心和思想充滿矛盾的魯迅」在香港得以被挖掘,離不開曹聚仁和李歐梵這兩位魯迅研究者的神交、對話與交接。早在五、六十年代,曹聚仁採納了深受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影響的「新傳記」(New Biography) 範式,重現魯迅內心的衝突與失敗,以「求真」的姿態刻畫魯迅作為人的具體、內在與弱點。而李歐梵早年因選修了愛理生(Erik Homburger Erikson)的「心理傳記學」(psychobiography)的課程而展開了對魯迅內心世界的探索,後形成了1970年代初期,〈「魯迅內傳」的商榷與探討〉一文,最終奠定了李氏以生命經驗體認魯迅、研究魯迅的重要標識。曹聚仁與李歐梵對魯迅「人」之面向的發現,實則是衝破了冷戰時期意識形態二元對立的局面,在香港這個邊緣夾縫之島嶼,開闢了「非左非右」即不被「左」與「右」話語所收編的第三條路。不被左右意識形態所吸納和同化的冷戰香港成為了魯迅之「內面」的生存場所,這也構成了香港面對中國與世界的文化隱喻:香港既在世界/中國之內,也在世界/中國之外,它與後兩者的聯動性,又形成了香港之為香港的內在驅動力。
由外而內:香港之外,文學之內
此書「自題」為文學之「外邊」,而實則是擊中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之內核。如果說對西方理論的熟稔是張氏文化研究的「利刃」(例如作者從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對「控訴」[accusare]一詞的理解出發,將卡夫卡[Franz Kafka]的法律書寫視為一種與權威鬥爭的「自我誣陷」),那麼遊走不同文本與文獻並將它們創造性地闡釋和編織成意義的互文網絡,則是作者罕見的寫作「內功」。當張氏在巴塔耶的「純粹的、無羈的、本源的」內在經驗中發現其內化鈴木大拙(D.T. Suzuki)的「禪悟」軌跡,在本雅明的波德萊爾形象中,察覺了隱藏在其憂鬱眼光背後的異化不安和都市主義的無望,我們或也會對作者一種超越常規學術批評期待的詩意抒懷會心一笑,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抵抗教條批評的風格練習?
換而言之,「外邊」或者說以香港之「外邊」地緣觀華語乃至世界文學之「內在」亦是近年來張氏在文化研究領域耕耘的真實寫照。作者常年執教香港高校,又親自參與香港本土文學創作及研究刊物如《字花》、《方圓》等出版發行,既在學院之內孜孜造就,又出金字塔城墻之外培育新鮮「文學血液」。正是這種出入學術體系「內」與「外」的行為,使得張氏的文學批評形成了一種漫遊理論叢林、出入文本語境、對話當下與歷史的自由之勢,而在其中,香港坦然而又明亮地成為了其批評的底色和寫法。
在此書的〈後記〉,作者回憶了2019年「五四文學遺產在香港:李歐梵、曹聚仁與香港魯迅閱讀史」的公開講座活動的由來和現場實況:「……活動的反應非常好,聽眾坐滿百人的講堂,部分參加者甚至要席地而坐。」事實上,當年席地而坐的聽眾中,筆者亦在其中。六七年後,讀到此情此景,不得不感慨,文學的軌跡終於在平凡眾生生命某一個時刻形成了一道微弱而又明亮的迴響,而筆者則是有幸地見證,香港如何成為這道迴響發生(genesis)/聲(voice)的開端。
1/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著,夏可君、尉光吉譯,《不可言明的共通體》(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頁11-12。
2/陳冠中著,《我這一代香港人》(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5),頁47。
3/朱耀偉著,〈導論:香港(研究)作為方法〉,載入朱耀偉編,《香港研究作為方法》(香港:中華書局,2016),頁22-23。
4/張歷君著,《文學的外邊》(香港:香港文學生活館,2025),頁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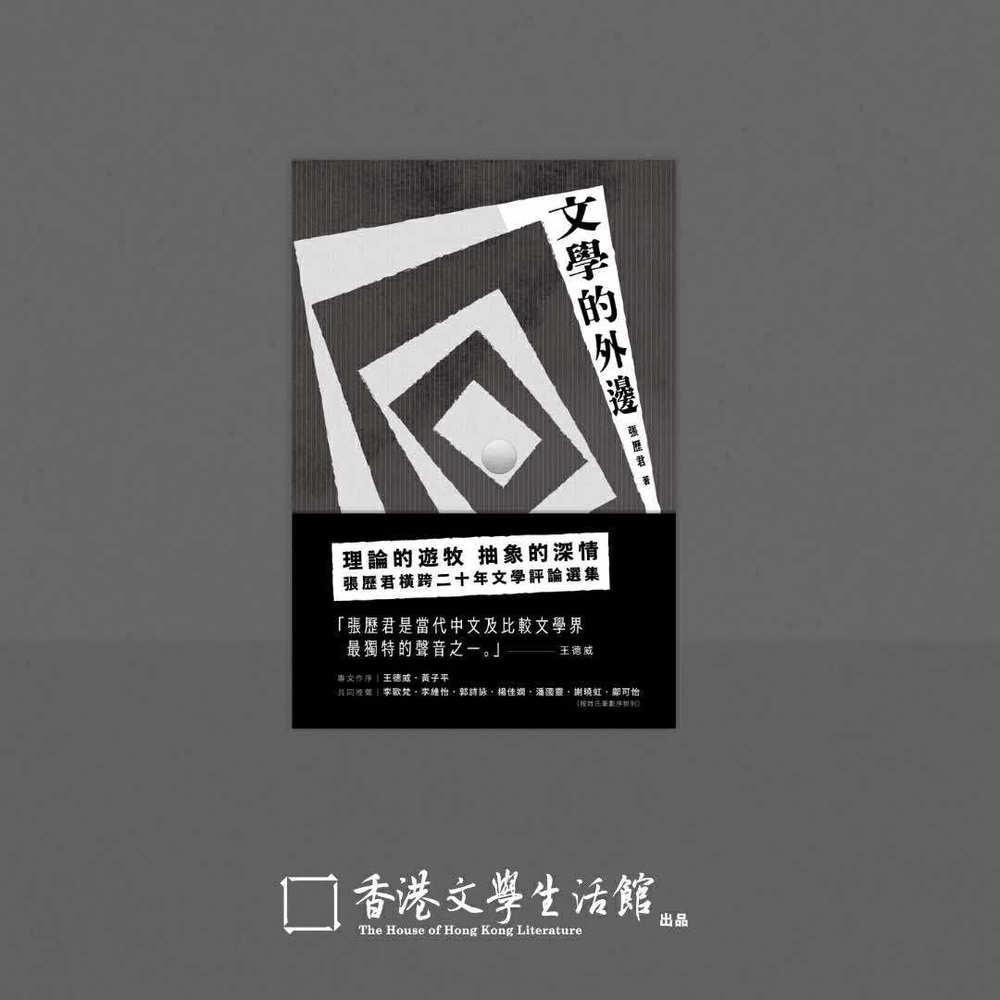
購書連結:https://www.hkliteraturehouse.org/shop/srtj85kadpdnzw7pkd3yggkpe8jn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