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吳其謙《後青春期憂鬱》嚴瀚欽序——〈犀牛、巨鯨、候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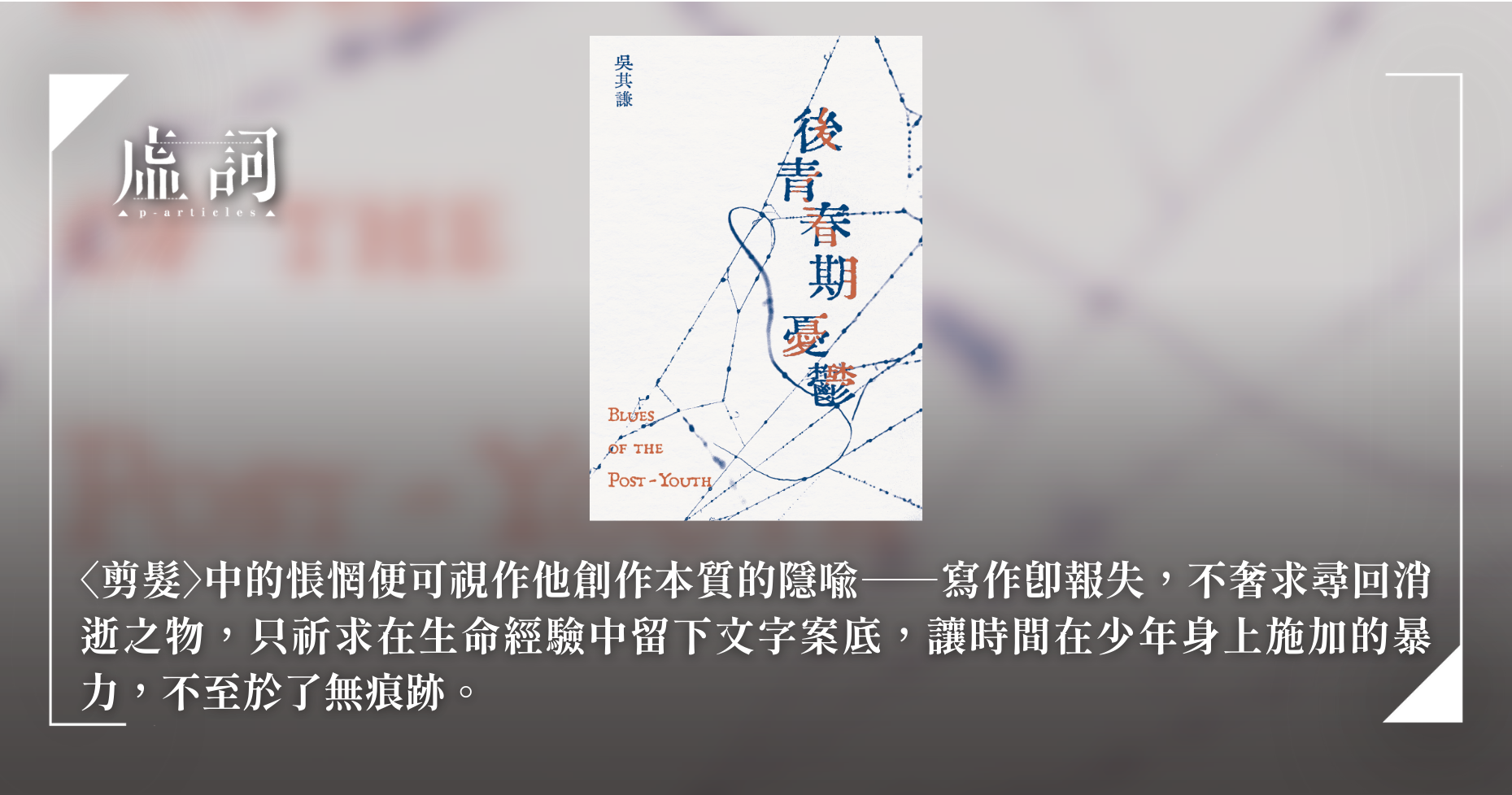
Template - 2025-09-29T153314.563.png
開始,我們失去的是記憶,但還知道我們失去了它,並渴望喚回它。後來,我們會連忘記本身也已經忘卻,城市不再記得自己的過往。
——奧罕.帕慕克《別樣的色彩》
引言
初識吳其謙的時候,他正站在生命的分水嶺,即將成為一個小孩的父親。那個即興聚會的夜晚,像繁忙生活中空出來的縫隙,我們在友人T的家中聚餐,聽搖滾樂。他看似雲淡風輕地聊起即將迎來的生活,戲謔將「徹底失去自由」,自嘲兒子應該會像自己兒時那樣,是個「百厭星」。但在酒精醺染的燈光下,我看到某種情緒自他眼中微微閃過,不經意間洩露着甚麼。這讓我想起他曾寫過的一首詩〈痊癒〉:
他們說,我的肩膊已經寬厚得
足以承受列車恆常輾過
是時候稱量過去,定義未來
(⋯⋯)
我走着,似乎重新感覺到體重
我痊癒了,帶着後遺症
詩中,他彷彿被時間推着前行,在每日的通勤中意識到自己肩負的責任,意識到自己早已不是那個可以隨意喊痛,卻始終有人寬慰的少年。而這也意味着,他必須將身上的傷隱藏起來。如今捧讀這本《後青春期憂鬱》,那閃爍的情緒,那些欲言又止的傷痛,彷彿一一具象了起來,恍若無數隱形的銀針。
最讓我猝不及防的刺痛來自〈剪髮〉,文中先用極為溫馨的筆調憶述柴灣舊居的髮廊,當長大後的「我」偶然路過,滿懷追憶之情推門探訪時,老闆卻報以陌路人的冷漠與疏離。那瞬息的頓悟何其銳利——原來並非人人都願意珍藏舊有的時光。正如他在書介裏的自陳:「現代人擅長遺忘,城市滿佈失物認領處,集體失憶以後,總有像作者一樣最先報失的人。」於是,〈剪髮〉中的悵惘便可視作他創作本質的隱喻——寫作即報失,不奢求尋回消逝之物,只祈求在生命經驗中留下文字案底,讓時間在少年身上施加的暴力,不至於了無痕跡。
洞穴裏的犀牛
究竟是怎樣的少年時光,才讓成年後的自己念念不忘?當我翻開《後青春期憂鬱》的首篇〈隱喻〉,便看到因天生的疾病而把自己隔離起來的他,終於在圖書館找到屬於自己的時空:「我穿過總是坐在櫃枱發呆的館長像穿過一件陳列品,然後找回角落那張小板凳(⋯⋯)我覺得自己置身於另一個凝固了的時空,與世界割裂開去。我漫無目的地閱讀,漸漸喜歡上第三人稱、句號,還有隱喻。」他透過書本中,那些第三人稱的敘事觀察自身命運,在隱喻的堡壘裏塑造自我,這份疏離感讓他每時每刻都身處空谷之中。而當他在〈房間〉裏描述:「房間不見天日,它明晰地與外面慘白炫目的世界分裂開去(⋯⋯)在我幽暗的斗室裏,我逐漸建構出對世界以及對自我的理解。」對他而言,幽暗已不再是囚牢,而是孕育認知的羊水。
自我隔離讓他自喻為世上最後一隻雄性北方白犀牛——蘇丹。這樣的孤獨延續到了大學(〈捉迷藏〉),當他看清迎新營裏的篝火與擁抱,不過是集體催眠的過渡性儀式,人終究要回到自己的洞穴裏獨自面對孤獨,他也就失去繼續扮演「我們」的氣力,才明白真正的歸屬不在喧嘩的群體,而在於坦承「人一旦開始躲藏就很難停下來」的瞬間。於是他帶着疲憊退回洞穴,像所有被存在主義咬傷的文藝青年那樣,讀枯燥的書,看長鏡頭的電影,聽小眾搖滾樂,更加心安理得地蜷縮在那個僅能容下自己的角落。
因此,當「我」面對〈隱喻〉中那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學生「你」時,才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的過去。此刻的老師「我」站在歲月的河岸,看着舊日的自己狼狽地涉水而來,突然理解教育最艱難的悖論:我們永遠無法替他人豁免疼痛,正如無法修復自己的創傷。於是,文章在此處才真正扣題——以「我」與舊我的對談隱喻「我」與「你」的對談。既然生命中的傷痛無法避免,既然只有當個體回望時,才能明瞭傷痛的意義,那麼身為老師,最恰當的姿態不是急切地告訴「你」一些無濟於事的道理,而是陪伴和見證。並在「你」變成一頭犀牛的時候告訴「你」(像告訴昔日的自己):你並非異類,你並不孤獨。便足矣。
傷痕累累的座頭鯨
言叔夏在《白馬走過天亮》裏如此描述成長之痛:「每個人都會在某一個天亮之前,告別敏感與脆弱的年少時光,無可避免地,一夜長大。」那是晨昏交替的曖昧時刻,對於吳其謙而言,這樣的告別或許就發生在畢業那年的旅途上。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裏以「壯遊」(grand tour)定義詩人的成年禮,而吳其謙的高原之旅,卻更像一場自我消解的儀式——徒步、禪修、呼吸海拔五千米的稀薄空氣,那些卡在夾縫中的異鄉時刻,既無法退回原點,又難以融入他者的疆界,他每分每秒都被提醒着自身的渺小。他終於懂得:「你必須接受生活存在另一種方式、另一種可能,接受你和你既有的價值只是滄海一粟。」
畢業旅行結束後,社教化仍不斷持續。他像袁哲生一樣躲躲藏藏許多年,卻在畢業後選擇了一份必須面對人的工作,必須直面教育制度的荒謬(〈特別課〉),必須習慣被身份規限(〈襯衣〉),必須坦承自己被瑣碎的生活挾持(〈火警演習〉),不得不做一些沒有marking scheme的選擇(〈放榜〉)⋯⋯於是新我不得不離開那小小的、光線很暗的房間,離開被四面白牆緊緊包圍的感覺,彷彿從自己舒服的洞穴中走出,直面灼身的烈日。
這讓我想起他給曾詠聰的散文集《千鳥足》作的序〈沒有勝負的井字過三關〉,他寫道:「聰(曾詠聰)寫兒時生活,不旨於還原歷史場面予以集體回憶,更多的,是為了對照他所否定的成人世界——孩時有多率性妄為,就更顯得長大後有多謹慎虛偽(⋯⋯)終究,也漸漸長成了軟弱的成人,生怕動輒得咎。」二人同為九十年代的「百厭星」,同為大學年代修讀文學的朋儕,步出社會後同樣投身教育,因此序中對曾詠聰的鋒利剖析實則也是倒轉向自己的責備,對他人的書寫終是一場映照自身的洄游。
直到那顆過於敏感的心逐漸鈍化,在無數次失眠之後終於不再服藥,不強求睡着,而是與失眠共處,與病共處,才正式步入了成人世界。就像〈不寐〉中,他夢見那頭停止掙扎的座頭鯨終於死去,最終垂直墜入深海,靜靜地躺在海底,沒有被任何人發現,只有「我」會在夢中偶爾認出牠滿身的傷痕。
「被省略」的成長
童偉格、胡淑雯《靈魂與灰燼:台灣白色恐怖散文選》的〈編序〉裏說:「一篇傑出的華語現代散文,首先是一篇看不出技術斧鑿之痕的作品;它唯一該具備的,是一道作者的聲音之流,衷誠地,鳴訴一段本真體驗,而使人共感於無論是記趣、憶往,或者,即使是那般艱難的傷逝與受創。」《後青春期憂鬱》中當然不乏各大比賽的獲獎作品(如〈隱喻〉、〈捉迷藏〉、〈順清〉),同時亦有篇幅短小的個人的呢喃。這些篇章篇幅不一、技巧不一,而貫穿其中,且最為動人的,則是他對時間「未徹底投降」的姿態。
當〈娥姨〉中充滿生命力的女人垂垂老矣,面容枯槁,唇色蒼白,當童真勇敢的阿俊墮落成躺平的青年,當〈老人褲〉中,「我」終於有能力買下心愛的衣物,卻發現已經沒有甚麼值得自己去取悅⋯⋯我們大概可以想見,時間的暴力是如何施加在單薄的個體上。
是的,吳其謙也在與自己不斷的拉扯之後,在生活中不經意地「厚古薄今」,最終無奈地和解(或是敗下陣來)。他固然無法永遠保持過去的純粹,固然要慢慢接受被生命磨平稜角的悲哀,但至少,他選擇了在變成另一種人的同時,用文字永遠記住那種被烈日灼傷的疼痛。我想起袁哲生在《靜止在:最初與最終》中用「浮誇的一代」定義早衰的靈魂:「我們是甚麼的一代?我覺得我們是浮誇的一代 (……)所有浮誇的人都漸漸感到步入窘隘,陷入恐慌。浮誇的人生的特徵是,從少年一躍進入老年,青年時期被省略了,所有浮誇者盡力延長他們的少年時期以符合浮誇的品質管制。」
他必然也曾深刻體會過這種「被省略」的成長,就像〈謎題〉裏,我們不曾想過,當年隨口說出的玩笑,果真在樹上結成了豐碩的椰果,更不曾想過,當椰子終於長得如此壯碩的時候,我們竟然要提防它掉下來,免得砸傷早已面目全非的自己。於是,他巨細無遺地羅列童年時的玩物:白飯魚球鞋、斜挎包、Game Boy 遊戲機、漫畫書⋯⋯這何嘗不是少年時光的延長,何嘗不是對時間溫柔的抵抗,透過作品回到過去,在精神上獲得安全感。
久別歸來的候鳥
讀到最後一篇〈裝修〉,全書收束於一種淡然的哀傷中。結尾處,「我」在敲打天花板的聲音中佯裝入睡。從少年時代將自己反鎖在房間的「深海魚」,到如今在裝修噪音中輾轉難眠的成年人,這個始終貫穿全書的房間意象,終於暴露出它最殘酷的模樣——成長從來不是破繭而出,而是不斷承受敲打重塑,被釘入成人模具的過程。於是我又想起文首提到的那首詩:
我痊癒了
面上的紅印日漸褪色
學會呼吸謹慎如假死的獵物
不再因炎夏而躁動、嚴冬而懷念關係
從年少的敏感症中,我康復過來
少年時過於敏感的體質,最終被馴化成成年後的虛偽謹慎。但吳其謙的妥協裏仍帶着溫柔的抵抗。他在〈明信片〉中堅持給珍愛的人寫信,在〈五千元的故事〉裏鼓勵學生用文字表達自己,在〈回港〉裏為一面之交的朋友繼續努力生活。然後用文字,為內心保留一間不被裝修的小房間。
十分喜歡〈記憶有嗅覺〉中的一個比喻,他說記憶就像一隻久別歸來的候鳥。那頭孤獨的犀牛被困了在童年,受傷的巨大座頭鯨已沉入時間的海底,而從犀牛到巨鯨,想必當中有太多被省略的無奈。但好在記憶像候鳥一般輕逸,當牠偶然歸來的時候,至少可以以文字為巢穴,讓牠在裏面短暫地棲息,好好整理旅途中被風吹亂的羽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