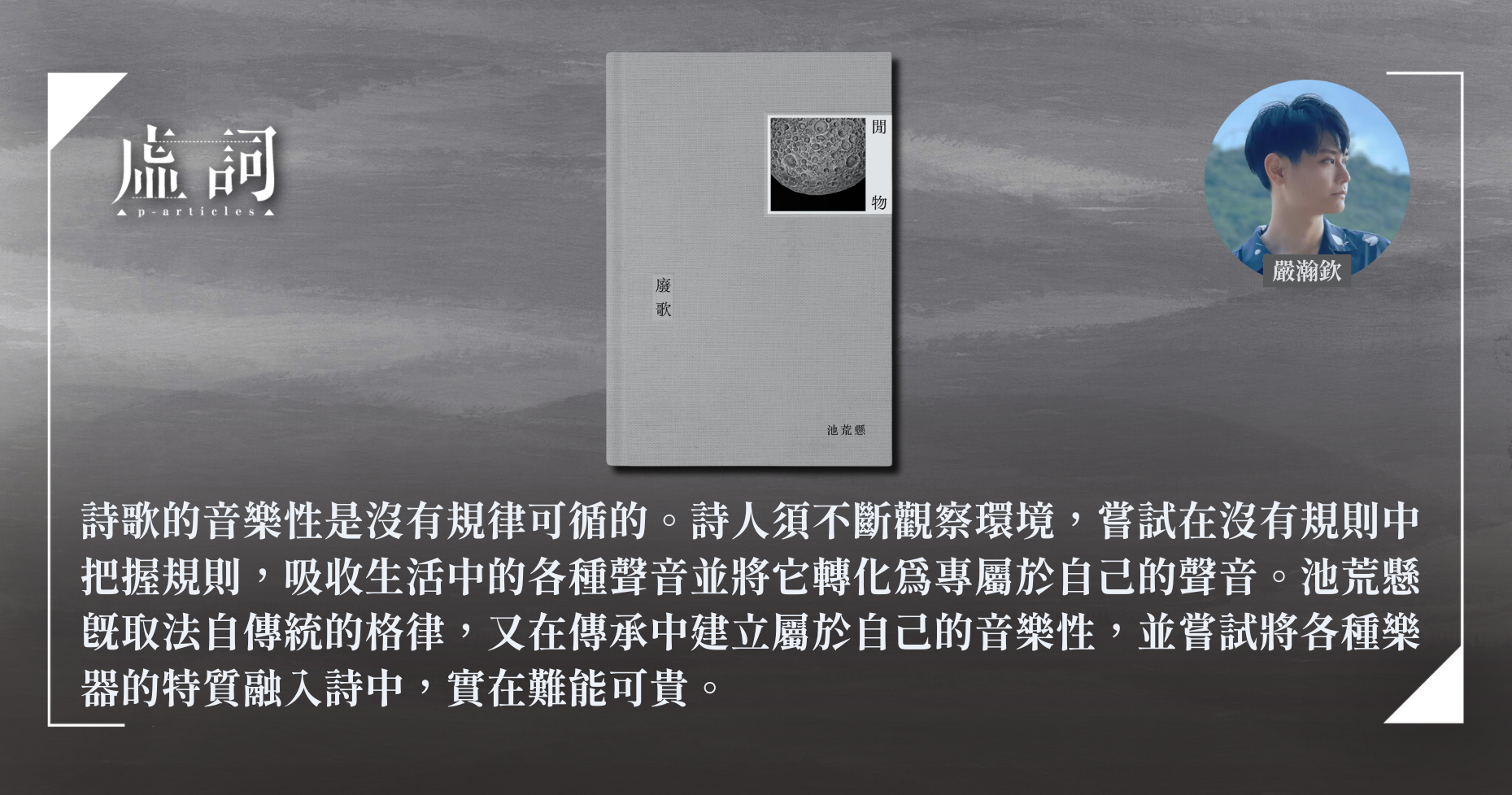淺析池荒懸《閒物廢歌》的音樂性
詩與歌關係密切,詩歌的評賞經常以「音樂性」作爲檢視的標準。更有人從發生的角度看,認為詩歌的起源本用於吟詠,斷言詩歌即是歌詞,音樂性正是詩歌有別於其他文類的根本。筆者對如此武斷的説法有所保留,畢竟韋勒克(R.Wellek)與沃倫(A.Warren)合著的《文學理論》[1]早已提出,音樂性並非詩歌獨有,在小説與散文中,聲音同樣是審美效果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不可否認的是,音樂性在詩歌的創作和評賞中的確舉足輕重,只是人們談到詩歌的音樂性時,時常將「音樂」、「格律」和「音樂性」等概念混為一談。台灣詩人張詠沂曾說:「世界各地的所有文化皆有發展出音樂,然而各種文化發展出來的音樂系統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就算是在同一種音樂文化之中的音樂系統,前後的音階系統也存在著許多差異。音階與協調系統絕對是高度人為的」[2]。被稱為「普世語言」的音樂尚且如此,與文字和語言關係更加密切的詩歌創作,其音樂性只會更加主觀,不同文化沉澱下來的格律必定相去更遠。畢竟律詩有律詩的嚴謹,俳句有俳句的靈光,樂府有樂府的錯落,商籟有商籟的張弛,詩經有詩經的一唱三歎,六行詩有六行詩的複沓迴環。
而且,詩歌發展至今,似乎陷入一種更為尷尬的處境。若完全不考慮音樂性,容易被說是鬆散無度。但依附於某一種格律形式,則會落入鐐銬的桎梏,反而變得牽強拘束。正如學者師力斌所說:「格律論已經進入一個死胡同。以格律為核心,期待一種定型化的音樂性模式,其結果只能是走向新詩自由的對立面」[3]。學者張桃洲在《聲音的意味》中雖稱「格律被視為新詩重返文學中心、重溫古典『輝煌』的一條切實可靠的途徑」,但他同時意識到這種做法「易於滑入『唯格律是問』和繁瑣的純技藝操作的窠臼」[4]。由此看來,我們如今談論詩歌的音樂性,便不應再局限於某一種格律形式,而應該採取更為機伶的方式。畢竟音樂性總是在不經意中發生,我們再也不能用一勞永逸的形式去定義和規範詩歌的音樂性。
詩人何其芳早在上個世紀主張要將「格律」與「音樂性」分開討論。畢竟音樂性是靈活的,格律是模式化的;音樂是包容性的,格律是排斥性的(謝冕語)。只是,當詩歌脫離了客觀外在的格律,音樂性又變成一個十分主觀的東西。夏濟安就曾在〈白話文與新詩〉指出:「現代人最大的失敗,恐怕還是在文字的音樂性方面,不能有所建樹」[5]。換言之,這很考驗詩人自身的樂感,以及能否單純通過文字讓讀者感受到這種樂感。這是一種綜合素養的考核,在沒有外在格律的限制下,詩人能否自覺地對押韻、換韻、鄰韻、寬韻、隔句用韻、複沓、排比、跨行對仗、隔節對稱、句式長短節奏、字頓等多方面音樂性元素進行綜合運用。一旦能夠巧妙運用各種調度手段,內在詩情便可以在最匹配的頻段,得到精準而細微的傳達。美學家朱光潛曾將節奏分爲内心的節奏和外物的客觀節奏,二者互相影響。當內心預期節奏與實際所感知的外在節奏相稱時,就構成快感的來源。
粵語的九聲六調為香港詩提供了先天豐富的資源。若要探討香港詩的音樂性,必然會回到最基本的問題——什麼是詩歌?詩歌可以怎麼寫?香港的詩歌可以有什麼不同於其他地區的面貌?香港歷來不乏詩人在這些問題上身體力行地解答,對詩歌的音樂性不斷進行嘗試。如陳滅與流行樂互涉的《低保真》、《市場,去死吧》,如蔡炎培從民謠中取法的《中國時間》、《無語錄》、《偶有佳作》,又如飲江堅持以粵語俚語入詩的《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和《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他們以一種更為靈動的態度,讓多方面技術恰當融合,產生一種協奏交響的效果,去實現詩歌的音樂性。不少詩作甚至被譜成歌曲。池荒懸為八十後詩人,現為石磬文化社長、香港文學生活館理事會成員。他於今年二月出版的《閒物廢歌》可謂是在這一脈絡上承襲下去。
自認識池荒懸以來,他似乎就不曾與音樂脫離關係。他曾學過二胡、色士風等多種樂器,懂得製作電子音樂,並且在石磬文化「讀音」計劃網站建造了「給詩人的粵音聲調分析器」,該分析器能夠快速辨識一首詩中每一個字的平、上、去、入。他的第一本詩集 《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和第二本詩集《海灘像停擺的鐘一樣寧靜》,書名都以沉默示人,詩如其人一樣寡言。但在表面的安靜之下,作者似乎正靜靜譜寫自己獨有的内在節奏。以與首本詩集的同名的詩作〈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為例:
一方塊建築
一塊平直的路
沒有人知道它們的意義
但知道它們的安靜
交通燈知道
欄杆知道
郵筒知道
城市的衣服是安安靜靜的
連花開的聲音都沒有
這是一個古怪的港口城市
入夜沒有遠洋的海怪傳說
上空沒有海鷗拍翅滋擾
遠航的船鳴被人遺忘
魚類因海水變辣而停止說話
地上沒有草沒有花
人代替了獸
獸因此依賴
幾何代替了樹
樹因此荒廢
車代替了馬
馬因此高雅
其他一切
都在流浪
冬季在流浪
塵在流浪
流浪狗在流浪
廣播在流浪
城市中摻雜的聲響
不論分貝
都只爲絕對的安靜
加上禦寒的大衣
城市中的人
安守本份
安安靜靜地做人
在安安靜靜的
港口城市
此詩描寫的雖是城市中各種靜物,但反復出現的叠句和排比、穿插其中的押韻、某些詞組的重複使用,無一不暗示池荒懸的寡言底下,實則掩藏著自己内在的聲音。而第三本詩集的發佈會上,他說在第二本詩集出版之後,便開始思考何謂本土詩的核心。他的結論是:聲音即是本土詩的核心之一。因此,《閒物廢歌》的面世似乎在向讀者宣告,他將要高調地把内裏的聲音顯發出來。單一個「歌」字,便足以讓不少評者留意到他想要在音樂性進行嘗試的創作野心。如洛楓稱他的「詩句往往織造起伏、連綿或斷裂的節奏,用『心』來朗讀的話,詩如歌,給人脈搏舒緩或跌宕的感覺,這源自詩人跟音樂長期相處的關係」[6]。彭依仁提醒讀者要留意「應留意傳統國樂和詞曲對詩人的影響。除了用字凝煉,語調冷峻外,傳統詞曲的節奏感也是值得欣賞的一面。此外,詩句中也洋溢著音樂感」[7]。廖偉棠則稱:「在『留下來』的詩人中,這樣做的詩人是最困難的證物保存著。幸運的是,樂感依然是他的滑翔傘,讓他無限接近荒地上的瓦礫而不被牽絆、摧殘」[8]。
先看〈腳鐐〉[9]一詩:
穿腳鐐跳舞好看
有一些字,開始被踏碎
成了塵,文章便打開窗戶
風且進,且出。死的墻
開始生長柔軟的內臟
文字碎成塵、落入海
在高處,山神與土地公
望天望海,連歎息都千言萬語
於是每人獲發兩隻
腳鐐
於是無人寫得出
一隻字。為此每人各交出
一篇文章
「腳鐐」是比喻,泛指政治、制度、規則等各方面的限制。評者鄭政恆說這首詩探討的是詩歌或文章如何在框架、限制與新的生機之間取衡的問題。適量的限制可以讓文章出現新的生機,但過量的限制只會導致「無人寫得出一隻字」的結局。「帶著腳鐐跳舞」讓筆者想起美國批評家佩里(Bliss Perry),這裡的「腳鐐」特指詩歌的格律。如果以這個角度理解〈腳鐐〉,我們甚至可以把它視為池荒懸的宣言,他對詩歌音樂性的取態——適當的格律可以為整首詩增添色彩 ,但我們不應過份依賴格律,要吸收轉化能夠爲自己所用的音樂性,摒棄限制詩思的僵硬模式。
筆者曾經學作近體詩,常親耳聽聞別人對格律的偏見,認為在破除格律後的今天,仍選擇進入格律的桎梏並非合乎時宜的事。但在眾多反對格式的論調中,池荒懸非但沒有順應時人,還主動嘗試和其他媒介合作,在傳統的音樂形式中借取養分。〈波盪〉[10]一詩正是他2021年參與「南音研究計劃」時,按照南音格律所改寫的自由詩。據詩人陳子謙記述:「當日他(池荒懸)展示了五個版本,讓人看到詩作如何在句數、用韻、結構上慢慢成形」[11]:
人生如寄 廢墟難修
人河往復依舊 今夜光害滯留
無聲無息 無盡走
似漣漪擺盪 又似苦修
提外賣晚餐 背囊掛身後
氣味通街遊走 彷似鄉愁
輪迴的日常 西服起褶皺
喧囂人群裡 獨你見海瞾
低頭無聲 繞步行走
避與黑狗 相遇街頭
輕騎、貨車 繞路慢走
還有電波、半月 山斑鳩
存在同時消失 彷似詛咒
行進同時倒退 怎樣逗留
結他長駐窗邊 風彈弦震抖
你說物極必反 內痛潛修
雷鳴只是瞬間 驟雨長久
煙霧又將冒起 繞蓋高樓
閉目低頭 山海依舊
候鳥遷徙 節氣無休
路人目光潛移 誰用口舌解剖
平靜晚飯 風浪中求
潮汐無聲 靜靜演奏
似漣漪擺盪 又似苦修
珍惜味道尋常 半凍啤酒
聽家常話語 天機虛浮
酒淺味浮 有海風調味
看水平線靜 浪花低飛
倒影深潛 再被激起
那些激起的尖叫 又漸衰微
船笛永遠準時 增添了風味
與對岸凝望 隔一海玻璃
破滅後波濤 湧聚又泛起
湧聚又泛起
彼岸從不迴避 也不遠離
整首詩共十段,除去首尾,其他段落都是四行。首段作為起式,寫「廢墟難修」之後的「人河依舊」,開啟並奠定整首詩的敘述。尾段作為煞尾,是整首的休止。而中間八段,無疑是對社會變動後的觀察和寄願。由於借用南音體材,整首詩句句用韻,有些句子甚至用了兩個韻脚。根據韻腳分佈,筆者姑且將整首詩分為兩個部分,一至八段為第一部分,此部分的「修」、「留」、「走」、「後」、「愁」、「鳩」、「久」、「樓」等為同一個韻。第二部分為最後兩段,此部分驟然換韻,「味」、「飛」、「起」、「微」、「璃」、「避」、「離」則屬於另一韻。韻腳的切換即是詩意的分水嶺,從第一部分到第二部分,情緒起伏明顯加劇,景語開始成爲作者的情語。「靜」與「低飛」、「深潛」與「激起」、「尖叫」與「衰微」,詩句的張力在這幾組反義詞的拉扯下達到極致,把詩推向矛盾並置的結尾:
破滅後波濤,湧聚又泛起
湧聚又泛起
彼岸永不迴避,也不遠離
陳子謙稱〈波盪〉的定稿,「既有現代感,又偏離了現代詩常見的節奏......詩句在有聲與無聲、破滅與重生之間擺蕩」[12]。在舊的格律中破滅,並在新的語感中重生。相信這正是傳統南音帶給池荒懸的養分,正如他說:「研習南音令我更了解廣東話的聲音特點和一些具體方法,我學習了很多,這些得著也許可以令我日後的詩更加『動聽』。如果沒有南音,我便要花更多時間去探索」[13]。
除了藉助傳統的韻律,池荒懸還常以練習樂器的經歷和音樂家的生平入詩。以筆者早前撰寫賞析的〈長髮——聽《流波曲》有感〉[14]一詩為例:
重新紮上千斤吧
兩根弦,折曲於一點
卻未敢說窒息是輕易的
再過幾年,你便要離開
這本來有指望的世界
如何定弦?過去流落他鄉的
困苦生活,或一種強光下
自我形成的永夜
別帶平鋪直敘的曲式上路
枯的蟒皮振動原本亦無害
瞬間的苦難無一不在兩岸之間
存在、流動、凍
官與流民,或留守房間的人
忘懷抑或珍藏著家傳姓氏
然而一切重要的發音始終會更替
在一聲又一聲巨響過後
何不讓噪音打亂拍子
失明者,換另一副眼鏡
當然,鄉愁仍是原地滋長的
所謂流落他鄉,所謂流波
變形再變形。我剪了指甲
卻留長髮。再過幾年
就連你,我也會忘記
全詩以民國著名二胡藝術家孫文明的生世為脈絡進行書寫。曲名的「流波」有兩層涵義,一指他在舊社會奔波不定的離散與遷移之苦,二指曲調如水波般緩緩蔓延,節奏平穩,速度變化較小,如泣如訴,似在娓娓述說前半生顛沛流離的困苦生活。池荒懸這首詩亦以此曲為寄調,全詩起伏不彰,平穩地述說孫文明的身世,但在平穩之中卻有意地在詩中穿插四字頓的詞組,如「再過幾年」、「如何定弦」、「困苦生活」、「官與流民」、「卻留長髮」,像是二胡奏樂的頓弓,發出短促而富有彈性的聲音,有強調其悲愴之意。而第二段的「瞬間的苦難無疑不在兩岸之間/存在、流動、凍」,前一句是整首詩最長的一行,後一句卻是整首詩最短的一行,並且是「二二一」的音尺分佈,音節短促醒目。作者如此安排這兩句的字數,無疑是想通過兩岸之間那長到難以跨越的苦難之河,反襯出孫文明苦困的生活。
若說詩意須通過恰當的詩藝(技術)傳達,那麼熟悉電子音樂的池荒懸無疑比其他詩人多了一種既神秘迷幻又綺麗酷炫的選擇。他時常在詩歌音樂節或讀詩會上為詩歌配上電音,或者讓參與者聽著電音進行創作。〈二極管〉[15]一詩副標題為「聽Aphex Twin與Global Comm unication有感」。Aphex Twin被譽為電子音樂界的莫扎特、IDM智慧舞曲的引領者。他重新定義了 Techno,顛覆英國舞曲文化,痴迷於創造、魔改與解構各式電子合成音色。Global Communication 則是由Tom Middleton和Mark Pritchard 組成的電子音樂二人組,他們 1994 年的專輯 76:14 在Dedicated Records 發行,成為 90 年代氛圍音樂和電子音樂的廣受好評的作品。這首詩講的便是他聽這兩個樂團的感受:
養神不養
神的台詞
跪在塵埃上
早晨祈禱
夜間褻瀆神靈
在水銀的漩渦中
貓夢見了各種甘泉或火湖
相反方向的陰陽魚
適逢電路不通
適逢逆數迷人
靜物好在不動
神好在神
塑膠虛無
卻總比你我
更接近永恆
跪在塵埃上
夢見水印的漩渦
卦象與樂感
暗中繁洐
二極管是電子樂器常用的零件,控制電流只向一個方向行進。於是他想象電路的正負兩極為「相反方向的陰陽魚」。全詩類似於通感,詩意模糊,若無作者現身説法,實在難以讀懂。但我們大可暫時擱置對詩意的解讀,單憑詩中複沓的節奏便可感受到迴環縈繞的美感,例如「養神不養/神的台詞」、「早晨祈禱/夜間褻瀆神靈」、「適逢電路不通/適逢逆數迷人」,以及重複出現的「跪在塵埃上」和「水銀的漩渦」。作者正如Aphex Twin和Global Communication一樣,耐心地利用樂感的滑翔,把讀者帶入那個奇幻神秘,變化莫測的夢境。雖然詩意模糊,但其中的「卦象與樂感」,已然在「暗中繁洐」。台灣詩人陳育虹曾說過:「詩人不試圖說服什麼,只是把感覺帶給人家」。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亦强調「每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個聲音的系列,從這個聲音的系列再生出意義」[16]。這樣的評價用在池荒懸這首〈二極管〉上再合適不過。
一九八八年,當詩人楊牧在《一首詩的完成》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旁徵博引古今中外的例子,向年輕的詩人們娓娓傳授如何琢磨作品的步調和聲量,如何觀察作品的句法、平衡與起伏時。我們或許就要意會先生的言外之意——詩歌的音樂性是沒有規律可循的。詩人須不斷觀察環境,嘗試在沒有規則中把握規則,吸收生活中的各種聲音並將它轉化為專屬於自己的聲音。身為以詩作為志業的寫作人,身為專研各種樂器的愛好者,池荒懸既取法自傳統的格律,又在傳承中建立屬於自己的音樂性,並嘗試將各種樂器的特質融入詩中,實在難能可貴,相信他的下一本結集絕對更讓讀者期待。
[1]【美】R.Wellek, A.Warren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頁158。
[2] 張詠沂:〈詩與歌──到底「音樂性」能給詩什麼?〉。鏈接:https://andrewchang123.wordpress.com/2009/10/08/%e8%a9%a9%e8%88%87%e6%ad%8c%e2%94%80%e2%94%80%e5%88%b0%e5%ba%95%e3%80%8c%e9%9f%b3%e6%a8%82%e6%80%a7%e3%80%8d%e8%83%bd%e7%b5%a6%e8%a9%a9%e4%bb%80%e9%ba%bc%ef%bc%9f/
[3] 師力斌:〈新诗格律与现代汉语关系的探索〉,《中國文藝評論》,2017-04-19。
[4] 張桃洲:《聲音的意味:20世紀新詩格律探索》(人民出版社,2014),頁9。
[5] 夏濟安:〈白話文與新詩〉,楊乃橋編《比較詩學讀本(中國卷)》(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頁115。
[6] 洛楓:〈城市的墓志銘與風景畫:讀《閒物廢歌》〉。
[7] 《閒物廢歌》推薦短評。
[8] 《閒物廢歌》推薦短評。
[9] 池荒懸:《閒物廢歌》(香港:石磬文化,2024),頁156。
[10] 同註9,頁77。
[11] 陳子謙:〈南音︰起點抑或歸處?──「南音新創作展演」的兩種實驗〉。鏈接:https://zihua.org.hk/magazine/issue-46/article/new-naamyam-2/
[12] 同註11。
[13]馬世豪訪、王家瑜撰: 〈《聲韻》詩刊十年:亂世中一起讀詩〉。鏈接:https://www.literaturehk.com/new-blog-77/2022/3/3/-
[14] 同註9,頁60。
[15] 同註9,頁130。
[16] 【美】R.Wellek, A.Warren著,劉象愚等譯:《文學理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頁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