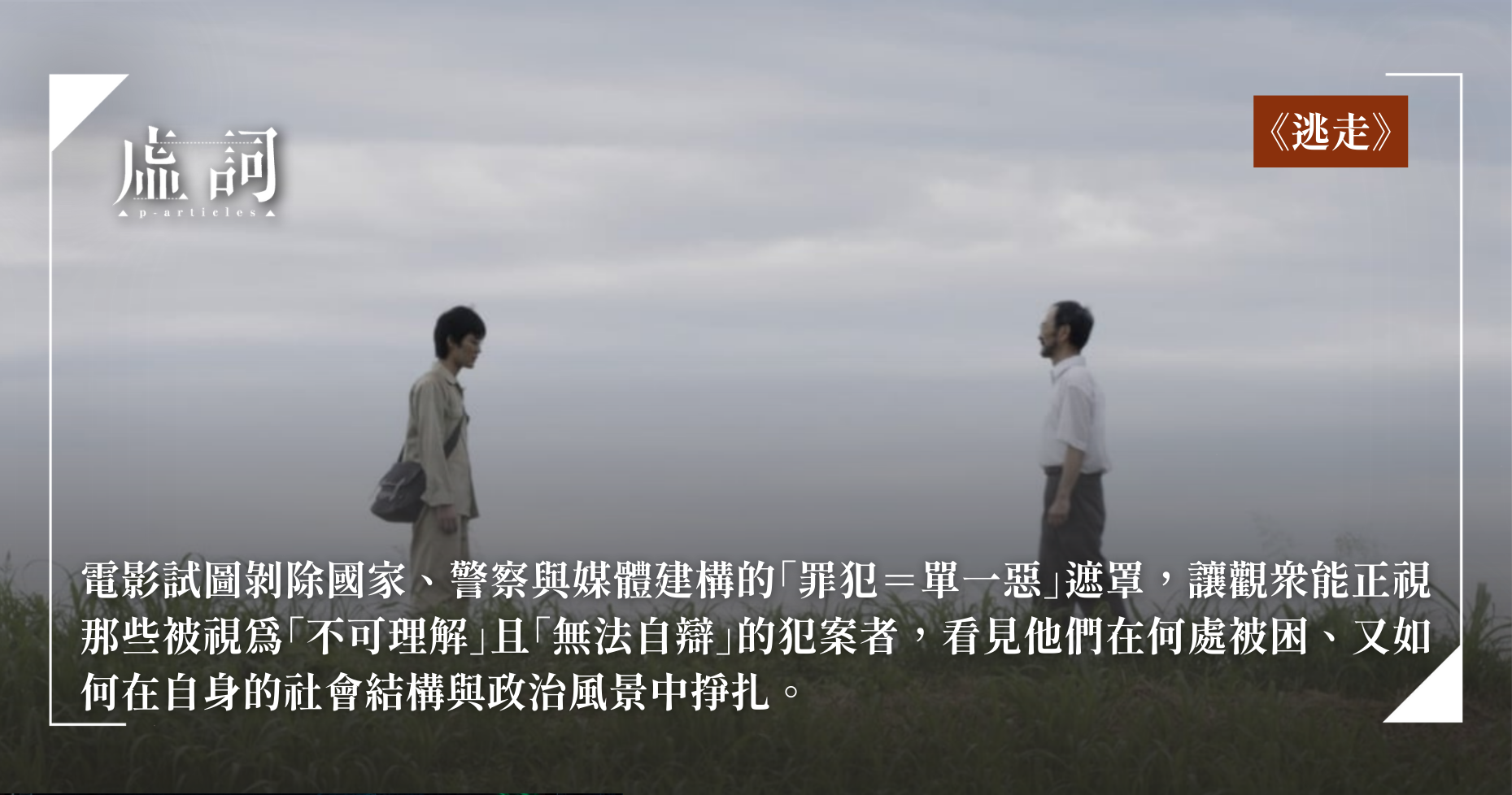足立正生《逃走》:逃亡與戰鬥的風景
影評 | by 惟嶼 | 2025-12-02
//
足立正生導演的新作《Escape》於十一月在 M+ 戲院上映。11月16日首映當日,仍受出境限制的足立以視訊形式參與近一小時的映後談。
回溯足立正生的創作軌跡,自1969 年完成《略称・連続射殺魔》(A.K.A. Serial Killer),他持續將攝影機指向被主流社會標記為「案犯」的一端——連環殺手、武裝鬥爭者、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以及種種越界的行動者。跨越實驗影像、宣傳式新聞片、紀錄片與劇情片的創作並非凝視「犯罪」本身,而是重建犯罪者視角下的風景。真正被顯影的並不是面目模糊的犯案者,而是一串埋伏在日常光景中,使暴力得以發生的政治條件。《逃走》延續創作姿態,以「案犯」桐島聰的逃亡追索近半世紀以來被封存的日本政治與記憶史。
//49年逃亡史
「49年」是桐島聰隱匿的時間。
2024年1月,一名叫內田洋的末期胃癌長者被神奈川縣醫院收治後主動表明自己是桐島聰,即70 年代涉嫌參與連續企業爆破事件的案犯。隨後,東京警視廳介入,向檢方提交了與五宗爆破事件相關的起訴資料;但桐島在一個月後過世,使案件無法進入司法審理。

桐島聰的意外現身與迅速亡故,在足立正生心中投下了一個急迫而難以迴避的提問:49年間,他為何選擇逃亡至死?49年後,瀕死的他又為何選擇公布真名?他立刻啟動製作,電影在桐島逝世一年後面世。
此前,桐島聰在大眾記憶中的形象如通緝單張一般扁平:長髮、厚眼鏡框、身高一米六,咧嘴微笑、眉梢微挑,一張永遠停在二十歲的臉廣布日本各都道府縣。燈箱柱、地道、車站角落,甚至赴日旅客隨手的旅行照中,這張臉偶爾出現,留下明確的微笑。半個世紀的長度足以讓這張面孔徹底去脈絡化,沖淡它曾召喚過的政治議程;也讓它從暴力與「恐怖份子」的治安框架中剝離,被城市庸常的風景重新收編。
同樣的49年裡,日本社會經歷 GDP 飆升、全面中產化與秩序化,深嵌全球資本體系;城市在高速現代化中自我吞噬,市民政治感受性日漸退場。世界另一端,巴勒斯坦地區戰事反覆,殖民殘緒迄未終止。全球與在地的震盪,共同構成《逃走》所回望的政治地層。
//「罪」與「無辜」之間:足立正生的倫理調整
雖然日本主流媒體與警方通告始終以「過激派」、「テロ」(恐怖主義者)的治安框架界定桐島聰在連續企業爆破事件中的位置,但反轉這個治安維穩的話語,他與同代行動者也可被視為未能成功取得合法性的位置的政治運動參與者——在既有政治制度內沒有發聲管道,因而採取了越權、越界的方式試圖介入公共領域。最後,爆破行動因計算偏差誤傷民眾,使「罪」與「無辜」之間複雜的地帶被刑事證據收束,桐島聰一生的行跡則被壓縮為「罪—逃—老—病—死」。正是如此,足立正生意識到介入歷史、打開敘述的急迫性。
《逃走》試圖鬆動桐島聰半個世紀中板結的社會形象,將他重新安置回1970年代激烈政治變動的總體中,理解被國家敘事排除在歷史之外的行動者。電影開篇便嘗試進行微妙的倫理調整,以舞台劇式的幾幕會議重建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的內部討論,形式上呼應大島渚《絞死刑》,各成員以獨白形式陳述分裂的立場:有人認為誤傷民眾是不可挽回的錯誤,帶著悔意主張中止;有人則堅持必須擴大震盪,使社會意識到反抗的必要。透過這種劇場化重演(註1),電影將當年單一組織的爆破行動放回日本安保鬥爭、反越戰與去帝國化的政治場景中,拒絕將行動簡化為「個體激進化」的結果。爆破案不是一個人的道德失誤,也非孤立式恐怖行為,而是七十年代全球激進抗爭理念在日本撞擊建制的複合產物。桐島與多數成員當時只是二十歲上下的高等教育青年,見證學生運動的失落,也在冷戰結構、左翼語言與國家鎮壓的交錯中選擇了革命的敘事。故此,「政治活動家」與「恐怖份子」的界線在語言中難以切分。
借助影像,電影試圖剝除國家、警察與媒體建構的「罪犯=單一惡」遮罩,讓觀眾能正視那些被視為「不可理解」且「無法自辯」的犯案者,看見他們在何處被困、又如何在自身的社會結構與政治風景中掙扎。
//「逃走」與「鬥爭」之間:留給人的位置
理解足立的嘗試,或許借詹明信(FredricJameson)的話語更為生動吧。他在《政治無意識》中如此肯定馬克思主義的總體化敘事的作用——那些「看似長久死去」的歷史事件只有在被重新編入「單一偉大集體故事」時,才能恢復原初的急迫性,如飲血復甦,再度開口言說。這個層面上,《逃走》確實為桐島的半世紀逃亡提供了一套清晰而堅定的精神解釋——將看似消極的隱匿,實則在延續未竟鬥爭。
日文中,「逃走」(とうそう)與「鬥爭」(闘争・とうそう)同音,構成一組語義上彼此牽引的雙生詞。逃走指向個體的生存策略,潛伏、匿跡,消失;鬥爭則指向顯性的政治實踐,直面對抗國家機器。足立正生利用這組同構關係,試圖將桐島聰半世紀的消失解釋為延續「未完的鬥爭」。在警方展開全面搜捕後,青年桐島被告知:「你的任務就是逃亡,不被發現。」逃走被規定為一種組織授予的使命,而非個人恐懼的偶然結果。往後的日子,他遊走在都市邊緣:鄉郊、舊工業區、工地、臨時工人宿舍,被脆弱且溫和的平靜環繞。電影中段,當青年桐島顯露出迷茫與動搖,敘事者便透過「老年桐島」的超現實降臨加以勉勵,老者向青年宣告:「逃走即鬥爭。逃到最後,就是鬥爭到最後。」
我理解足立製作本片的「非此不可」,但仍然無可避免察覺到其中同構的危險性,即總體化敘事在單一文本中的脆弱。一方面,我們需要沿著桐島的人生脈絡進入歷史,才得以再度回望他的生命;另一方面,當電影開始鋪展足立所熟悉的歷史縱深,那股宏大敘事的力量自動運轉,膨脹到再度將桐島聰作為個體的細節壓平,觀眾真正聽見的並非桐島的內在獨白,而是後設性的思想投射。在這個雙重運動之間搖擺,電影試圖將桐島還原為一個人,另一方面卻不斷把他拔高為理念的道成肉身,他作為「人」的空間,在敘事後段愈發縮小。

如果只將《逃走》試作一部孤立的文本,分析或許可以告一段落:我們觀看到「逃走」與「鬥爭」的同構,同時目睹個體與歷史寓言之間的拉鋸。然而,將電影放回足立的創作脈絡,我很難將其中的信念解釋為「革命失敗,而敗走會抵達另一種勝利」,如此姿態,或許太過簡單。回看1971年攝製的宣傳紀錄片《赤軍:PFLP 世界戰爭宣言》,其中接受足立採訪的巴解成員談及寡不敵眾、勝算渺茫的處境:「我們不會把自己視為個體……單獨的生命必須聯合、擴張。」在這種革命語彙裡,所謂「革命主體」早已超出了具體個人,而是由一個個不斷折損的個體串接構成。
作為實體的歷史,只能透過後來者的敘述加以把握;電影本身就是一組敘述,而每一次敘述必然伴隨變形。足立始終想打開行動者內心的風景,而當桐島終於被「演」出來時,屬於他本人的細節、痛感與猶疑卻遭到稀釋。至於是否將自己的處境投射到桐島身上,足立在映後談中的回答是「yes, and no」。
//逃走,作為一種景觀
我可以理解,敘述中溫柔而堅硬的騎劫是足立正生歷史觀的體現。但在影像層次上,電影並未完全服從這套整合,反而留下些許從敘事中「溢出」的部分。
四十九年過後的日本,安保運動與左翼激進政治抗爭的歷史被擠壓到社會記憶邊緣,桐島高度符號化的臉孔同時在現實中完成了一次「風景化」。足立回憶,許多日本民眾早已習慣了那張通緝令上的笑容,「連小學生會對著他的照片說:今天要考試,希望你替我加油。」他的大頭相逐漸從警戒圖示變成一種親切的時代符號,不再標記某種危險,成為日常所見風景的一部分。這個角度,電影文本無法佔據現實,也無法統治敘述,但仍然固執地提醒了桐島聰不可見的在場。
影片中,桐島選擇作為地盤工隱匿,理由恰恰是不引人注目,工人多為外地而來的邊緣流動人口與在日韓裔,只要身體還能動,總有搬運與拆除的工作;雇主也鼓勵他安心開工,因為經濟發展、都市重建會源源不絕製造生意。他的行跡恰好回應了足立在六十年代加入若松組,經由集體創作與逐步理論化出的「風景論」(fūkeiron)。足立曾指出:日常所見的一切風景,甚至明信片上的「美景」,實質上與統治權力的某種身影相連,是資本主義與國家體制的外在顯現(註2)。最簡單的例子是工地,大規模的土地規劃與基礎建設需要動員金融、行政、都市計畫等多重權力。在早期實驗色彩濃厚的《略称・連続射殺魔》中,足立刻意讓敘事沈默,攝影機長時間凝視道路、圍欄、工廠與集合住宅,讓「看起來什麼都沒發生」的城市風景暴露出其中潛伏的暴力秩序,風景即政治。
表面看來,桐島聰逃亡的後半生已經遠離了暴力與國家權力,他的出租屋只有一台舊式收音機、半瓶未飲完的燒酒,日常平淡,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而這個「逃亡中的日常」並不溫柔,他禁止自己像通緝照上那樣無憂無慮地微笑,每一個鏡頭都在提示他藏身的地方不是一個中立的空間,而是體制重新布置城市、重新分配身體與勞動的前線。如此,以通俗劇情片作為影像形式的《逃走》確實延續了風景論部分的敏感,桐島從在逃亡中被迫將身體安置在結構性暴力近乎透明的最細微處。而當國家以平穩、建設中的景觀蓋過異見者的呼聲,暴力就是風景中的正常狀態,桐島聰執行的匿名勞動便是匍匐其中,忍耐。
如果說足立早期的實驗電影與政治參與在於逾越既有「政治電影」的模式——既然風景本身就是體制的呈現,要真正改變它,便必須介入體制本身——那麼,《逃走》作為一次影像上的再介入,面對的是一個「介入失敗之後」的世界。風景消化了爆炸,桐島的逃走在這片景觀上留下微弱而幾乎不可見的刮痕。
這個意義上,電影呈現出自我反身性的矛盾,也留下一條不算答語的回應:足立正生透過老年桐島的獨白,竭力為這段逃亡賦予鬥爭性的意義,讓「逃走」在敘事層次上重新對接革命的單一大故事;另一方面,桐島四十九年間隱匿的行跡與他所承受的風景,本身自成一段難以被敘述捕捉的語言。他遁入風景,在日常化的暴力之中生活、呼吸,日復一日,同時固執地作為一個歷史的觀看者存在著。
註1:影片亦具體交代組織運作:東亞反日武裝戰線近十人的小組被分成「大地之牙」、「狼」、「蠍」等單位,以一種半分散的蜂巢結構運作,各自負責選定企業目標、製作爆破物、計算火藥量與決定行動日程。
註2:Masao Adachi, interview by Jasper Sharp, Midnight Eye, August 21, 2007, http://www.midnighteye.com/interviews/masao-ada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