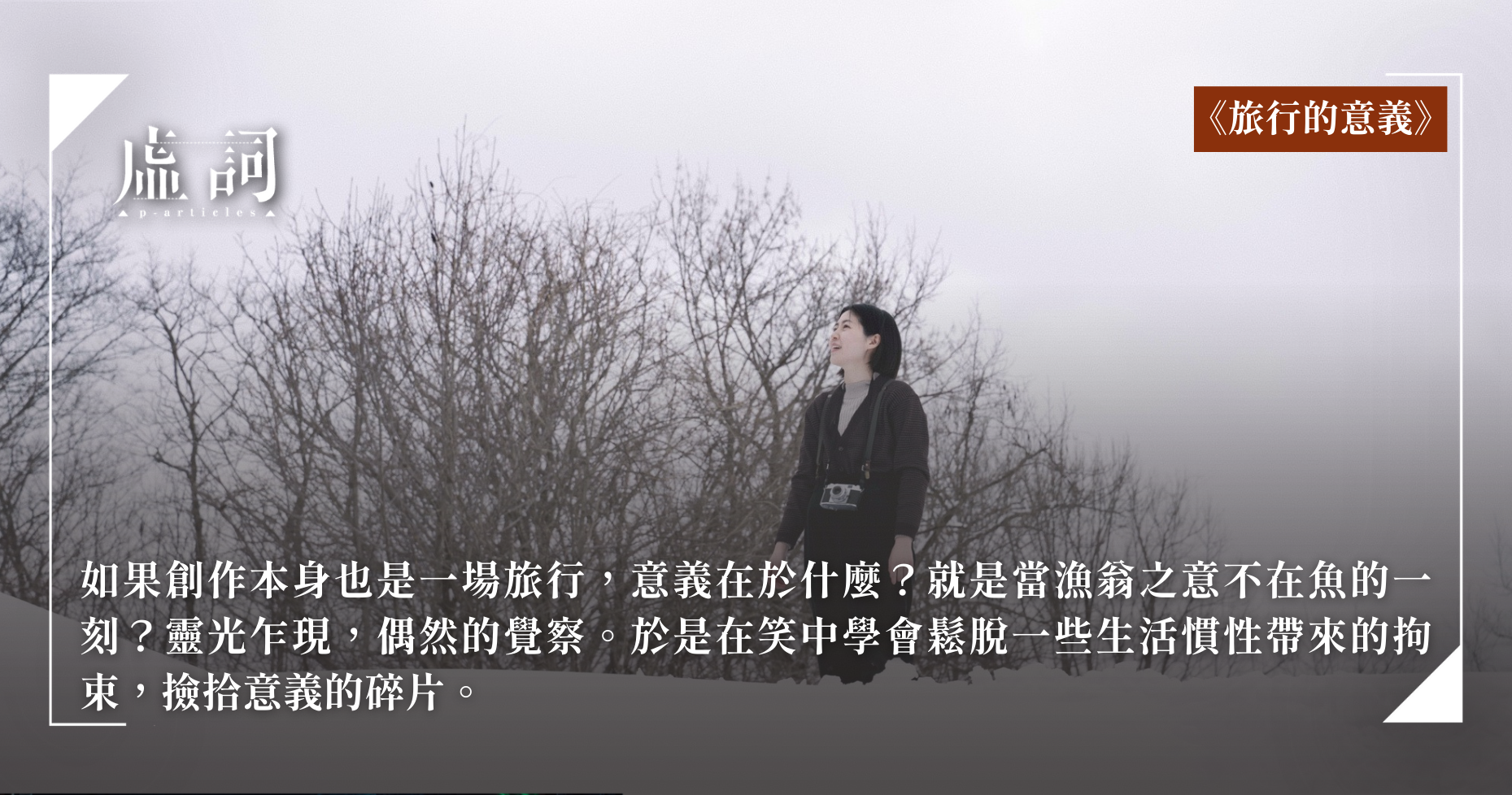漁翁之意不在魚——看三宅唱《旅行的意義》
影評 | by 陳嘉歡 | 2025-12-31
【劇透警示:本文將詳細討論劇情細節、轉折與象徵意象,包括兩段故事的核心事件與結局。若尚未觀賞電影,請先避開本文,以免影響觀影體驗。】
一對青年男女和一對中年男女,相遇相識又分開,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想起相似的鏡像關係有《一一》,後者捕捉到生命重複的幻相,前者則脫離循環繞出可能的去向,是雪地裡蹣跚向前的足印。
旅行是消散的霧,夏日暖風吹散以後在霜雪中被重塑。如果用三個問題貫穿兩對男女的故事,可能是:
1.我們如何處理孤獨感?
2.彼此療癒是可能的嗎?
3.我們該如何面對殘缺的魚身(人生)?
年青世代的故事
男女在島上晃蕩,偶然在沙灘上遇到。男生說曾在右邊的海面看見屍體,是抱著孩子的女人,下面就是八爪魚洞穴,會吞噬肉身。因此覺得可怕。女生對畫面有更同情的直覺,她說:「比起可怕,更是覺得可悲吧。」
殘缺與不安是人生的真實形態,旅行能夠揭開真實的自己,也源於對陌生的恐懼。在本地歷史的博物館裡,女生看見島上漁民與生死相拼,女人為死者弔唁的海洋信仰,木製偶像和畫作。這種對死亡靜默的敬畏之情,在兩個故事(海洋和雪地)裡得到不同的呈現。比起語言對話,電影裡比較著眼以畫面處理這個恆久的主題。
兩人在沙灘上看見擱淺殘缺的魚身,靜默無言。在臨別的一天,女生先跳下水,隨意問起魚在哪裡。男生想要回應女生的問題,為此在冰冷的海裡尋找活魚的蹤影,不惜把嘴唇凍紫,簡單真摯的情感。海裡的男生向岸邊的女生比劃(「這麼長的」魚),聲音卻被海浪掩蓋過。
在岸上散步時,男生說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提出的疑問亦很真摯,不知道生命如何變得值得活下去。女生提到兩個看似相似,卻截然相反的答案:用另一種身分繼續人生,或者重新開始另一段生命。她希望離家後永遠不回去。永恆似的決絕是青年世代的底色。
中年世代的故事
男人營運破落的旅館,認為戲劇應該刻畫幸福,例如發達致富。興起之時,半騙、半逼迫失意的女編劇結伴一同偷竊觀賞用錦鯉魚,其實也是另一種純粹,荒謬可笑。
中年承擔生命另一種的沉重。女編劇認為自己沒有天賦,在發佈電影後(年輕男女的故事),在自己的影後談裡尷尬不安地捲縮身體,直白地說出「可能自己沒有天賦」的話。面對朋友教授突如其來的死亡,她嘗試模仿教授生前的興趣,用拍攝擷取生命眼前的一刻,以鮮明的感官刺激自己,取代被語言符號追上的壓力。她想到,旅行的刺激來自於可以從本來的語言文字符號中掙脫,將眼前的生活陌生化。
拍照為提醒自己活著的此刻。但恰巧,當她下意識放棄紀錄的意圖時(無意地丟失教授的遺物相機),反而能夠享受其中。偷錦鯉後,男人滿心期待打開木桶蓋子,以為可以賣幾百萬日圓,誰料魚被凍水冰封。女編劇因此覺察到生命的可笑。在沉重中感悟到輕盈,重新找回生活和創作的節奏和意義。
在男旅舍主人的抱怨下,女編劇才知道養錦鯉一家正是他前妻,富麗堂皇、被誦經聲圍繞的庭院,錦鯉魚池和亭亭玉立的女兒,都是他觸手不可及的幸福,嘗試令其觸手可及,用半夜偷魚的方式,將幸福單一歸因於財富,最終也落得一場空。是否池邊的神明真的有力量,或是誦經者的一聲聲吆呼奏效,醒來以後,紅藍燈便在門外徘徊。(頗喜歡結尾,刑警溫柔摸他的額,彷彿這不是一場犯罪,只是出於小孩發高燒的妄想癡語。)
女編劇在虛構過程中有所窒礙,對於自己作品的主題也難下定義,原來界定自己的作品很難,但是在現實的旅行中,她經歷自己虛構作品中鏡像般的事情(一男一女在孤島中相遇,不深入地相識,但某程度上相知,尋找魚的蹤影,最後離開對方),似乎她主宰故事的同時,她亦被自己的故事帶領,開啟新的經驗。對白不時重複(如:「話真多」、「經常待在室內會憂鬱」)。在看似重複的經驗裡,不同的比相似的更引人思索。兩次旅行中的閃光和趣味,沉思和低吟,證明女編劇並非沒有天賦,而是在沈靜的想象中受困,走進雪地裡,短暫地參與他人的人生,反而鬆動到新的可能。
兩個故事
青年和中年的兩個故事因為互相呼應,在敘述兩個基調相近的故事中,或許也刻畫創作者(導演三宅唱)對創作迷惘,但又從創作中重新得到力量的過程。也不禁想問,如果創作本身也是一場旅行,意義在於什麼?就是當漁翁之意不在魚的一刻?靈光乍現,偶然的覺察。於是在笑中學會鬆脫一些生活慣性帶來的拘束,撿拾意義的碎片。如河合優實蹲在沙灘裡,嘗試點亮煙頭明暗的光影,一閃、一閃。
語言在意義的必要中消卻,剩下身體感受風和夜色。可能寫下這篇也是不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