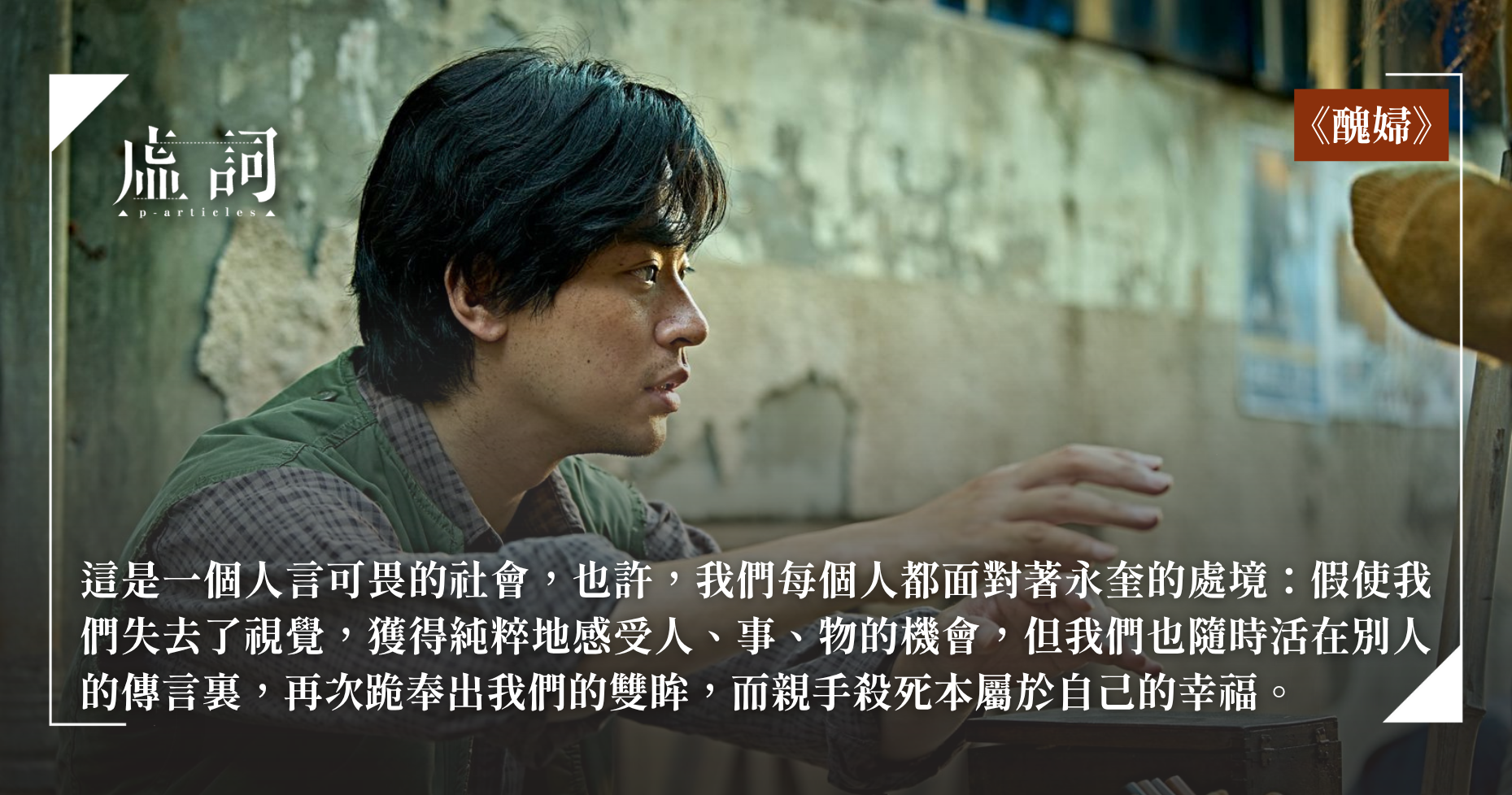《醜婦》:兩個傳言的世界
影評 | by 姚金佑 | 2025-11-12
《屍殺列車》的名導演延尚昊新作《醜婦》(The Ugly)近來在香港戲院上映,油麻地電影中心完場後,甚至有映後座談會談論該作,題目為「為何韓國人對美醜如此執著?」。題目如此設立,難免因為該部戲就是圍繞一名醜婦,所以,美醜,便是作品的重中之重。而且,電影一出,也有些影評專論戲中反映的女性困境。然而,儘管這些都是《醜婦》有所觸及的面向,但是,我認為該部電影的重點是落在「傳言」的恐怖。
誇張點說,《醜婦》就是一個由傳言堆砌而成的故事。這個傳言,起始於韓國國寶級雕刻家任永奎的兒子東煥接到警察的電話,被告知尋獲他母親鄭金熙四十年前的屍體,被判斷為「他殺」。究竟母親是如何死去的?母親生前到底是怎樣的人,這似乎比訪問國民雕刻家更有趣,於是,本來進行採訪的女記者,就轉而與東煥一同查探金熙的身世。除了母親的親人形容她醜得要命之外,逐一接採訪的人群,由昔日工廠的同事,到金熙的女前輩金淑,再到當初工廠的白老闆,無一不認為她的臉容不堪入目。
當然,查探的過程,也逐漸發現母親是一個善良的人,仗義執言,當女前輩金淑被白老闆強奸,她便為金淑公開聲討,一如她小時揭露父親有外遇,隨即受全家冷待,並離家出走。是待她好的永奎給了她再次追求正義的勇氣,但是,原來父親永奎是一個在社會底層掙扎求存的老實人,自小因天生失明而受人欺凌屈辱,當他以為雕刻圖章刻得一手好字、獲人青睞,甚至與金熙結為連理,走向幸福之際,卻意外發現,周圍的人當初欺騙他——原來金熙是個醜女人,也因為金熙追究白老闆,而使他一同受折磨,再度過上屈辱的人生。卒之,永奎親手殺死了他曾以為的幸福。
這部作品有趣的是,它以五場訪談作為電影的敘述結構,是挺新穎的形式:第一次是金熙的親人,第二次是金熙的舊工友,第三次是金熙的女前輩金淑,第四次是金熙的前老闆,第五次是父親永奎。自調查牽涉母親金熙的死亡起,這訪談已不再輕鬆,儼然如盤問不同的證人,如黑澤明的電影《羅生門》一般。然而,與《羅生門》不同的是,每個人在訪談中除了證詞之外,還共享著一樣的傳言,亦即是金熙醜陋不堪。這傳言是跨越每一場訪談,似是彌漫著某種氛圍,逐步籠罩一切,而這就是圍繞金熙而建立的傳言世界。
其實,戲中還有與金熙的傳言相對的另一傳言世界——父親任永奎天生失明,卻能雕刻出世上最精緻的印章,是舉世知名的工藝大師,是韓國仍存活的國寶級人物。這段敘述,看似是維基百科會搜尋到的描述,幾近客觀的存在,但又何嘗不是人云亦云、口耳相傳的一種傳言?吊詭的是,為何強奸員工、拍攝猥褻照片的白老闆對永奎殺人的指控,引來東煥的憤怒,而眾多受訪者對金熙醜容的描述,卻使東煥帶著沉重的心情解開信封,一睹母親的真容?
戲中呈現的兩種傳言,不必僅是隱喻男性的權威,女性的困境,它的涵義不限於此,而意味深長。尤值得注意的是,戲中永奎描述自己當初殺死金熙時,稱自己終於「看清」,大家因為他雕刻精「美」的圖章,才給他最低限度的尊重;大家因為他蒙在鼓裏地娶了「醜」婦,而看不起他(在他看來),令他再度過上屈辱的人生。諷刺的是,這正是他這個盲人真正「盲」的開始。這是一個人言可畏的社會,也許,我們每個人都面對著永奎的處境:假使我們失去了視覺,獲得純粹地感受人、事、物的機會,但我們也隨時活在別人的傳言裏,再次跪奉出我們的雙眸,而親手殺死本屬於自己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