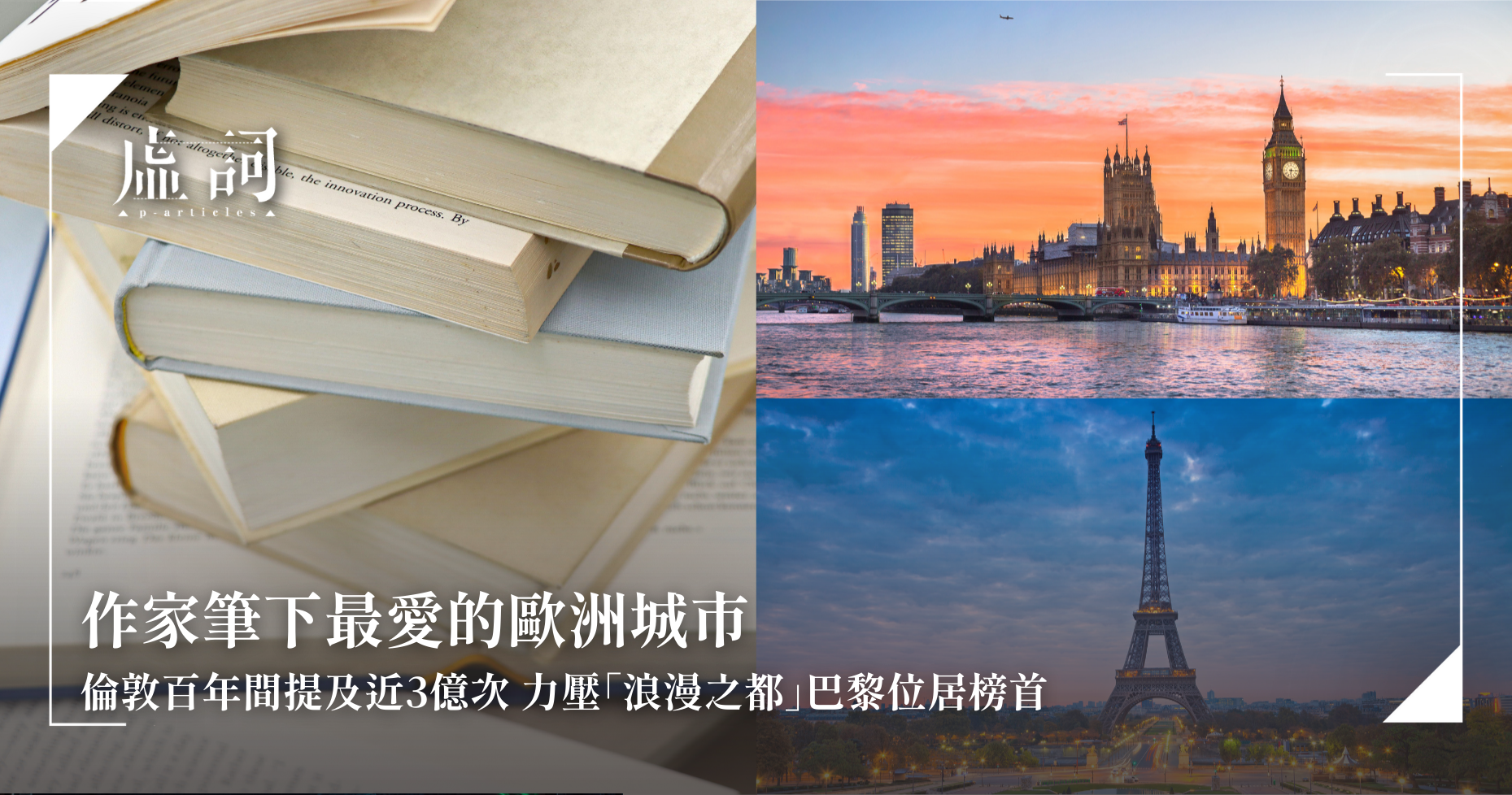作家筆下最愛的歐洲城市 倫敦百年間提及近3億次 力壓「浪漫之都」巴黎位居榜首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11-28
小說不僅是故事的載體,更是引領讀者跨越國界的紙上導遊。許多作品以異國城市為背景,細膩刻劃當地的景觀與氛圍,讓未曾踏足該地的讀者也能在腦海中構建出鮮明的城市印象,完成一次「精神上的旅行」。但你是否好奇過,究竟哪座歐洲城市最常現身於作家的筆下?英國印刷公司 Aura Print 對Google Books超過2500萬冊出版自1920至2019年間小說的進行統計,發現在百年間出版的小說,最常被提及的城市為倫敦,力壓浪漫之都巴黎,而羅馬則位居第三。
在排行榜中,倫敦以驚人的 286,675,501 次提及次數雄踞榜首,被譽為歐洲的「文學首都」。這一數字幾乎是第二名巴黎的三倍。研究指出,倫敦在文學作品中的提及高峰出現在 1960 年代,這反映了當時該城市充滿叛逆能量與文化變革的時代氛圍。
然而,倫敦的文學底蘊遠早於此。若是將 19 世紀的作品納入統計,其數據將更為驚人。從維多利亞時代狄更斯筆下霧氣瀰漫的《苦海孤雛》與《雙城記》,到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系列,乃至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這些作品構建了倫敦深沉而哥德式的基調。進入現代,諸如《BJ 的單身日記》、《真愛挑日子》等作品,則展現了倫敦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多元面貌。
緊隨其後的是巴黎,以 95,290,475 次的提及次數位居第二。這座「浪漫之都」的文學黃金時代落在 1920 年代,當時海明威、史坦因和費茲傑羅等「迷惘的一代」作家流連於左岸的咖啡館與鵝卵石街道,將巴黎視為藝術、愛情與叛逆的象徵。海明威的《流動的饗宴》與《太陽依舊升起》便是該時期的縮影。此外,雨果的《孤星淚》、《鐘樓駝俠》以及大仲馬的《三劍客》等經典名著,早已將巴黎的形象深深烙印在讀者心中。當代文學如《巴黎小書店》等作品,則延續了這座城市的浪漫傳奇。
位居第三名的是羅馬,累積了 48,840,949 次提及。作為「永恆之城」,羅馬的文學魅力源自其厚重的歷史與神話色彩,提及高峰同樣出現在 1920 年代。若研究範圍追溯至更早的世紀,羅馬的排名勢必更高,畢竟莎士比亞的多部劇作皆以此為背景。現代以羅馬為舞台的作品多屬歷史題材,但也不乏《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或改編為電影的《教宗選戰》等現代故事,持續吸引讀者探索這座充滿權力與救贖意象的城市。
排名第四的柏林擁有 37,079,709 次提及,其文學高峰出現在 1940 年代,反映了二戰前後,柏林均成為眾多作家心儀的故事背景。從柏林的《柏林,亞歷山大廣場》到伊薛伍德的《再見,柏林》,記錄著柏林的創傷、分裂與重生,使其成為尋求深刻歷史意義的讀者之首選。
第五名的佛羅倫斯則以 19,414,470 次提及延續其文藝復興的榮光,佛斯特的《窗外有藍天》與丹·布朗的《地獄》皆讓這座城市成為藝術與智性探索的代名詞。
除了前五名,維也納、雅典、都柏林、阿姆斯特丹與布魯塞爾也依序進入前十名榜單。這些城市的文學形象各具特色,例如都柏林因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而不朽;阿姆斯特丹則透過《安妮日記》與《生命中的美好缺憾》展現了歷史的沉重與現代的浪漫交錯;維也納在 1980 年代的提及率上升,展現出其在精神分析文學。
如今,讀者不再滿足於紙上旅行,而是親自前往書中場景朝聖,包括倫敦的貝克街、巴黎的蒙馬特、都柏林的喬伊斯步道、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周邊等等,都成為文學旅行或文學散步的熱門路線,甚至有許多城市的觀光局與出版社合作,推出「海明威路線」、「狄更斯步行團」、「喬伊斯都柏林一日遊」等主題行程,讓書迷親身步行自己讀過的故事。
蘇格蘭作家Alasdair Gray曾言,諸如佛羅倫斯、巴黎和倫敦等城市激發了無數藝術創作,以至於初次造訪的遊客往往不會感到陌生,因為他們早已透過繪畫、小說、歷史書籍和電影遊歷過這些地方。
Aura Print 的數據既量化了歐洲各城市在作家心中的重量,同時亦印證出文字如何超越時空,成為構築城市印象的基石。作家們筆下的細膩描繪,讓讀者在尚未踏上旅途之前,便已在腦海中完成了對異域的探索與想像。當人們終於手持機票親臨現場,踏上倫敦的霧巷或是巴黎的左岸時,心中湧現的往往並非初次見面的陌生與驚奇,而是一種彷彿早已到訪過般的既視感,以及與書中場景久別重逢的熟悉與感動。
小說中提及到歐洲城市次數排名:
- 英國 倫敦 286,765,501次 高峰:1960年代
- 法國 巴黎 95,290,475次 高峰:1920年代
- 意大利 羅馬 48,840,949次 高峰:1920年代
- 德國 柏林 37,079,709次 高峰:1940年代
- 意大利 佛羅倫斯 19,414,470次 高峰:1920年代
- 奧地利 維也納 18,995,437次 高峰:1980年代
- 希臘 雅典 15,118,606次 高峰:1960年代
- 愛爾蘭 都柏林 15,021,998次 高峰:1920年代
- 荷蘭 阿姆斯特丹 12,868,807次 高峰:1990年代
- 比利時 布魯塞爾 10,949,717次 高峰:199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