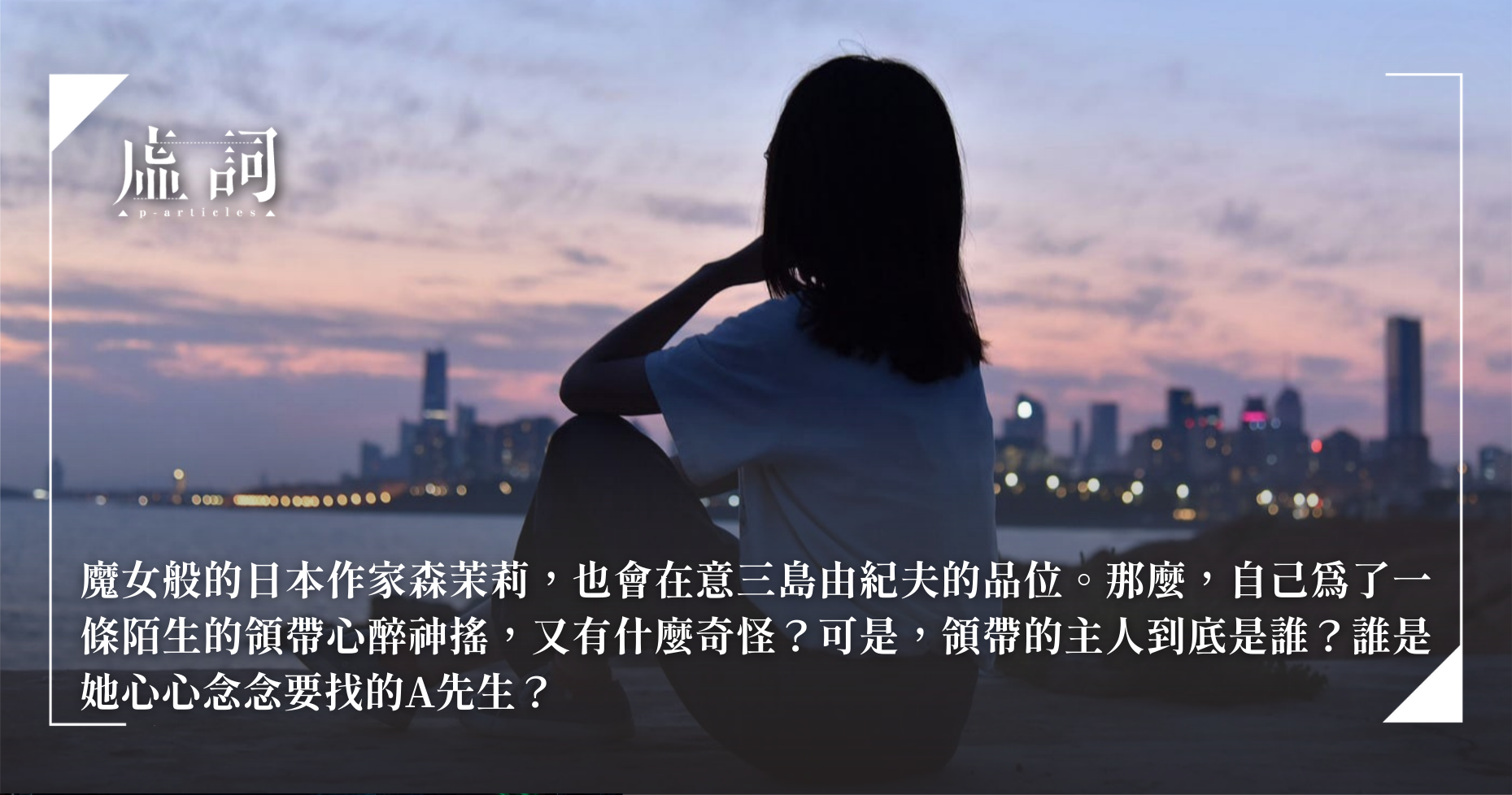A先生的領帶
小說 | by 李曼旎 | 2025-12-05
她習慣孤獨已久,原本懶得戀愛,也不想結婚。女性身體開始發育的十四歲到如今二十四歲,十年間的大部分日子,她對愛情的幻想都寄託在少女漫畫、乙女遊戲,那些虛擬的溫柔情愫,已足夠滿足她對情感的需求。虛擬的男主角可以溫柔地對她說早安、晚安、明天見,一個單身女性所需要的陪伴大抵如此,還有什麼比這更多的呢?高中畢業後一段時間,她從自己的身體出發,朦朧地探索著美,探索著性。美是很純粹的東西,絕大部分時候如此,可以在美術館或公園靜靜找尋。性呢,相比之下可就沒有那麼文雅詩意了。首先被想起的,是充斥在某些社群軟體上的同城交友信——交友,或是比交友更深入的東西——通常是女生列出對於對方的要求,身高長相之類,附上自己一張甜甜自拍照發佈。對這些網路帳號她一度信以為真,想著真的有這麼多二十出頭和她差不多的女孩,可以隨便地對陌生男人交出自己的肉體嗎?後來才知道那些絕大多數是竊用真實女生照片的假帳號。
儘管如此,她還是沉迷上看本不該看的社群軟體。她鍾愛在上面欣賞女性的軀體,軟且白像曼妙的家畜,腰曲線塌陷在一分一秒流逝的時間之中,她看,比絕大多數男變態還看得用力。看多了她便感嘆,這個世界對男人多麼好,發明這些柔膩的肉只為將他們輕盈地包裹。
與此同時,她對色情暴力的閾值也一直提高。玩一款遊戲《The Price of Flesh》,遊戲裡的可怖男主角低笑著,形容女主角的身體,You are so……
對話在這裡停住。會是什麼呢,beautiful嗎?她喜歡這個英文單詞,那麼悠揚,那麼……像蝴蝶。對話框翻到下一頁。是「unbroken」。這個詞,讓她當時,悚然心驚。
接下來遊戲女主角該遭受到暴力的虐待,身體受損、殘缺了。而屏幕外的她呢,何嘗不是在遭受某種無形的摧殘?但至少現在,儘管一直放任自棄不在乎對身體的後天修飾,對於一塊肉來說,她仍是年輕的、完美的、不曾破碎的。那陣時,她的筆記本夾著時尚雜誌女性模特兒的剪報,卻不是為了模仿她們的穿搭,僅僅是想要收藏,那些女體姿容優雅,如此自信地存在於世,服裝鏤空之處皮膚光裸。她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竟能從這些凌亂的女性氣質碎片中獲得慰藉。
如果有人問起她的初戀,她會微笑不語,偶然的契機才提起,大學三年級去東京交換,校園的銀杏樹下她「愛」上的那個女孩——如果想到就會幸福,覺得她比世上的一切都重要這種幻覺,可以稱作愛的話。短暫的幾個月她們一起看書,一起去聽交響樂團的演出,一起在千鳥淵划船,陽光碎進她們的眼睛,輕微的刺癢與疼。莉子說喜歡泉鏡花的小說,說那是現實以外的另一個世界,她想,世界之外還有一個世界嗎?船到中央,莉子忽然問她:「妳有談過戀愛嗎?」她一時語塞,搖了搖頭。莉子笑了笑說:「我也是。一直沒有很確定什麼才算是戀愛。」
她渴望與她有更深入的聊天,可她太緊張了,不知是說母語之外的語言讓她緊張,還是其實是看見那個女孩才心跳加快?某個假日晚上,兩人一起窩在莉子家看寺山修司的電影,那是一部實驗性強烈的作品,濃烈的色彩挾持七〇年代的風,呼呼向她們吹來。她們裹著同一條毯子,她的頭微微靠在莉子的肩上,莉子沒有躲避。「很冷嗎?是不是應該把冷氣關小一點?」她聽見莉子問。「沒有很……冷。」她說。其實她想說的是,有妳在就不會冷,可她說不出來。或許她一輩子都說不出這麼輕佻甜蜜的話,她太容易緊張了。好不容易克服刻入肉裡的緊張感,已來到她要離開東京的時間。雖說往後隨時可以再來,可是,有見她的理由嗎?她不知道她對她的笑,是她真的讓她快樂,還是社交中應有的禮貌。
莉子,早上好。莉子,晚安。莉子,明天見。莉子,再見。
這就是目前來說,她最接近戀愛的一種關係,她知道永遠不會真的是。往後跟莉子偶爾聯絡,匯報近況,她卻總覺得失落。曾經親近到餵彼此吃麵包上的奶油,把彼此指甲塗成糖果顏色的兩個,現在卻只能是聊天室裡一來一回的可愛貼圖,她怎麼能甘心?莉子又是怎麼想的呢?有時候不得不承認,她其實不太懂莉子,就像莉子也不太懂她。離開東京前幾天,她們最後一次去看演出,是一場弦樂四重奏,她聽不太懂,莉子卻沉浸在音符中相當專心。她望著莉子的側顔,幾顆小巧的痣排列在鼻側、臉頰,像若有若無的星子,真想說些什麼,但她記得在演奏廳要保持沉默。她也就這樣一直沉默下去。
直到如今,她過著並不需要戀愛對象的生活。結束在東京交換的學程,大學畢業忙著讀研究所,研究所畢業要找工作,年輕女子無心戀愛,在現今這個社會不但可以被容忍,甚至是被鼓勵的。與此同時,女性不再能以家庭為由逃避職場,她在投遞工作簡歷的循環間隙,有時會胡思亂想,女性地位的提高是不是一個社會為了增加勞動力的騙局?這樣想太沒有獨立女性的精神了,她一個取得碩士學位的知識女性若持這種懷疑,會被同伴恥笑的。她用力搖搖頭,把這種思想摒棄在腦外。身邊戀愛過的朋友鼓勵她打開心扉,也該試試看愛情的美妙,她不覺得自己其實有關上了些什麼,可還是答應了一位過去同學的看展邀約。是關於都市、工人的攝影展,拍攝建築工地上膚色如銅,沾滿泥沙瓦礫的男子,那是一種屬於男人的肉體美,她站在相框前,看他們裸露的肌肉筋骨,感到自己正在一點點被剝離。約會的男子說:「看上去很有力量吧?」她點點頭,嗯嗯。
他們再也沒有見過面。
很多人都說,現今單身女子的性,不一定要倚賴男性完成,她和同伴逛過成人用品市場,一排排假陽具亂葬堆般陳列在那裡,當然也少不了手銬、皮鞭、項圈、皮拍之類的特殊道具,性在這裡已然毫無神祕感可言。她們看了幾個兔女郎模型,黑色深紅色兔耳撩撥男人心,又摸了好幾隻硅膠胸部,軟軟涼涼。甚至在一個轉角處,還放著一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塑像,著他經典的藍色西裝,嘴唇鼓起來,像是要發表演講。意氣風發樣卻是和成套懸掛起來的蕾絲性感內衣堆在一起,哪個廠商敢這麼搞怪?她覺得好玩,讓同伴替她和總統大人合影,就在這個曖昧不明的場合。回去看照片,塑像雖然風格滑稽,但總統最經典的藍西裝上一條紅領帶,卻是嚴嚴整整地繫著。
有一種奇異的情緒浮上她心頭。
哪怕是成人市場的總統先生,也好好穿著西裝、戴著領帶呢。
她從未學會繫領帶。唯一一次需要用到領帶的場合,是拍大學畢業照,連同學士袍一起發下了一條,戴在裡面,整體形象看起來更正式。她卻不知道怎麼把它束成漂亮的形狀,就連懶人打法都磕磕絆絆,任由它在襯衫前垂下。畢業合照上她也是那麼不合時宜,和同學們硬生生擠在一起,襯衫上的領帶歪歪扭扭。常在影視劇看到妻子替丈夫打領帶的溫馨情景,或是女生替剛剛有幾分大人樣、第一次穿西裝的男生繫領帶,彼此都有幾分羞澀。那好像是一種宣告著親密的儀式,女人學會如何照料男人的溫馨場景,她暗自想,這種情形該永遠都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會否是她太笨拙了呢?
也再度試過和男生約會,不再是同學,而是在網路社群。約會軟體上跟著感覺尋找。新新世代的男生已摒棄了上世代把粗野當作男人味的不良習慣,有的比她打扮得還精緻,讓她有些懷疑自己。但男人畢竟是男人,她還是沒有辦法適應,虛擬作品以外真實的男性,比她更粗碩的骨架,星星點點的鬍茬。
這就是佔據藍色星球上全部人口數幾乎百分之五十的物種。
會否她根本不喜歡男人?否則,她也不會在過去的東京,愛上一個女孩。
她看了大量同性題材的電影、文學作品,卻無法把作品中的女女情侶同莉子與自己聯繫起來。但她堅信自己對莉子的情感,太險峻太過真實。她是愛女生,還是只愛莉子?上一次給莉子傳LINE,那邊悠悠晃晃浮現已讀,莉子傳來一張合照。莉子戀愛了,男友是白皙清秀型。想到這裡,她不由得暗笑:是幾時她也學會這樣物化男人了?往前只有男人會把女人按照外表分類:大胸無腦型、文靜清秀型、甜美活潑型……
現世代不同了,男人也要學會取悅女人。男性舞團、健身教練、八塊腹肌、硬朗線條,不都是為了取悅女性觀衆嗎?雖説對真實的男性軀體仍有陌生感,她倒是看得非常開心,好像懂得了一點男人的樂趣。從古至今,都是女人在為男人表演呵。
她的年齡又增長了些,二十五歲以後的日子就像水一樣流去。她從研究所畢業,廣投履歷,最後開始了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像所有年輕上班族一樣擁有一張識別證、一張辦公桌、筆電、一個屬於她的郵箱。還有,一條日日夜夜重複不變的捷運路線。二十五歲的單身女子,聽上去尚很年輕,但二十六、二十七歲呢?她發現自己在朋友間,正在扮演一種頗尷尬的角色。女伴們不再和她一起逛成人市場,也不再帶她健身帶她看表演。工作和結婚——不妨說正式點,叫事業與家庭好——已經佔據了她們絕大多數時間。大學同學、研究所同學中唯獨她依舊獨身,社會開始製造種種女人恨嫁的焦慮。她不時懷念起在日本當交換生的時日,如今她的日語已經好到如同母語,可以跟莉子談論任何話題。上世紀地下戲劇、泉鏡花的文學還是友川カズキ的歌曲,但是,已經不是二十出頭時的心情了。
二十多歲時,她的人生充斥著幻覺。殘酷的、不現實的,幻覺。
這種幻覺一直發作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封來自東京的邀請函。這是莉子寄來的信,淺粉色,她熟悉的頗俏皮的橢圓筆畫,寫著:「希望妳來見證我的幸福。」好消息是,莉子記得她,說永遠不會忘記她。壞消息是,莉子結婚了……不,這也是好消息才對。她用掉本就寥寥無幾的假期,跑去東京參加莉子的婚禮,從成田機場走出去,一切都倒轉回她二十歲的年齡。東京如舊,一點未曾改變,就像她從未離開又或是從未來過,而她卻只是來參加一場她不是主角的婚禮。這讓她有些鬱悶,東京其實不需要她,就像莉子不需要她一樣。
無論如何,她還是在表參道附近種滿白色紫陽花的洋館舉著香檳杯,假裝很豪邁的樣子一口飲下,一點都不優雅。新娘挽著父親的手進場,笑容完美無缺,她被埋在人群後,看見莉子上揚的眼角,她記得,幾年前的莉子分明是垂眼。她也看見新郎,很聰明的長相,和莉子宛若一對璧人。與新郎新娘合影的照片,她笑得齜牙咧嘴,一點都不優雅。該怎麼優雅地面對一切的發生呢,這一點,莉子從二十歲的時候就做得那麼好,那麼有禮貌……連數年前對她說出「我對你的感情,似乎已經逾越了禮貌的範圍」這種話時的樣子,也那麼有禮貌……
她決定忘記莉子——莉子知道了一定會說,好遺憾——可也只是遺憾而已,莉子是多麼狡猾的人。她離開了洋館,剩下的幾天時間去霓虹燈旁的街角咖啡廳,在下北澤逛二手市集,在那邊她看到了一條非常非常漂亮的領帶,是她少女時期喜歡的Jean Paul GAULTIER牌子。領帶底色是黑色的,不是黯淡死去無神的黑色,是某種熾熱的黑,類似隕石寂滅後留下的顏色。上面繡著的,是紫色的龍與花纏繞在一起的圖案。
這是一條男士領帶。
但身為女人,並且剛剛從對另一位女人的愛情中緩過神來的她,還是毫不猶豫地將它買下,偷偷嗅聞上面或許有前一位主人殘留的男香。領帶的標籤上粗糙凌亂地,寫著一個A。買下這條領帶,似乎反倒成了她這次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到底是什麼樣的男人才會系這樣的領帶?
當然不是商務人士,一條繡花領帶對他們來說太亂太花哨,不夠精幹可靠。當然也不是總統先生,不是電視主播,他們的穿衣搭配甚至有專業的團隊安排,已無餘地隨心所欲安插下一條莫名其妙的舊領帶……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親身試驗一種方法。她決定找一個男人,哪怕是為了這條領帶。
僅僅是為了這條領帶,A先生的領帶。
甚至開始填起這樣的問卷:
您今年幾歲?(請填數字)您的擇偶意願強烈嗎?(請填是或否)您的擇偶標準?(請簡略填寫)
一晃眼竟然接近三十歲的她,仍然不願把尋找一位異性長久相處的過程稱做是「擇偶」,討厭其中隱含的,人必須配對成偶不可單獨放置的含義。但既然要把所有遐想都簡略填寫在一片空白,那麼答案,就變得非常簡單了:一位可以配得上那條領帶的男人。
她開始了比之前更頻繁、更有目的性的約會。想當然地,先從古著愛好者開始尋覓。她約會過好幾位著花襯衫蓄長髮的男生,他們身上總是有上世紀的香水味,將身體埋進那種氣味中讓她安心。但她總覺得他們的氣質有所出入,不能匹配那條在漆黑之中流光溢彩的領帶。
那,搖滾樂手和地下詩人呢?這其實是她讀大學時最想從事的職業,儘管也不知道算不算職業。總覺得職業就該意味著有穩定的收入穩定的年假,規定的工作日和格子間,不會出錯的。所謂的樂手和詩人,看起來更像流浪漢。不是循規蹈矩就是窮困潦倒,她總有一種感覺,這個社會要將他們這些人中間最最傑出最最有詩意的人集中起來毀掉。
無論是最年輕、最完美、不曾破碎的身體,還是最年輕、最完美、不曾破碎的頭腦。
還是見一些自視為普通人的普通男人。後來她相約的男生,聊天話題不再集中於小眾愛好,個個都告訴她,你們這個年齡的女人應當現實一點。他們說,女人才愛幻想,而男人要一些別的東西。男人就不愛幻想嗎?她不服氣,男人幻想起來,要比誰都可怕……所有歷史書、文學書上講述的「他」的故事,早已說明了這一點……
在東京上學時,她聽莉子説了過去的日本學運,還有發生在另一些國家的事情,多遙遠多陌生。莉子那時候講述那些故事,眼睛幾乎噙滿熱淚,令她也深受感動,可後來試探性地提起,莉子竟像是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那般。不過,陌生的故事中間,也有她可以有共鳴的内容。比如在青年莉子的推薦下讀羅莎盧森堡的獄中書信,看到盧森堡寫評價某位男性:「只有那條領帶,上面佈滿了白色豆子形狀的斑點,這真的很惹眼!——這樣一條領帶可以成為離婚的理由。是的,是的,我知道——女人們——即使有著最高貴的靈魂,她們首先注意的還是領帶……」
啊,哪怕是讓她不敢設想的女革命家,也曾為了一條領帶發牢騷。魔女般的日本作家森茉莉,也會在意三島由紀夫的品位。那麼,自己為了一條陌生的領帶心醉神搖,又有什麼奇怪?
可是,領帶的主人到底是誰?誰是她心心念念要找的A先生?
如今是她花錢將領帶買下。那已經是她自己的領帶了……
洗浴過後,她赤身裸體,久久凝視鏡子裡的自己,將紫色龍與花的領帶纏成圈,套在自己的脖頸上。死成漩渦圖形的龍複又甦醒過來,是那樣溫柔地,吸吮著她的皮膚。
一切都過於完美。一條失去原主的男士領帶,竟與她的裸體如此契合,她幻想自己是在和那位A先生親吻、愛撫,在一切步向破碎之前。
她拍下照片,將一塊除卻脖頸有勒痕外,無瑕的、美麗的肉發佈在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