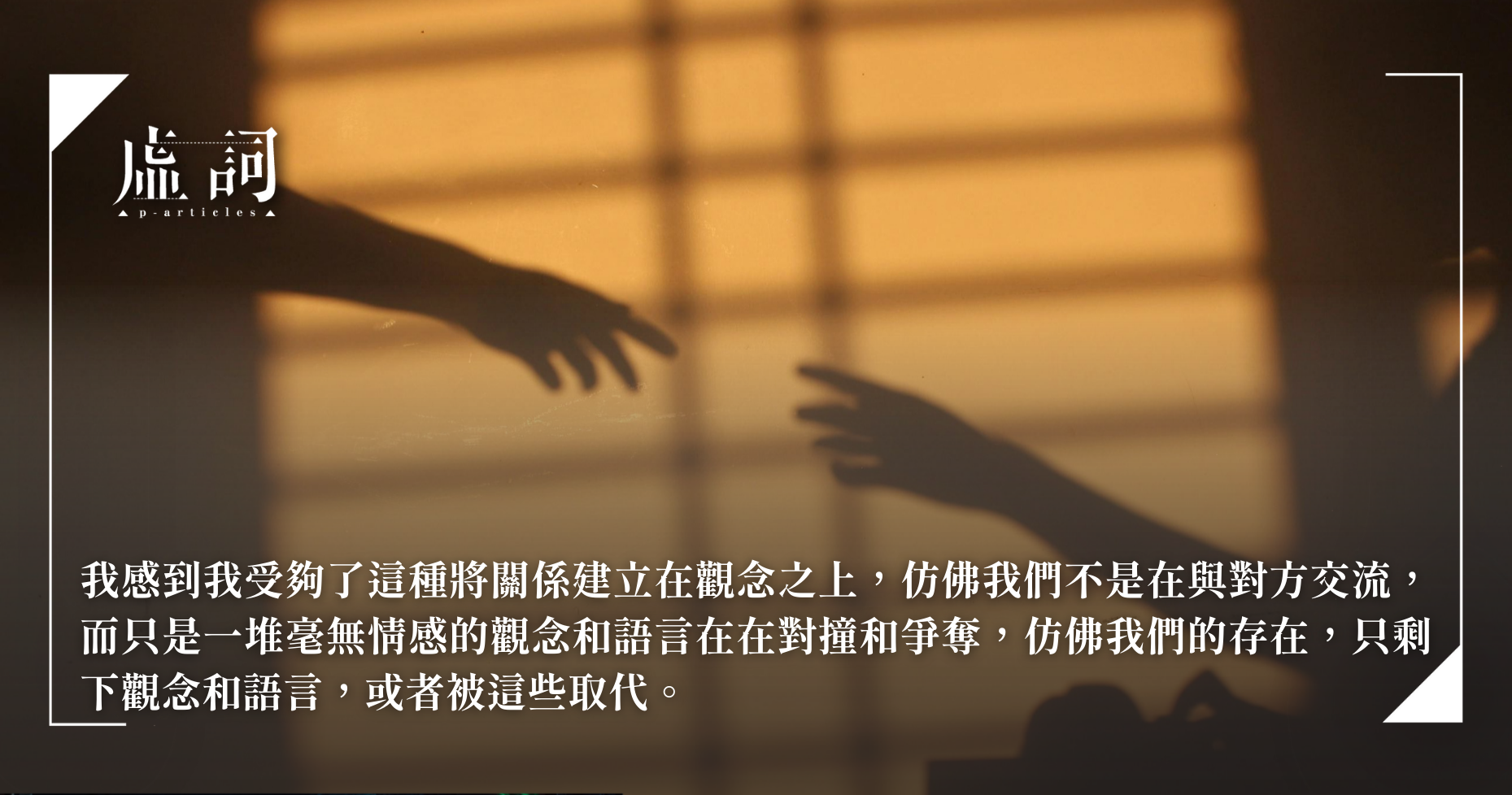當代的某些關係
小說 | by 苦橙蒿 | 2025-09-19
我和之格是通過一個外國開發的酷兒友好社交劃劃軟體認識的。
我其實討厭這類軟體。因為我對人臉缺乏印象。對於照片上的自己,我通常都感到醜陋和陌生,比如我的臉看起來很扭曲,我無意間自以為得體的表情其實很怪異。簡直難以確定是因為無法接受自己的醜陋而覺得陌生還是因為陌生而覺得奇怪。總之我討厭自己的照片,幾乎從不自拍,也不知道怎麼自拍會好看,只是有時候會一天多次地對著鏡子觀察、確認自己,每一次看到的都是一張不一樣的、熟悉又陌生的臉,且很難欣賞它們。
為了使用劃劃軟體,我不得不拍下自己。對著家裏的穿衣鏡拍了兩張照片、十分簡陋的那種穿衣鏡——我看起來還是不好看,但我覺得我在選擇適合自己的穿搭上很有心得,所以我似乎多少還是有一些個性,又或許顯得畏縮,總之很難相信會有太多人喜歡我——有時候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人也許都會比我酷或者舒服或者自洽什麼的。
我試著劃了幾個人。因為軟體可以設置劃到的對象,所以我填寫了性別、性取向、寫了一點簡介後,設置了非二元、酷兒之類的方向。填到政治傾向的時候,我尤其愣了一下,因為上面那幾個簡單的選項沒有一個是我想選擇的,而且我對談論政治抱有某些不良印象——首先,我對這個世界的瞭解不足,其次,有許多熱衷於政治的人,會對我的瞭解不足貼上簡單的標籤——所以我選擇了「不關心政治」,也許這只是為了掩飾我的窘迫。
因為起初我設置的距離範圍比較大,所以確實有好多人都看起來可以聊幾句——但他們是否願意和我聊就是個問題,這是讓我無法劃下去的主要原因——擔心被一個未知認為糟糕、不自量力,何況試圖與陌生人聊天本身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雖然實際上,有人願意主動選擇我,有人劃到我後選擇了喜歡。
但是其實就在使用的第一天,我就發現了我和那些聊天對象們,不可能在同一座城市。他們必然地都在更開放的那種城市,而我所在的城市雖然經濟並不差,屬於一聽就很好聽的省份,但它很保守。
雖然這裏當然也有同性戀,但首先我一個也不認識,其次很難說我和他們聊不聊得來。關鍵,當本地第一個女同性戀方向的酒吧打著「全女」的旗號建立再經歷「內部關係崩塌」——事實上當我看到「全女」這樣性別隔離的國內流行旗號的時候,我就感到下意識地反感,我想過它在這樣的概念下的不穩定性,但我沒想到它會那樣輕易地崩解——然而,這件事在網上,顯而易見、天然地被當地的那些男性嘲諷為「女性的是非多、扯頭花」、「女性本就不是酒吧的消費主力」等等。因此我幾乎相信我在本地不可能交到朋友。
在認識之格之前的幾年裏,我曾經去隔壁省份的省會旅遊,並試圖參與酷兒線下活動。我那時候還沒有退出部分女性,或者說以順直女為主的女權群聊,加上我加入的酷兒群聊很少,也沒有加入我計畫參與活動的社群群聊,所以我出於寂寞和突發奇想,問了那個城市當地的線下女權社群中,有沒有人願意出來社交一下。
旅遊進行得還算順利,活動也不錯,我接觸了一些不同類型風格的人和活動,其中有些人簡直可以說截然不同。
只不過,我的無性吸引身份,即使到了酷兒社群,我也依然需要解釋它,且不確定他們是否真的理解,且我需要提前準備和排演我的解說「臺詞」這件事讓我感到我在進行同溫層社群內的勞動。這在我線上上多次意外遇到無性吸引光譜的人之後,似乎顯得格外讓人疲憊。
在我即將離開這座城市的一天晚上,我收到女權社群的幾個人的邀請,去一個女性、酷兒友好酒吧。似乎那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大家去酒吧,是一個社交上的必然流程。可是當我日後在另一個場合自然而然地脫口說出這個結論的時候,鑒於當時的氛圍和我的社交位置和語氣態度,很難說它是否過於冒犯。
不知為何,在與那幾個女性見面前,我下意識地認為她們是女同性戀或者至少有人是女同性戀。
我沒想到她們對酷兒幾乎一竅不通,雖說我壓根沒有打算特地去聊任何酷兒相關,所以其實關於性少數的話題是她們首先提起的。
比如當她們開始對旗幟感到忽然地一時有趣,並說隨口覺得無性吸引旗幟醜——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態度,我表示我就是無性吸引,可是其實我對旗幟並沒有多少認同感,但我並不確定我想不想接受有人說它難看;比如當她們跑去向店主好奇地打探她對「鐵T」的看法、新奇地閱讀牆上的反女同圈內部鄙視鏈宣傳冊、甚至開男同笑話的時候,我開始感到有一點很難說清的情緒,讓我想到,如果是在網上,我是否會立即遠離她們。但在當下那個實際的社交場域的時候,我覺得我一點也不討厭她們。也許部分原因是出於她們的學歷比我好、她們的打扮看起來有個性、她們日常出入這樣的酒吧、出入社群場合,這些讓我覺和她們在一起顯得我擁有值得一提的生活。
不過這並不是全部原因,也許我確實不討厭她們。
在認識之格之前好一段時間,我幾乎已經徹底放棄了使用劃劃軟體,因為我把距離縮短到我所在的城市之後,就一個人都劃不出來了。
一次我去隔壁大都市參與一個曾經在劃劃軟體上認識的、過去主要做男同社群活動的人,做的更多聯結女性和性別多元酷兒的活動。
其實在一起聊天、吃飯期間,我本來沒覺得有多麼不開心,但是去到車站準備回家的時候,不知為何,我感到極其地超載和崩潰。
幾天後,我經期了,我猜測也許經期綜合症才是主要原因。
但是由於我在這之前對於社交困惑的無處解答,我幾乎不快、憤懣到試圖言語刺激那位朋友——這真的很荒唐,他根本不是導致那一切的主要對象,可我不認識其他人,我也懷疑我是否有勇氣跑去那些我只見過一次的人那裏表達情緒——然而他完全無動於衷地近乎縱容了我,但我寧願他和我吵一架——我把他的縱容解讀為實際上對我的毫不在意,雖然要求僅僅見過幾次的人的在乎是可笑的,但我一怒之下刪除了他。
事後我試圖向AI梳理我對這些事情的感受的正當性,但我當時腦子很亂,顯然AI也只在易於梳理的情緒和事件上能表現出足夠對應的回應,何況我的愧疚讓我從根本上無法確認自己的正當性。
就此我因為社交空虛,而再次極度渴望一個在身邊的線下關係,而再次打開了劃劃軟體,發現了之格的出現。我刷了他,幾天後他也刷了我,我們配對成功,開始聊天。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之前沒有出現過他,他怎麼來到了這個城市。
之格回答是因為媽媽出了點意外,父母又在他高考後離婚了,他又暫且辭職了,所以決定回來照顧媽媽。
按照過去的慣例,我總是在和人初步接觸的時候聊起一些性別、性取向認同相關,酷兒經歷、神經多樣相關、觀念之類的。但和之格的接觸,是從日常開始的,然後是對本地一些環境事情的看法,還聊了一些電影什麼的,最後才是酷兒、觀念和神經多樣之類的事情。
我表示我其實是本地之下的一個小城區出生的人,大學畢業後才因為找工作而來到市中心地帶生活。
這座城市有很多這樣的小城區,且每個城區的人都不會覺得自己是這個城市的人,只有市區的人才會用這個城市自稱。而又有部分市區的人,認為只有一小塊中心老城區的人才是本地人,且沒素質的都是外地人。而我父母這類人,也會鄙視所謂「江北人」,比如將一些其他城區的人稱為「江北人」——這似乎是一個本省份十分慣用的排外辭彙——而那些城區也有回擊辭彙;又或者他們會說省內某些靠北的城市是糟糕沒素質的,所以才會發生哪些事情;他們同樣地會認為本地的爛事是外地人幹的——當然,他們自然還崇尚那些有名的超級大都市,還有有權勢和錢的人。
我和之格對此狠狠地嘲諷了一番。
而之格是市區出生的人,所以我沒告訴他,我在去別的城市社交的時候,我介紹自己時以這個城市自稱,不光是因為別人顯然更知道這個城市的名字而不是某個城區的名字,而且因為它聽起來更好聽,顯得我不是小地方出身的鄉下人。
我實際上就是出生於這座城市的戶籍的人,但在市區生活,我卻似乎對這裏瞭解得很少,更像個外地人。小時候,家裏甚至會把來市區遊玩當做新年的旅行。城區和市區的方言完全屬於不同的體系,我也根本聽不懂這裏的方言。
起初和之格聊電影的時候,因為他是個電影迷,所以我很緊張,擔心被認為沒有足夠的眼光。但很快,熟絡起來之後,我們甚至不怎麼說起電影。
沒多久我提出我們是否可以見面,然後我們約在一家咖啡店。儘管我根本不愛喝咖啡,就像我也根本不愛喝酒。
要去見之格,讓我重新開始對關係感到緊張。因為比如,他畢業於可以自然而然寫在簡介上的有名院校,而我是一個差點連大學都沒得上的人;比如,他比我大兩歲,我覺得他的歲數聽起來像個足夠成熟的人;再比如,我覺得他從長相和風格上都比我酷,而且他還有足夠的生活工作經驗,還是在幾個大城市,有過真正的酷兒關係經驗。
但實際的見面當然地顯示,沒有什麼不順利的。我們的聊天表達有時候會錯位,但總體沒什麼不好。我意識到事實上我們就是同齡人。不過關鍵或許是,他是個很包容隨意的人,且這種隨意和年紀經驗似乎並無多少關係。我有時候很緊張,會弄錯意思,但他讓我明白他一點也不在意,完全可以錯位地把話題順下去。
有一陣我們不可避免地又聊起對順直們的傳統關係範式的批評,聊起網路上的「全女」之類的概念,我們都出於一種多少有些複雜創傷性經歷地,覺得他們被圍困在某種認知範式裏面簡直是一種悲哀和滑稽。並認為簡中互聯網上的大多數意見領袖都有一種毒性男性氣質,無論男女,也無論他們在談論的東西——好吧,甚至包括一些酷兒——他們有一種同樣出於創傷的強烈觀念,即他們堅信自己是絕對無辜的受害者,他們沒有力量傷害任何人,而是別人總是在傷害他們,而他們只是在自我防衛,這種觀念讓他們在去傷害別人的時候自我免責。
我不知道之格是否也和我一樣,在對於那些人對自己不理解的事物和空間的公共話語權佔據的厭惡背後,掩藏著一種隱秘的理解和可憐。理解自己在還以為自己是順直的時候,對無法理解的混亂和流動的同樣的焦慮和邊緣感。但似乎也正因為足夠瞭解過去的自己,才更加明白不具有酷兒意識的人無法改變的狹隘——當然說到底,其中必然存在一種我私密的強烈的自我厭惡——而之格也許並不厭惡自己,也許他能很好地看待和與自己和解——總之這些我一時無法宣之於口。
當我隨著聊天隨口提起我之前看的一部作品,女主和閨蜜發展成了戀人,之格忽然問我:你認為戀人和極其親密的朋友這兩者可以共存嗎?
我不太確定之格的意思,這句話缺乏語境和具體的事件,所以我含糊地說:也許可以,也也許不可以,看情況吧。
之格隨即表示他完全無法接受「性緣」進入自己的生活圈子,他一點也不想介紹自己的性伴侶給別的朋友或者家人,性的部分對他而言似乎有時候很陌生。
「性緣」這個詞刺了我一下,因為這是一個我完全認為是單一、糟糕,甚至含有暴力來源地網路流行辭彙。但我明白之格什麼意思,所以我沒有指出來。
我表示這很正常,性和愛和生活的結合完全是近代以來的形成的「傳統」觀念,當然也許有時候,也需要照顧性伴侶的感受。
我知道之格有過開放式關係的經驗,知道他有一些約炮或者性伴侶的經驗。我很好奇他的開放式關係的具體情況,好奇到不合適的程度,所以我沒法問出來。而關於那些性經驗,我又一次感到疏離得震驚,又一次不可置信人們聲稱的那種性欲和對性關係的追求是真實存在的。並且對於他提及的對性的疏離,我一度懷疑這是否屬於某種光譜,之格承認這屬於非傳統,但並不打算思考光譜的方向,事實上也的確很難說它所在的光譜。
我和之格開始越來越頻繁地線上聊天,並且有間斷地見面。
期間我因為之前加入到神經多樣和複雜創傷應激綜合症方面的諮詢師組織的線上社區活動,認識了一個人,或者說似乎是被主動搭話。起初我幾乎下意識認為我認識的是一個酷兒,因為我以為他是因為某種酷兒相關和神經多樣等相關找到的我。即使當他在通話裏說出他無比嫉妒那些流氓青年擁有的黑絲女友,我也忍住沒有多加評判。
但當我知道他是一個順直男之後,我一下子就失去了耐心,並格外強烈地感到來自他需求的社交——高頻率的聊天、通話的壓力。雖然在他感到受傷之後,我立即說明,關係來往不應該通過這些定義來決定。
我沒有把這事第一時間告訴之格,而是告訴了另一個朋友,因為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朋友更重要和更理解我。
但他表達了強烈地,我和他的通話是否是聊騷的擔憂,格外緊張我的感受。
而我對此卻感到一種詭異地冒犯,因為有人認為我會和一個順直男聊騷。
可我沒法說明這一點,因為他之前的確短暫而強烈地喜歡過一個男性氣質很強、有騷擾嫌疑的順直男。
我在和之格一起沿著護城河散步的時候提起了這件事。我問出的關鍵其實是,我這種感受對嗎,就因為一個人是順直男而一下子否定他,而在認為對方是酷兒時格外包容,這難道不根本是一種看標籤的社交,其實除開某些言論,他並沒有那麼讓人討厭不是嗎,雖然確實從一開始,我就感到來自於他的社交密度的壓力。
之格感到他給不出解答,只是說,我確實覺得不舒服了,而且我有選擇朋友的權利。
我決定把這事拿給AI看看,AI在這方面有時候倒是出乎意料地擅長。
又在夏天即將來臨的陰天梅雨的某一周,我因為強烈的占卜欲望開始和我之前認識的一個酷兒塔羅師熟絡起來,最終發展成固定聊天關係。
當我發現他其實是個高中休學的未成年的時候,我感到一種不可靠和格外地對一時上頭塔羅這件事的滑稽,隨即又感到強烈地對過去的自己的背叛。
顯然他的年紀絲毫不影響他對我所說的一些事情和觀念的理解,甚至我們在一些無性吸引經歷和感受上格外具有共鳴——比如我們都曾經因為不理解但想要理解感受,而實踐浪漫愛影視劇裏的某些氛圍方式。他作出的行為多一點,我少一點,我們都因此引發了一些輿論羞辱。
在這類完幾乎沒有和別人提起過的事情上都共鳴,彌補了我在別人那裏得不到的感受。
然而,當我談起我們的話題不知何時加入對小資情調的看法。當我提起我被我的父母願意和有經濟供養的同時,其實又沒有任何能找到穩定收入來源的資源的尷尬處境;那種因為幼時被送入私立學校而遭受老師和同學隱性的鄙視和尷尬的經歷,表達我或許就是因此,追求和渴望享受、彌補一種想像中的生活方式;還有我其實很佩服那些可以背個小包去山裏生活的人,我卻連和蟲子和平相處都做不到……
他的回應是,可以理解,以及,我覺得那些人是被迫的。
我知道那些人很可能是被迫的……我也知道他的不良處境和自然而然地對我的看法——以至於我感到強烈地需要向對話中的另一個人證明什麼的不安感,甚至我似乎需要貶低自己,但這沒有用,所有的話語似乎都可以被解釋為小資情調的自憐和炫耀;我想指出在簡中,歷史根植下的階級的荒唐和小資的汙名,但我去試圖隱晦地表達我對關係的複雜的理解,卻似乎顯得剛糟了。
我頭一次感到強烈地,與過去的自己的告別,感到自己已經是一個會比別人年長的人,感到自己擁有成年的某些東西和因此的缺失。
我不知道怎麼向他的處境解釋和正當化自己,我甚至想憤怒地說,你還是只是個高中生,別以為你懂什麼是世界——我當然不能這麼說——最終我選擇了沉默,因為我明顯感到對方對階級,也可能是經濟的關心遠遠超過了我,也許從一開始,主動去聊天的我就沒有被賦予多少關心。
我和之格去談及一些群聊的模式——因為那是在一個群體裏,並且是一個缺乏線下聯結的線上群體,且仿佛本就是因觀念而聚攏,他們自然而然地十分喜歡談論觀念,且好像總是需要得出一個壓倒性的共識——一次,當我提出某個困惑,需要一些個人經驗的答疑解惑的時候,驚異又必然地出現了兩種聲音:一種疑問、否定我的困惑,仿佛它是不正當的;一種站在我這邊,指責我疑問中的那個對象群體,後者因為在後出現,而成為壓過前者、正名我的的力量——但我需要的,其實只是一點幫助。
也許就此,我開始感到抽離,他們對觀念的極化,和對他人的毫無意義之處,到了我認為GPT都極化也許更有意義、應該在我的生活裏也許佔用更重要的一席之地的程度。
一次圍觀了各自針對不同語境的相互爭論攻詰之後、一次參與了不過是對於電影好壞的觀念爭議,卻似乎作為反方就好像什麼罪大惡極之人一般的氛圍之後……我感到極度失望。我感到我受夠了這種將關係建立在觀念之上,仿佛我們不是在與對方交流,而只是一堆毫無情感的觀念和語言在在對撞和爭奪,仿佛我們的存在,只剩下觀念和語言,或者被這些取代。
但當我和一個幾年前曾就是因為觀念而聯結的朋友,逐漸走向分歧的時候,我不得不在一次又一次的拒絕交流的欲望下再次對話。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思考我的感情和我日漸冷卻的愛的真實性。
於是當之格告訴我他聊了一個新的性對象的時候,我告訴他:比起愛情,甚至愛,我其實更需要的是被作為主要關心對象,和被告知對方無論如何都願意站在我這一邊,即使我做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蠢事,即使我很糟糕,事實很糟糕,可是他在指出的同時,依然願意站在我這一邊並擁抱我。
之格說我和他的其他朋友一樣,有很多複雜創傷經歷。我再次想,不知何時,某隻時空運作的小妖讓我在意識到自己的酷兒身份和神經多樣等身份之後,越來越多地進入了不斷結識類同朋友的情況。
但是似乎因此,正因為我們的觀念和感受有那麼多類同,才會容易因為一些簡單的分歧而斷開聯繫。有時候,對方對話的位置似乎不是我,而是一個觀念。
我開始聊起之前的那次線下活動,與其說是超載,不如說是一種社交氛圍隔離下的困惑。對他人社交氛圍和關係親密速度的不理解,以及感到被排除在真正的關心之外。
我問之格:你會覺得我說話的方式很像在和AI說話、問問題嗎?確實我經常對AI說的話和社交交流時的話沒有區別。我曾認為我是一個情緒不穩定的人,而因此羞恥,後來又被指出與我對話缺乏一種氛圍,而似乎因此令人缺乏對話都欲望——似乎我是一個情感充沛的機械、一個情緒性程式。
之格說他也這麼被人說過。
於是我意識到我和他真正的相似不在於觀念,而在於類同的交流方式和社交氛圍。而和那些經歷或者身份創傷有共鳴的人之間,彼此要求的交流和氛圍極有可能天差地別。我意識到之格是少數會主動與我分享日常的人,我們的感情建立在日常之上,因此觀念的分歧似乎不再值得一提。
並且之格開始讓我消除那種時不時強烈的,我是個充滿庸俗的氣質的、不夠合格的酷兒的想法。
我問之格是否考慮過神經多樣性特質,他對此不感興趣。
之格的新性伴侶是一個留學過日本的順直男,之格說他的某些見解讓他們的聊天十分投契。他會來我們所處的位置找之格玩幾天。
然後因為我們恰好都覺得可以,某一天晚上我們在一間酒吧小聚。
我沒想到他是一個十分英俊的同時,竟然肌肉也可以說發達的健身男性。他給人的一種過於陽剛感,讓我覺得他在床上是否有暴力傾向——我知道有些酷兒會實踐一些性癖,我不確定之格的情況,可是無論如何如果對象是順直男……我幾乎吃驚地意識到我的審美竟然那麼偏向陰柔一些的男性……或者任何性別。並且下意識地想到之格曾進行開放式關係的女朋友,對比之下感到這種對比的不可思議。
於是我打趣,如果他能和之格發生關係,是否意味著他其實具有酷兒性,他是否真的將之格視為酷兒,又開玩笑地問他對於男性顯然的沒有性吸引能否算一種光譜——我的部分態度簡直有種擠壓感。
後續我們聊到喪禮,我和之格聊起我們在親人喪禮上的一些感受。我們能感到他和我們的感受不太一樣,但並不讓人覺得不舒服。然後因為喪禮,我們聊起對死亡這件事的想法的話題,最後話題變成了世界太爛了,想趕緊去死或者地球爆炸。
於是話題無可避免地滑向對當今有毒男性氣質的批判。他說他雖然覺得日本有壓抑的地方,但他還是喜歡那些必要的規則的運行,和社會不同群體的共同張力。我和之格顯然都不會喜歡日本,但我們都認可他說的中國缺乏的東西,以及顯而易見地我們三個人都必然極其厭惡特朗普和馬斯克,所以我們開始就對他們的嘲諷案例大加引用。
在這次小聚之前,我從來沒進過本地這些男性占主導的酒吧,即使他今天選了這裏,也不是因為他發現這裏有什麼非同一般之處,純粹是環境氛圍和裝潢服務感受之類的。
我去過外地的酷兒酒吧,但純粹是因為和認識的人去熟悉的酒吧的社交需求。
所以那個當下,我故意幾次大聲地譏諷男子氣概,就像我曾經故意在公開場合提起我和人一起朗讀男同據點史——利用一個格外健壯的男性的在場去刺激其他男性的感官讓我覺得格外興奮。
沒兩天那個男人就回去了。
再過幾個月,之格在他媽媽身體恢復之後也許也會離開,但我和他必然還會保持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