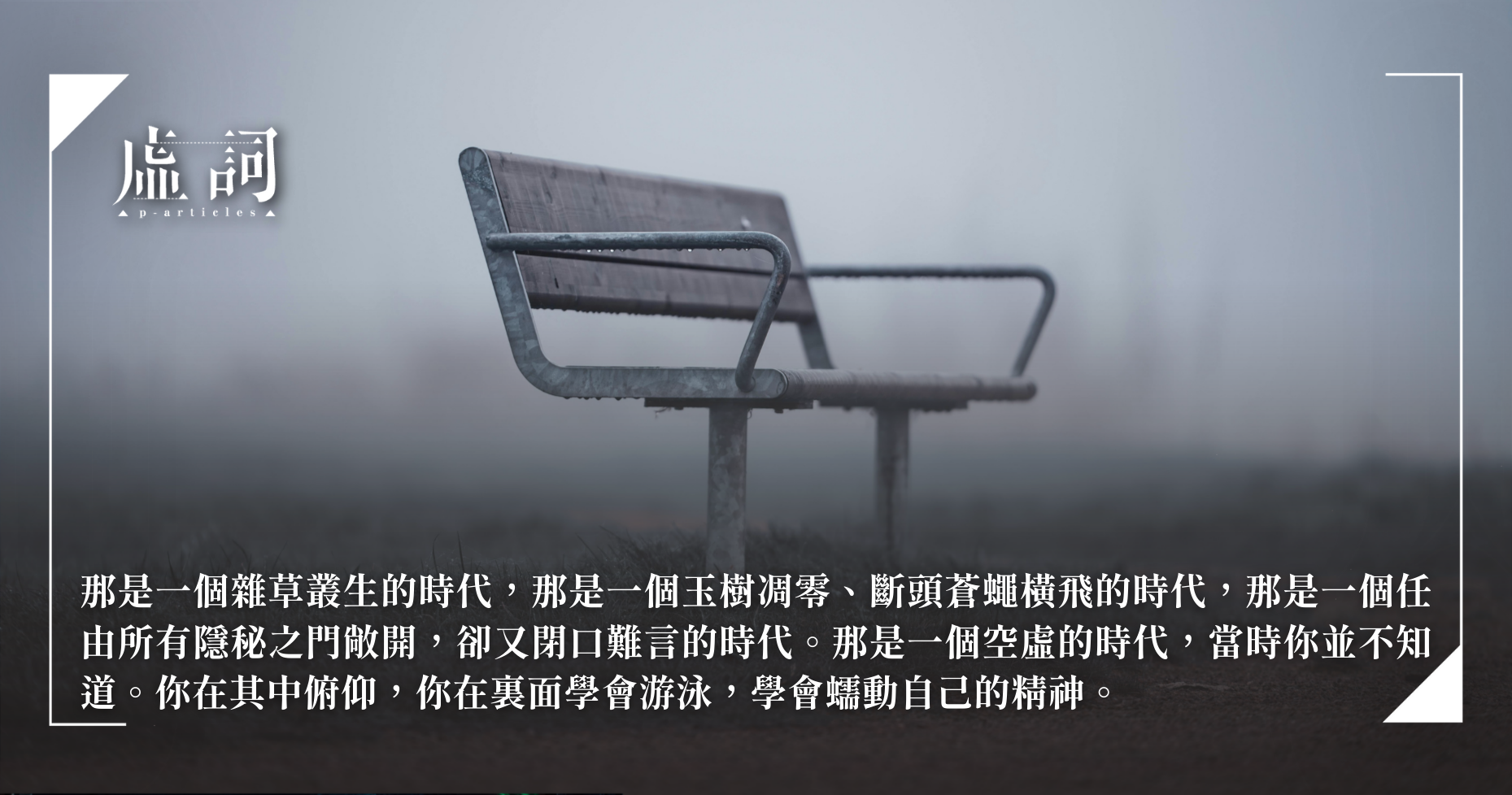允許一些可怖迴旋起溫暖
小說 | by 簾櫳 | 2025-09-12
我向/我的獸跪下
——王鷗行
A
說窗户。說腳步聲。說木質牀板。水龍頭。嘩啦啦、嘩啦啦。說夏天。說你滿眼綠意。還未睡醒。說記得。說你還記得。說悲傷。你真的感到——悲傷嗎?說喉嚨。說你的喉嚨,整夜整夜被人穿過。說你還記得那個夜晚。然後,告訴我。(1)
告訴我。那些我還未知的多餘部分。而在此之前,先聽我講述。我知道的,整個故事的六要素。我知道的那些夜晚。那些,被我深深目擊的一切。我在此書寫,只為搞清楚這些。是的,就這些。這些,就足夠了。
來吧。讓我來看你。讓我們重新來過。讓我們先回到那年,回到你那些明亮的幻想上。那年六月,你過完你最後的兒童節,然後在心裏輕輕摩挲少年這個詞語。我知道那是為什麼。我知道你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在長大,就是因為聽到這個詞。你聽到這個詞,是別人用它來稱呼你。是一個真正的少年,每日騎電動車往返於城鄉之間的少年,是他賜給你這個詞語。你被認可了。你被允許了。你被允許加入進去。你不知道是怎樣的事物將你囊括進去,挾你愉悦地躍過那個暑假。而等到站在新學校的大門前時,你才訝異於自己竟遺忘了對它的思考。但是,不用擔心,這些我都知道。來,我帶你回去。回村裏去。回家。
你在那裏出生。那小院東側的小屋。我會告訴你,更正式的稱呼是東廂房。我會告訴你,和弟弟不同,你就在那裏降生。你降生由村裏的接生婆接着,從母親胯下黑暗的甬道探出。你一降生,就回到家中。回到祖輩一磚一瓦的勞作下。你第一次被要求跪下,也是在這居所中。你向那幅黑白照片跪下,你做出這姿勢,僅僅是完成這姿勢。你早已觀察過那照片中的人,你的曾祖父。但在此之前,你從未想過還要與他發生聯繫。你已從他們口中聽說過死亡的含義,你以為他們所說的去天上,是說再也不用管地上的一切。是說這個人徹底走了。
你意識到自己又錯了。你想問問你不明白的那部分,可不知怎的,你覺得自己知曉答案。你知曉祖母會怎麼說。我們是一家人。你認識到家不只生活在同一個屋中那麼簡單。你是個早熟的孩子,你要記住這一點,任何你發現顯得可怖的事物,都只是因為這點。就像你們搬去縣城,家就隨之長在樓房上。我要告訴你,這樣做是說,你有兩個家,而不是讓你去辨認真假。我要告訴你,世界中沒有什麼是非此即彼的,除了世界本身。我要告訴你,因為再不告訴你,就來不及了。
看到了嗎?你開始學東西。你的國家在互聯網鋪就的軌道上瘋狂前進,你成長的速度也不遑多讓。你是鐵軌日復一日摩擦濺出的火花,你的城市也是。你體察你搬入的這座城市。當時你不覺得它小,有時你會覺得它逼仄,也只是因為人多了一點。很快你便習慣了。你習慣一個班學生的數量,你們村子要十多年才能產出;你習慣樓下一排排飯店,隨便一家菜單上的種類數,要遠超你吃過的所有飯菜;你習慣聽同學們說起的不是蟲子,或是他家的狗,而是動畫片中各種顏色的英雄。你學會這些。你學會這一切。來吧,我告訴你一切中,最令你安心的是哪樣。你終於發現所謂的錢,潛藏在它下面的秩序,是多麼重要。你感到一種天然的邏輯,在支撐着這座城市。唯有這種邏輯,才可以解釋一切,解釋那些在《道德與法治》課本上永遠不會有的事物。而那些事物才是你每日遇見的大多數,才是你遭遇的真實。每每帶着父親給你的錢下樓買煙,你腳下噠噠的聲響,就是在預支着它的有效。
而我的述說,至此已變得冗餘。從你得到手機的那一刻開始,從你打開手機不是為遊戲,而是為閲覽文字的那一刻開始,你便成為滾滾東逝長江水的一小段支流,溺在全國人的悲歡裏。我必須得說,那是一個雜草叢生的時代,那是一個玉樹凋零、斷頭蒼蠅橫飛的時代,那是一個任由所有隱秘之門敞開,卻又閉口難言的時代。那是一個空虛的時代,當時你並不知道。你在其中俯仰,你在裏面學會游泳,學會蠕動自己的精神。你招搖過市,鼓動自己的心臟,你用一種韻律吸引所有的話語坐落。你博覽羣書。你學會了。
是的,你學會了。你學會說話,你學會誇讚,你學會謾罵,你學會賣萌,你學會嘲諷,你學會與人對線,你學會曖昧的手段,你學會索尋資源,你學會去哪兒找你想要的東西,遇見想遇見的人,你學會貼上標籤與被貼上標籤,你學會區分烏泱泱的人羣,順便把自己加以歸類,你學會如何保護一個人,又如何去傷害一個人。你學會了所有事,你學會了置身事外。你學會了擱淺。你試着用這種方式去承接一切。現在,你能承接一切了。因此,讓我們直接一點。讓我們直接來說。還記得第一次射精嗎?還記得你點進Q羣的那個下午嗎?還記得你是如何觀看那所謂雨後小故事的動圖,然後神啓一般顫動着身子去瀏覽器鍵入各種關鍵詞嗎?還記得你終於得償所願,那渾身酥麻的第一下嗎?我知道,你都記得。是我,且只有我,親眼見你一次次用雙手將自己箍緊,將寂寞箍回虛空。你看見自己是一條鬣狗,弓起身子要釋出光燦的嘶吼。你聽見自我深處有無數細小的歡愉,有如盛夏的蟲鳴,應聲起舞。你覺得你又回去了。你覺得你又要迎來粉色晚霞,和短短的一瞬永恆——空氣泛藍,你要結束一天的遊戲,你要沿小徑下山,回家吃飯。你覺得昨夜終於徹底遠去了,覺得自己的嘶吼聲能把父母之間漸遠的距離壓回。
可最終壓回的是你自己。你在宿舍,見他們自慰,從來都是無聲無息。你學會了這種方式。無聲無息。的確有必要存在,平日的你們實在太過喧囂。現在,我們來說說那間宿舍,以及那所學校吧。
現在,我們終於能一窺你那些明亮的幻想。終於能看着它們脱離,從你的大腦,血淋淋地。那並不可怖。真正可怖的,將由我來告訴你。真正可怖的,是你當時一無所知。是你當時覺得所有未知的,都顯得那樣美麗誘人。真正可怖的,是你對一切都懷有希望,是你在一次希望落空後,又生出更大、更明亮的希望。真正可怖的,我們把它留在最後,不是嗎?
告訴我,那些疼痛過後,你記下了它們是如何發生的。我向你保證,我會把一切都根治。我會帶你回到那天,告訴你,你的幻想不堪一擊。我會向你使出那一擊,證明我對你,從無謊言。我會說,你盼望的集體生活,只代表身邊有人,有話語,聒噪、吵鬧、無意義,只會使你看上去更像一頭困獸;你期待的知識,只是渴求被你記住,並不能帶你出走,哪怕走出一隻青蛙體長那般的距離。我還會說,就連青蛙這樣的比喻你也不能再想,我要說,以後有足足七年,你都不會再見到青蛙。
好了,我想這已經足夠對你說明了。你知道的,你是一個早熟的孩子,現在是少年了。現在,你能想明白那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了嗎?你能想起那幾個夜晚,說說你為何心甘情願讓一切發生嗎?別擔心,我在這裏,我會補上你所有的留白,不允許任何人一絲一縷的遐想,不允許任何事又找上你要回溯你的記憶認祖歸宗。我不允許。
我只允許你的述說。來吧。說。說他的指腹是怎樣一簇火焰,滑過你水痘印遍佈的肌膚,點燃你一生中最茂盛的情慾;說他鹹腥的口水怎樣沾染你,而你受凍如雪花,插在心臟上一跳一跳片片消融,要收攏一場漫無邊際卻又穩穩注向一點的連日大雪;說你怎樣奏着無聲的和鳴,褪去的衣物緊縮在身下承接每一個重重敲下的高音;說你如何震顫如蟬的一對翅,微小而又高效地起落晶瑩飛落的汗液。說你們在牀上舞蹈的方式,說你們握住彼此身體的方式,說你們如何擁抱,說你們如何揮動舌頭,說他的陰莖如何慢慢探向你的缺口,充實你搖搖欲墜的核心。說他如何使着柔軟的鐵,掘你深深的謎。
說。說這一切。說你對這一切的理解。喂,你到底怎麼看。為什麼那是被允許的?為什麼兩個男生擠在一張牀上是大家默認的,為什麼他每日當眾親吻你的臉龐,大家也只是一笑了之?為什麼他們的唇碰撞如兩顆白星,大家紛紛為之喝彩?為什麼那條路當時安全如置身子宮,現在他們卻告訴你那通向的是精神病院?你到底怎麼看?
彆着急。我不是在逼你。我們再感受一遍吧。我們一起。我們一起再尋一遍謎底。來,睜眼,讓瞳孔觸摸黑暗,用眼神來摸索你的身體。你看到了嗎?你看見那山麓下圍牆四立的校園了嗎?你看見那狹小的宿舍了嗎?你看見另外幾個人酣睡的姿態了嗎?你看透自己的身體了嗎?你看到自己盡力壓低的喘息了嗎?你看到那股液體如何載着你在空氣中飛翔了嗎?你看透所有的運作之後,是什麼在提供着動力了嗎?
你看不透。你兩手空空。你握住了世上最大的東西。你感到他那根幼小的陰莖可笑地晃來晃去。在你的體內。你渴望的不是它。不是這種疲軟。你渴望的是利劍,是破開胸脯,找到你淹在喉嚨裏,找到如深秋般淹在你深喉的話語,然後刺開它的利劍。你要刺開它,讓它灑落,醉紅周遭的一切。
你要刺開它,刺破這個圓,你要刺出一條直線,一條只需在上面邁動雙腿就表示你在前進,然後得到家人稱讚的直線。你要刺出它。你從前擁有的那條直線。
你那時沒有。你那時只能默默承接。翌日你踏着黑暗去到教室,早讀,唸誦英語,做夢,夢到我,我為你在夢中又圍出一個夢,然後,刺破它。我要讓你醒來。要不然,再過幾秒,老師就會發現;再過幾秒,你就又要受罰;再過幾秒,你就不得不再次發現一切仍和原來一樣。
B
紅燈停,綠燈行。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我的父母卻不相信我知道。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我不記得從哪裏知道這句話的,只記得從哪裏父母認為我不知道。那恐怕得是一二年級的考試了吧。不過那門課的名字倒是記得十分清楚,叫做《道德與法治》。即便現在來看,也不得不承認這名字異常拉風,相較語文數學這種一目瞭然的名字,此種抽象卻又顯得具足的稱謂,更能激發一個男孩的探索欲和勝負欲。而我那時恰好是個再正常不過的男孩,因此很快便迷上了這門課。事實上這門課不似我想的那般高深,反而十分簡單,只需要背課本就行了。老師也曉得這一點,上課從不多講,簡單說兩句,然後我們就開背。
似乎扯太遠了,但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這些,所以還是有必要說一下,對吧?基於你已對我有幾分瞭解這點(當然我不清楚具體是多少),我想無需再贅述為什麼選擇從經驗出發得出的那個答案,而不是課本上的那句。那是我最根深蒂固的東西。我能告訴你的呢,就是我當時的欣喜了。直到現在我依然沒有掘出那股欣喜的源頭,當然猜測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的,直接告訴你那個我覺得最接近真相的吧。
在選擇了「紅燈行,綠燈停」之後,我應當有一種勝利的感覺。對手是課本,一個永不會有錯的權威,一個相當大的東西,相信你不難理解,戰勝這樣的對手後,會泛起怎樣一陣滿足的感受。我懷疑正是這種感受使得我做出抉擇後未加以仔細思考就轉向了下一題,更近一步說,我甚至懷疑是對這種滿足的渴求才促使我做出了那個抉擇。不過,這樣就未免顯得太可怕了些,也不會有多少人相信這樣的說辭吧。所以其實我不應該解釋什麼的,事情發生了,直到現在我都還未能理解,怎能指望那時的我想出一套妥善的說辭去應對父母的詰問呢(或許也不算詰問,更應該是某種嘲笑吧,總之我願意理解成惡意,那樣我會好受點)?
總之,事情就是這樣了。我帶回一張99分的試卷,錯了一道所有人都會的題,儘管我知道那不是我的錯,可我又能向誰去討要那失去的一分?幾年後,我所處的小縣城終於安上了給人看的紅綠燈,有時走過我會生出拆掉它們的強烈慾望,我想那樣就可以維持我的正確,我就可以指着馬路上那唯一的,給車看的紅綠燈,等它變紅,車紛紛止住,然後我拍拍身邊人的肩膀,示意我們該走了。示意我是對的。即使我永不會告訴他這個故事,他永不會知道為何那時我顯得那樣自足。
我只可以告訴你,有關這一切。我知道你都看見了。你看見我顯得那樣不安,在一次次被慾望傷害之後(雖然剛才已經解釋過了,但我還是害怕遭到你的誤解,因此我再說一遍吧,這樣寫是想把原因歸結為某種惡意),我分明見你搖曳在我的某處。你一定是可以看見我的。
我期待你向我解釋這一切。比如我最近為何那樣沉迷刷各種dating app?當我的手指在屏幕上滑來滑去時,到底是什麼被滿足了?我覺得那是種虛假,虛假的女人的臉,虛假的看到臉時的感受,虛假的心理感受牽引肉體作出的反應——它是虛假的嗎?我清楚唯一真實的只是一些微小的可能(有關一具美麗肉體對我的垂青諸如此類),我看到自己日復一日對着這種真實發情。我真希望自己是頭野獸,沒有那麼多細想的機會,我真希望世上乾脆沒有真實了,我抱着虛假過活要比現在這樣好得多吧。就連我的希望也要是假的。
就連我在這裏的書寫也是假的。寫到這裏,我終於發現我已向你透露太多的真實,量多到足夠讓我不安了。但我還有很多話想說,為了滿足自己,我想只好委屈下你,閲讀下面這些半真半假的文字(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把它理解為惡意,更近一步的話,我現在已經明白自己不介意你的消失了,所以假如你想的話,請自便吧)。
說起來,我有懷疑過自己的性取向,可最後還是成了不折不扣的異性戀。今天看來,那些懷疑真好若浮夢般不可思議,於是為了證明曾經有過的真實,我試圖對男人的肉體起反應。
我考慮自己會喜歡哪種男人。先是從記憶下手,我回憶了讓我懷疑自己的那個傢伙(不是進入過我的那個,是心理上的那個),我仔細想了他肉體的方方面面(重點想了當時我愛得要死的白葱似的修長手指),以及性格中討我喜的那部分。回憶過程中我並沒有發現情慾來過的痕跡,有的只是一些年華老去的嘆惋。甚至我還一邊想着他的肉體一邊撥弄了幾分鐘自己的生殖器,但是它毫無反應。
我便只好啓動B方案,蒐集各種男同做愛的視頻來看。連續三個夜晚我都是在觀看別人做愛中度過的。也不能說毫無反應吧,但那也僅限於一方穿着女裝,也就是所謂的CD(老實說,我並不知道這是哪兩個詞的縮寫,我只曉得這麼稱呼就行了)蠕動那些衣物時,才有慾望出洞的感覺。大多數時候,我很清楚自己只是對着那些衣物(準確來說,是潛藏在衣物後面,浮於虛空的女人的肉體,以及緊緊圍繞肉體生髮出的各種可能,場景、手段、動作、聲音等等)生出幻想。但有時的確不一樣,我會感到那些白皙的肉體,包括那根晃盪在空氣中的粉色陽具確有一種難言的魅力,使我一點一滴昂起頭來。硬要說的話,就像是兜滿了水的蘭花吧,一副任狂風驟雨侵入卻屹立不倒的軀體,真叫人期待其徹底傾頹的那一刻。
那一刻要由我來完成。我審慎地對那些誘惑到我的肉體加以考察,試圖找出是哪些部分在吸引我。沒多久,我就發現這是種愚蠢的做法,因為肉體與肉體之間的相似太多,慾望便只好建立在它們細小的差異上。除非我能對所有裸露的肉體發情,但這顯然不可能(或許曾經有過那樣的時期,未來可能還會有,但不是現在)。因此接下來我就在telegram的某個羣組瀏覽各式各樣的肉體(我曾在此尋找過女性朋友,未果,倒是意外發現了許多同性戀交友的羣組,想來也是情理之中,少數平台承載少數羣體嘛)。
我就是這麼認識他的。他發在羣組裏的那幾張照片真叫人吃驚,很難想象現在還有着那樣的軀體。古希臘美少年般的軀體,薄而緊貼的肌肉,張弛有度的線條,每部分都嚴謹地遵從幾何韻律而切分(雖然看得出有PS的痕跡),雙腿筆直地撐起自腰部垂落的曲線,肩胛骨下彷彿暗自生長着一對行將舒展的雙翼,優雅地將整副肉體向上提了提。像是貝尼尼的大理石雕塑活了過來。而我想做那隻捏住大腿的手。
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始終未能下定決心私信他。我害怕自己又是在對着肉體背後的文化,對着貝尼尼在發情。因此我繼續一天天地逛那個羣組,觀看肉體,但在那之後,無論是怎樣美麗的肉體都再難吸引到我,就連先前我收藏的幾具再看也顯得那樣寡淡。對這種變化我並不感到陌生,這意味着內心深處有種自信在催促我變得不一樣。
我開始想象。想象他接受我的邀約,在結束每日的工作後,我們倚偎在一起,像紅色電影中的情人那樣,愛情是一種附庸,一種佐料,我們靠它更好地吸食各自的崇高。我要弄清楚他的崇高是什麼,是怎樣的崇高養育出了這樣的肉體,我企圖沾染這種崇高以徹底接納他的肉體。我想象他的肉緊緊壓在我的肉上,我想象那種觸感,那種温度,我覺得會像經盛夏烤炙的泥土那般緊實温暖。我們甚至還會辭去工作,徹底離開這座城市,去到他的故鄉生活,不管是深山還是海濱,我們會過上別樣的生活,像從前那樣,依靠肉體的苦行生活,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樣樣具體。我想象他是疲倦的,唯有靠進入我才能重新點燃自己,我想象他是善於流浪的,唯有靠親吻我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居所,我想象我可以處理好這一切,我想象我們的第一次見面,想象他的言行舉止無時不刻在證實着我的想象。我想象自己幸福如一道天火向深林吐露此生所有的秘密。
終於,那天來到了。想象把我喂成一個再也不能移動一分一毫的胖子那天,我嫺熟地點進收藏,點擊他的頭像,私信了他。我向他發送了自己的裸照(之前幻想得那樣厲害,很大程度上也是對這幾張照片不抱信心的緣故——正因為大概率無法得到,才愈發希冀在幻想中得到滿足)。幾分鐘後,他回覆了我,說我很好看。之後是幾句無關緊要的廢話,然後我們約在週六晚上見面。
我們在日餐廳見面(這家我之前來過,生魚片格外鮮美)。他和照片上差別不大,穿着一套考究的白色西服(寬鬆的休閒款,蓋住了我想要看見的那種曲線)。我還是勃起了。他似乎發現了這點,覺得很有趣,顯得遊刃有餘,慢悠悠地咀嚼着食物。他說他在一家遊戲公司做美術(他的聲音不符合我的想象,但也不算難聽),本地人,初二那年發現自己是同性戀。
我問他是怎麼發現的,他說和大多數人一樣唄,和好朋友玩着玩着就有了反應,之後漸漸就意識到自己不一樣。他還說自己算比較順的,高中的時候在網上接觸到了同志,後來關於這方面的風氣起來,就更沒啥好顧忌的了。接着,他講了幾個笑話,其中有個是關於他試圖找女朋友的,剩下的都與他的前男友們有關(說實話,都挺沒意思的)。我注意到他說話時喜歡盯着我的耳朵,後來喝了些燒酒之後他就不再那樣做了,說話時選擇低着頭。對我來說,他低頭的樣子更有感覺,這樣我就看不見他的眼睛,因為他的眼睛和我想象中的差別太大了,一點都不亮。
吃完飯後,我們在他的特斯拉上接吻。大概持續了四五秒,我就猛地推開他,含糊不清地說了句抱歉便匆匆打開車門走下車,之後大腦空空地又向前走了好一段距離,才蹲在樹下嘔吐。他沒有追上來。我就是這樣成為不折不扣的異性戀的,不過也不好說,畢竟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跟任何人做愛了(也沒有自慰)。有時我比較希望自己是同性戀,我想象自己要是成為同性戀的話,一定才華橫溢,敏感而又不自知,瘋瘋癲癲地過着不一樣的生活吧。
1/此段是致敬王鷗行詩作《此生,你我皆短暫燦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