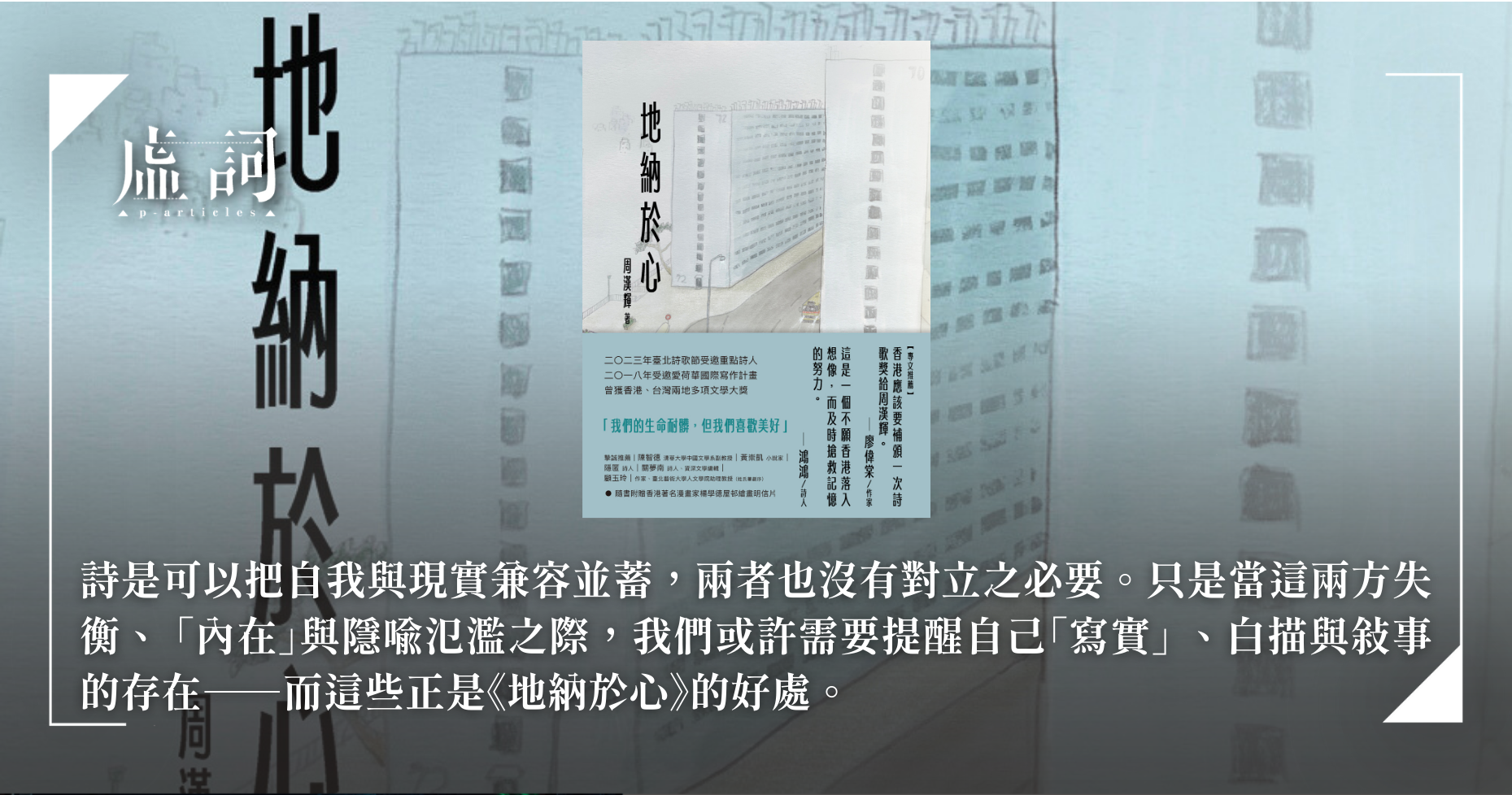再讀周漢輝《地納於心》:兼淺談現代詩的兩種書寫對象
書評 | by 寧霧 | 2026-01-20
近年香港詩人出版的詩集中,我最愛《地納於心》。讀了許多遍,創作靈感枯竭時,重讀此書,常有得着。
《地納於心》以尋常的公屋、街道、飲食為主題,雖有也斯珠玉在前,卻能翻出新意。詩集中,不少詩乍看平淡無奇,不見斧鑿痕跡——沒有令人眼花繚亂的譬喻、意象與形容詞的堆疊、文句的雕琢,卻很耐讀,耐心細味亦有回甘。《地納於心》的風格清通自然,詩中的深情和悲憫也恰到好處,足見周漢輝深厚、穩健的功力。
周漢輝繼承了也斯、鍾國強等本土詩一脈強調「生活化」的傳統,也如馬若、鄧阿藍、黃燦然等詩人一樣,常以庶民、普羅大眾作為書寫對象,但在傳統之上亦有所開拓。初讀《地納於心》,較喜歡的是〈瑞田樓記〉、〈杏仁霜 I〉等較明朗直白的詩。後來留意到,他善於效仿電影技法,以長鏡頭調度畫面,以蒙太奇操縱時間。如〈仨〉之中截取一人生命中三段光陰,交錯縱橫,以山景邨內一座剝蝕褪色的三角小亭,作為三線交錯的一點;於前作《光隱於塵》中,也有令時光倒流的〈無傷〉一詩。空間的逼仄是《地納於心》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如〈搬家日〉中:「他住在劏房/窄小僅容生存,容不下你的好意/他的女友也沒到過當中,需要/便相約在旅館」為逃離空間上的桎梏,詩人選擇縱浪於時間之中。
非線性敘事是周漢輝作品的一大特點。這種手法並非炫技,也有呼應、強化題旨的作用。如在今年桃城文學獎中獲獎的新作《動物救援》中,他以三條人物線互相交錯、複疊:社運的倖存者、受家暴的少女、受傷的獨眼黃狗。講述不同暴力的受害者們相似的命運,以及如何共情、送贈、抱擁、療傷、拯救。
對眾生之苦的刻畫,在《地納於心》中早有着墨,如寫大興邨兇殺案的〈我們的快樂時代〉:「在認識不久的混混身下/強暴,後來做愛,成孕/過程像你讀不懂,我也/寫不了的某本絕版詩集」在此,詩人在他人之痛苦面前,坦承寫作的局限、自身的無力。又如在〈密居誌三首〉中,直面貧富懸殊的社會議題,寫劏房戶如溫水煮蛙般的日常之苦,呈現他們的拮据:「操練萎縮」、「像你活成不完整的人/因居於這不完整的空間」、「城市的牆已夠繁密/像上帝勤於關門/而馬虎於開窗」。詩中的「我」在多年的面試中來回徒勞,諷刺的是,還曾感恩住進新劏的房間,這也許亦帶有作者的自傳色彩。
這些小人物所能做的,只有「牽緊妻穩住眼前一切意義」(〈幸福與詛咒〉),又或者尋覓制度的漏洞——「而你一家人/知道另一漏洞,提早獲批額外/一間公屋」(〈搬家日〉),甚至連自己的誕生,也是意料之外的偶然——「你也生於漏洞,源自一層乳膠」。
以上詩作,均展現出周漢輝善於敘事、聚焦現實的特點。與其說似短篇小說,不如說像微電影。周漢輝也是電影愛好者,首部詩集以《長鏡頭》為名。在《地納於心》中,也有致敬雲溫達斯《柏林蒼穹下》的詩作〈蒼穹下〉。其詩風亦如我喜愛的安哲羅普洛斯,好用長鏡頭,沉鬱,悲憫,如借飲食寫親情的〈杏仁霜 I〉:
我們的生命耐髒,但我們喜歡美好
你說起首爾的冬旅,那件厚白衛衣
像平原,讓狐獴挖掘,脫線纏成雪花
盼待下一次外遊。黑髮耐髒,但我說
白髮也耐看,為你拔除繁影間的一線光
一痛,拈不住,融化在杯中杏仁霜
周漢輝的詩作也許可以被稱為「電影詩」,與我們常聽聞的「散文詩」、台灣詩人洪萬達的「劇場詩」(如〈一袋米要扛幾樓〉 )等等,均展現了現代詩如何向其他藝術形式汲取養分,以豐富自身的生命力。
《地納於心》的另一優點是拒絕煽情,字句冷靜,情感節制;結構亦然,在情景推進後,多見舉重若輕的收結,如〈瑞田樓記〉:
老婦人摸著道壁扶手,晨運緩行
注視他們步入單位,像未來人
回看今人,早知命運——正面
兩片窗光前,一見屯門山脊
決定租住。劏房中一留六年
情感起伏成稜線,承托禱告
同居,一直為了成婚。再在
兩片窗光前,九龍樓堆親近
上帝旁觀窗內,也許眼神柔暖
他們在空氣中比劃,預留位置
給衣車與畫架,從前劏房容不下
鴻鴻在《地納於心》序言提到:「我喜歡周漢輝的節制,那讓他不會被淚水或熱血蒙住雙眼,看不見世界的複雜:『昨天兒子傳訊直言掛念/你煲的老火湯水,但你記得他下班夜歸/寧願喝啤酒。』——詩,可以留下的,畢竟是這種複雜,而非濫情。」
「他們在空氣中比劃,預留位置/給衣車與畫架,從前劏房容不下。」如此收結,餘音嫋嫋,只有名詞、動詞,連結動作與物象,沒有冗贅的形容或隱喻,令人聯想起也斯「又一輛孤獨的電車/轉過彎角/擦出一閃的青色光芒」等句。衣車與畫架,在詩中並非藍色窗簾,並沒有別的意思,而是具體可感的生活物象。由此可窺見周漢輝的詩觀:不故作驚人之語,強調觀察,尊重存於現實中的具體事物,不肆意徵用它們,用作象徵或隱喻——展現作者意念的載體。
周漢輝特別注重觀察。如在〈鳥〉中寫道:「樓壁裝嵌了邨名,麻雀/安歇於筆劃上,像另開/一筆——觀微,描物/對別人略過的細節著迷。」他在與黃柏熹的訪談中提到:「這種寫法很依賴觀察,你已經脫離了想像,脫離了意象的撞擊,所以觀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街道是一個無限地提供很多靈感的地方。當然,對普通人來說,街道就是他們生活的場所,在寫作以外,真實的人的生命存在著動人的力量。」
周漢輝以觀察取代想像,作為詩歌靈感的泉源。從極細微處提鍊詩意,攫取靈感,如屋邨樓壁筆劃上的麻雀、日落於絲襪茶袋、屋邨裡環環複疊的圓形走廊、融化在杏仁霜中的白髮......從我們這些在地上行走的微塵,到宇宙天象、太陽諸星,均成為其觀察的對象。由《光隱於塵》到《地納於心》,均體現其以小見大、包羅萬象的襟懷,亦暗合佛經中「須彌藏芥子,芥子納須彌」的哲思。
古羅馬作家第歐根尼·拉爾修曾寫道:「人生......像一場節慶,有人來此為了競賽,有人為了勤業,但最優秀的卻是那些觀察者 (theatai),同樣地,在人生裡,有奴性的人爭奪着名利,哲學家卻爭取着真理。」周漢輝強調觀察的取向,直接繼承自也斯《雷聲與蟬鳴》以降,本土詩一脈注重賦體、白描的香港文學傳統,同時也符合現代詩鼻祖——波德萊爾,在城市中漫遊並觀察人群的做法。
在《地納於心》中,周漢輝常採用第二或第三人稱敘事,少見「我」這一人稱代詞。多以「你」、「他」、「她」取代作為抒情主體(lyrical subject)的「我」。「我」隱身於幕後,如此敘事手法令我聯想起美國詩人傑克・紀伯特(Jack Gilbert)的詩。在詩集《烈火》和《拒絕天堂》中,紀伯特在講述個人經驗時,慣用「他」代稱自己,製造距離,令追憶亡妻與前妻的澎湃深情更為克制、凝練。這也令我聯想起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的「有我」及「無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我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不同於在前者之中,主觀感情蓋過客觀景物;王國維以「悠然見南山」為例,說明何謂「無我」。在此物我融為一體,不知悠然的是我還是南山,不知是先有南山之悠然,還是先有我之悠然。「我」的聲音雖然存在,但是淡泊靜默,隱沒於背景之中。
《地納於心》所追求的,也許正是這「無我」的境界。詩中人、景、物多不着我之感情色彩,詩人節制地使用「我」,而多用你、他、她......這一節制,反倒使感情更為純摯難得。詩人帶著一種距離來觀察自己,把自己也視為物的一種;更混淆了敘述者、被敘述的對象以及讀者的身分,讓我們自由選擇自己的位置,在不同的視角中游移,避免了現代詩中常見的弊病:把焦點放在自我身上,造成「自我」聲音的氾濫。一旦我們把「我」轉換成「他」,便不難發現,我們常以為屬於內在的自我,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外在的書寫對象。
風景的發現:現代詩的兩種書寫對象
柄谷行人的理論,為我們認識現代詩的兩種書寫對象,提供了一種絕佳的視角。柄谷行人寫道:「在風景畫那裡,畫家觀察的不是『事物』,而是某種先驗的概念。」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在象徵主義詩歌那裡,詩人觀察的不是「現實」,而是自身意念的投影。由此,我們便可以區分出現代詩兩種常見的書寫對象:「現實」與「自我」。
我們稱之為「現實」的——包括:大眾、平凡的生活者、茶几上的茶杯......是對象的一種。另一種則是「自我」。柄谷行人闡述弗洛伊德的說法,指出在近代,人們建構出抽象的思考語言,繼而發現了一種「內在」的風景。近代文學旨在探索人的內心世界,以心理、自我為書寫的對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小說、普魯斯特、喬伊斯、伍爾芙的意識流寫作、美國自白詩......這個把「自我」對象化的西方文學史脈絡,對華語現代詩創作不無影響,衍生出這樣一種詩觀:以「我」作為書寫對象,強調「內在的我」。而由於這所謂「內在的我」,其實不過是一種心理活動,在客觀世界中無法被感知,因此這類詩人往往傾向借助超現實、象徵、隱喻等手法,去描寫這虛無飄渺的「我」。茶杯不再只是一個普通的茶杯,窗簾也具備了多重的指涉。
現代詩的這兩種路數,乍看是浪漫與寫實、主觀與客觀之爭的舊調重彈,實則遠比這複雜。在《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中,柄谷行人引述夏目漱石的觀點,解構了浪漫與寫實的二元對立,指出兩者只是在名稱上敵對、在比例側重上有所不同——「在內容上,雙方均是來來往往,相互交錯。」兩者的內在關聯,使不少作品可以被編入任何一方。柄谷認為,對立的形式,往往只是對相互糾結之樣態的一種切割。在我看來,這種樣式可以追溯到基督教中「上帝」與「魔鬼」的對立,對整個西方思想史有重大影響,以不同面貌重現,例如薩伊德 (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闡述的,所謂「西方」與「東方」的對立。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洞見了:這種對立往往以一褒一貶、主導與衍生的形式出現——使我們習慣認為,在所謂的「對立」中,支持其中一方,必造成對另一方的揚棄。
柄谷繼而指出,寫實亦植根於內心——無論作家如何努力,也無法達致純粹的客觀。「寫實主義的本質在於非親和化。也就是說,它促使我們觀看那些,因為看慣了而視而不見的事物。」柄谷所說的非親和化,也許與我們常說的陌生化相通。柄谷以「將熟悉的事物陌生化」為寫實的前提,這首先是一種心理、觀念上的轉變,例如把大眾、平凡的生活者,當成純粹的「風景」來發現。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大眾」這一風景的發現,恰恰意味着知識份子自我意識的覺醒。柄谷還提醒我們,「寫實」往往存在着一種目的,寫實的過程也不是完全脫離想像的。作家的自我意識凝視現實的某一部分,篩選出具體對象,或美或醜,因此也摻合了主觀的成分。柄谷引用蓋歐格.齊美爾 (Georg Simmel) 在〈風景的哲學〉中的觀點,證明「截取的自然」並非真正的自然:「自然不會有切片。自然是全體的統一,要是從那當中能切取什麼的話,那旋即不再是自然。」由此看來,寫實的對象不是純粹的現實,而是現實與主觀取捨、陌生化、想像的結合——現實與自我意識在此混融,這也許正是「地納於心」的一種解讀。
另一方面,以「自我」為對象的作品,展現的是純粹的自我意識。常見於華語當代詩壇的「內在」書寫,被視為理所當然,造成敏感、憂鬱、病態的「抒情自我」之氾濫。本地詩人嚴瀚欽的詩句可謂一針見血:「一樣的時代催生一樣的詩人/一樣的詩人嘔吐一樣的文字/連血都是一樣的。」柄谷指出,把疾病美化、浪漫化是浪漫主義其中一個特徵。然而浪漫主義的理念,也許與強調「內在」的當代詩歌有相似之處,但兩者不能混為一談。這些詩也許繼承了浪漫主義強調想像的精神,但浪漫派所追求的感受和情感,在忽視感官與觀察,過度依賴想像、隱喻與虛構的「自我」書寫中,大多落入浮泛與濫情的窠臼。
針對耽於自我與超現實的現象,在六、七十年代的港、台詩壇,雖早有大規模的檢討和批判之聲,但此現象至今依然存在。王家琪在〈也斯與七十年代「生活化」詩潮〉中指出,對現代詩「明朗化」的檢討,又可分為立場近於現實主義、援引左翼理論、注重社會意識的「現實派」,與包羅「平白」、前衛實驗等諸般語言風格——來自「現代派」內部的聲音。
若從歷史淵源追溯「內在」的泉源,柄谷的看法是:「內在自我」並非憑空出現,而是承接了基督教告白、懺悔的傳統與西方繪畫的影響,成為現代文學的主流。柄谷以文藝復興時確立的線性透視法說明——在近代文學中,自我如何成為一種不證自明的制度:「從繪畫來看文學,便能了解成為近代文學特徵的主觀性以及自我表現的思考,是為了應對『世界是由持有固定視點的一個人』來看的事態。」
自我意識被內化,成為詩的第一原理——在繪畫上,濫觴於透視法;在哲學上,則可追溯到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而一度被奉為圭臬的法國象徵主義及超現實主義詩派——波德萊爾、馬拉美、蘭波、魏爾倫、阿波利奈爾、洛特雷阿蒙......也是一種所謂「向內探求」的、「投入」的詩。受意識流、象徵主義影響,現代詩逐漸側重書寫封閉的自我,過度依賴想像,抽象、脫離寫實,喪失對客觀世界的觀察和共情。類似的想法,也見諸奧爾嘉.朵卡萩 (Olga Tokarczuk) 的諾貝爾獎致詞:
我們活在一個第一人稱敘事的現實中......我們認定這種個人化的視角、內心的聲音,是最自然、最人性化且最真摯的,即便它擺明捨棄了一種更為寬廣的觀點。因此,以第一人稱敘述,往往被視為是在編織一組無比獨特、絕無僅有的花紋;被視為是擁有個人的自主性,時時意識著自我和自身的命運。但,這也意味了在自我和世界之間築起對立,而那個對立有時會令人感到疏離。在我看來,第一人稱敘事是現代社會非常典型的一種光學特點,也就是個人扮演著世界主觀中心的角色。
若依循柄谷的「倒錯」理論來看,我們以為的:先有一個自我,然後再有自我書寫——事實也許是:先有一種書寫「內在」的制度,自我意識繼而出現。由此看來,現代詩專注於「內在」的傾向,並非源於一個先驗的「自我」,更像是一種被文學傳統所塑造的書寫慣性。其實「自我」與「現實」一樣,不過是風景的一種、書寫對象的一種。「此前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東西,開始看來饒富意義」——柄谷以風景畫為喻,把這一過程稱為「風景的發現」。我們亦可把「自我」視為對「寫實」的價值顛倒,而發現的新風景——客觀世界不再重要,主觀想像成為焦點。日本當代詩人四元康祐也觀察到這種現象:「詩常被歸類在內心吶喊、真相、戀愛、苦痛等文學範疇內,並被禁錮其中。但詩並非僅僅如此。」把詩的書寫對象,局限於所謂「內在」的感情和心理活動,其實是作繭自縛。四元康祐因此提出了「消除自我」這一觀點,這似乎也暗合王國維提出的「無我」與周漢輝抽離的寫法。「現實」之中,其實也存在着上班、飲食、思考的我,這個「我」不是沉溺於內心世界裡,而是作為眾生的一份子,經歷並生活著,和光同塵。
孤獨的練習:以隱喻為核心的自我書寫
象徵與隱喻,往往被現代詩的初學者,視若搖滾樂團中的主唱。以隱喻作為詩歌的核心,其實是一種取巧。于堅曾言:「隱喻是一種簡單的詩。一旦我們明白A所暗示的B, 這首詩就結束了。這種闡釋是做字謎遊戲。某些詩貌似深刻,其實只是我們暫時不知道謎底而已......面具後面是一疊面目模糊的面具,這就是今天世界詩的隱喻遊戲,被闡釋為深刻。」
以簡單冒充深刻,以機智自詡睿智——是以隱喻為核心的詩之弊病。台灣詩人洪萬達、旅居英倫的香港詩人Eric Yip,均在作品中展現新一代詩人對隱喻的反思。
洪萬達在〈論詩詩〉中寫道:
當台中慶綺出現在我的生命之後
當她揮舞她的手手腳腳,當她
用她隱匿於黑暗裡的眼睛看我
我就不想再使用譬喻了
我發現去描寫「什麼像什麼」(她拉了一把椅子,坐在
我的面前)永遠都不會是真實
可是如果不在故事裡加油添醋
她會不會跟其他的女人一樣,
因為感到無聊,而離開?
無獨有偶,Eric Yip 在Tenor(〈男高音〉)一詩中,也有此句:Now that I feel love, all metaphors/have turned duplicitous.(「如今我感受到愛,所有隱喻/都變得虛偽。」)隱喻容易趨於虛偽,言過其實。于堅一語中的:「修辭遊戲意味著語言的失德......修辭過度,隱喻遮蔽了誠。」隱喻的缺席或許會令詩減少趣味,但趣味不能作為一首好詩的靈魂。周漢輝的作品中當然也有漂亮的隱喻,但不佔主導地位,讓位於白描。就如人聲,在瞪鞋搖滾、後搖滾音樂中,被還原成樂器的一種,成為道具和點綴。隱喻與白描一樣,只是一種工具。周漢輝詩中的隱喻密度不高,不沉溺於加油添醋的隱喻遊戲,如一碗清湯腩,恰到好處。
以上多位詩人,均強調真實與誠的重要,這也呼應了米沃什 (Czesław Miłosz) 提出的——「詩是對真實的熱情追求」這一詩觀。米沃什在《詩的見證》中,引述他仰慕的遠親——詩人奧斯卡.米沃什 (Oscar Miłosz) 對隱喻與象徵的見解:「這種小小的孤獨練習,在一千個詩人中的九百九十九個詩人身上帶來的結果,不超過某些純粹的詞語發現,這些發現不外乎由詞語意料不到的聯繫構成,並沒有表達任何內在的、精神的或靈性的活動。」米沃什在這裡所揭示的問題是:自法國象徵主義以降,詩歌容易淪為一種隱喻遊戲——徒具意象的撞擊,成為「小小的孤獨練習」、智性的炫技。
這種現象離不開當時的時代背景。米沃什寫道:「在十九世紀的法國,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都不被視為藝術消費者。剩下的就只有中產階級及其壞品味。」米沃什點出,這種過度依賴想象、與現實脫節的藝術觀,符合當時的社會結構:「奧斯卡·米沃什因而抨擊了現代詩學的一個基本宗旨:它被法國象徵主義者們編成法典,並且此後一直在以多種形式重新出現。它是這麼一個信條,認為真正的藝術不能為普通人所理解。但那些普通人是誰呢?一整個社會結構都被反映在這樣的信條裡。」
需要注意的是,米沃什同時提醒讀者,創作強調寫實、貼近大眾的詩,不等於呼籲詩應有社會承擔,也不是要讓詩拋棄獨立與批判,成為某種意識型態的工具,產生另一種虛偽與糟粕。當中的分別,有如魯迅與「紅色文學」之對舉。故寫實的詩,不應以左翼文學一概而論,誠如夏目漱石所言——我們不必一定要把作品當成某某主義代表的結果。正如漱石解構了浪漫與寫實,或許左翼與現代派的二元對立也是毫無意義。此外,王德威認為,對現實的關注,不能局限於「感時憂國」,而是應該「從淚水走向更多層次的感情取向」。不流於眼淚和煽情,警惕於暗藏優越感的憐憫,也正是周漢輝詩的一大特點。
溫柔的詩學:對他人生活的平凡與苦難有所認知
米沃什認為,詩應該具備高遠視角,但詩同時必須從高處走下來。這種注重日常、落實在地的詩風也類近於愛爾蘭大詩人希尼 (Seamus Heaney)。希尼稱米沃什為我們的世紀詩人,他在引述米沃什的觀點時寫道:
詩人必須身處普通人群之中,與火車站地上的難民家庭處在同一視線高度,與他們一同感受那位母親分給孩子們的發餿麵包的味道,即便此時軍隊巡邏的皮靴正步步逼近,城市遭到轟炸,地圖和記憶在火焰中化為灰燼。要讓詩充滿人性,就需要對他人生活的平凡與苦難有所認知。光是身處先鋒派的沙龍裡是不夠的。正如他在《1945年》中所說,有些東西「無法從阿波利奈爾那裡學到,也無法從立體派宣言或巴黎街頭的節慶活動中學到」。米沃什會深刻地理解並完全認同約翰·濟慈的觀點,即痛苦和煩擾的世界的作用在於磨練人的才智,使其擁有靈魂。
米沃什與濟慈觀點的一致——以及他在《烏爾羅地》中,對浪漫派詩人威廉.布萊克 (William Blake) 思想的和應,恰恰證明了這些詩壇巨匠的作品能夠超越所謂浪漫與寫實之對立,結合真實與熱情,拒絕單一、片面的界定。由此看來,《地納於心》既是寫實的,其實也是浪漫的。這也與朵卡萩對「溫柔」的闡述不謀而合:「溫柔在我們每次仔細且用心觀察另一樣人事物時、觀察某種『自我』以外的東西時出現......它是種意識,是也許略帶憂慮地一起分擔命運。溫柔是深深關心另一樣人事物,關心它的脆弱、它獨特的天性、它無法逃避的苦難,以及在歲月面前的束手無策。溫柔能感知到我們之間的羈絆,感知到我們的相似與相同。」多次重讀《地納於心》令我確信:周漢輝的詩不囿於自我,詩中體現的溫柔與人文關懷,與希尼、米沃什、朵卡萩等近代重要作家的精神遙相呼應。
周漢輝自言受黃燦然啟發,寫面向大眾的詩。這讓我想起美國詩人羅桑娜.沃倫 (Rosanna Warren) 的話:「我想寫對歷史負責的詩歌。」歷史不一定是大的歷史、英雄奸佞的歷史,也包括小的歷史、普羅大眾的歷史。而這兩者往往互為因果。在我看來,周漢輝也具備這樣的胸襟,正如其詩中關注的:劏房戶、公屋居民、自殺的小學生、失蹤者、被強姦者、露宿者......詩人有時親歷,有時參與對話,有時退居幕後旁觀。觀察的不只有苦難,也有平凡。而自我的聲音,亦在這些平凡和苦難中若隱若現,恰恰證明了——詩是可以把自我與現實兼容並蓄,兩者也沒有對立之必要。只是當這兩方失衡、「內在」與隱喻氾濫之際,我們或許需要提醒自己「寫實」、白描與敘事的存在——而這些正是《地納於心》的好處。
「讓詩充滿人性」、「對他人生活的平凡與苦難有所認知」、「痛苦和煩擾的世界的作用在於磨練人的才智,使其擁有靈魂。」——希尼的這番話,或許也適用於周漢輝。香港有這樣的詩人,是我們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