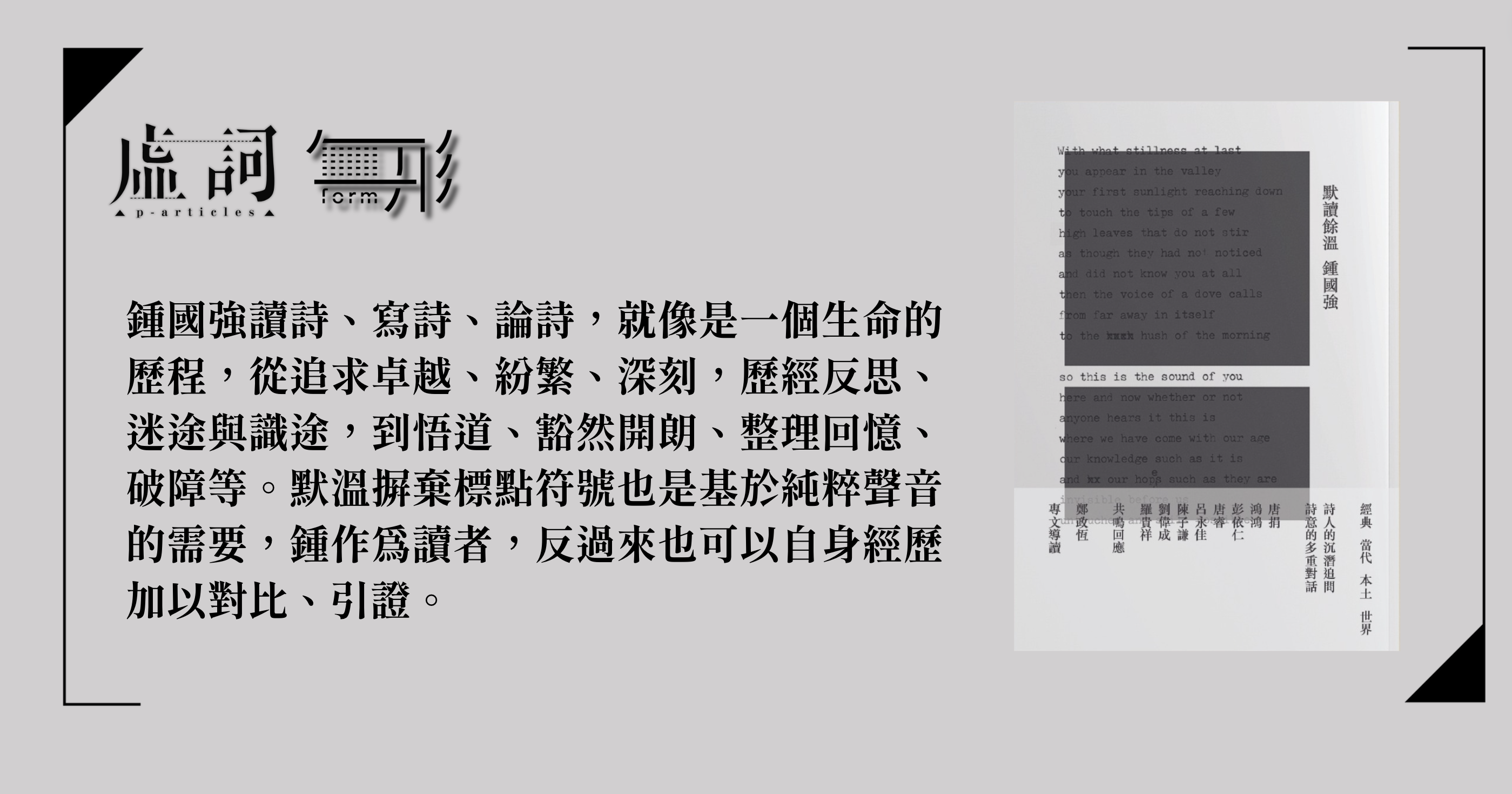【無形・同病相連】重闡本土 讀鍾國強《默讀餘溫》彭依仁
2023年是詩人鍾國強的豐收之年,除了小說集《動物家族》外,還有在中國大陸出版了由其翻譯的《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及《煙與鋼﹕桑德堡詩選》,然後是去年年底字花出版詩歌評論集《默讀餘溫》,我反覆閱讀當中一些文章,這些文章,或為鍾閱讀詩歌、翻譯外國詩的筆記,或為闡述對本土詩或年輕一代詩歌創作的看法而寫的短文。前者包括談論美國詩人默溫(W. S. Merwin)、希米克(Charles Simic,或譯西米克、西密克)的〈生長中的默溫——讀默溫詩札記〉及〈希米克的死亡書寫與黑色幽默——讀希米克詩札記〉,還有收入《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的〈植根於本土,唯在事物中——《春天及一切﹕威廉斯詩選》譯後記〉,還有拿楊牧與葉慈詩對讀的〈在學童之中——讀楊牧詩中的學童、孩子和年輕一代〉及談李立揚的〈為誰寂寞的飲食——讀李立揚的飲食親情詩〉。後者主要為其回應香港詩壇中關於本土詩及自動書寫爭論的〈本土詩的一種面向——以阿藍、關夢南、馬若詩為例〉,輔以談論蔡炎培、西西、飲江的〈接受不同的言語以同一的語言——雜談蔡炎培的粵語入詩〉、〈互吃的共生——讀西西詩〈水母與蛞蝓〉〉及〈光明與良善——讀飲江詩中的「光潔明淨」〉,還有對新晉詩人胡惠文的評論。這兩類文章分別構成書中〈內篇一〉及〈內篇二〉的主題,另加上談論張曼儀翻譯理論的〈由信達雅到再創造——漫談張曼儀老師《翻譯十談》〉及評論王証恒小說集的〈由豸般的存在——讀王証恒短篇小說集《南歸貨車》〉。
在〈內篇一〉以談論楊牧的〈在學童當中〉一文及〈從七疊海岸到海水灣——記讀楊牧詩〉開始,繼而讀孫維民詩的札記〈可是,我的悲傷頑強抵抗——讀孫維民《地表上》〉和談李立揚的〈為誰寂寞的飲食〉,之後就是〈生長中的默溫〉和威廉斯詩選譯後記,而關於默溫的文章又是書中篇幅最長的。就文章次序和篇幅來看,這可說是鍾的私愛。而將對比楊牧與葉慈詩的文章放進卷首,那是因為楊牧對鍾國強的詩歌創作有不能磨滅的影響,而楊牧的詩風亦承自葉慈,第二篇〈從七疊海岸到清水灣〉則是悼念楊牧離世的文章,文章開頭就說「楊牧辭世。想來自我寫詩以來影響我比較大的詩人,都陸續離開了……」而楊牧以降,鍾最為激賞的華語詩人,則為孫維民,及以英文創作,然有華人背景並承襲中國詩歌傳統的李立揚,後者以親情及飲食入題尤為鍾所傾心,鍾也寫了不少同類詩作。然而就詩風影響而言,則莫過於默溫,這也是書名《默讀餘溫》及文章名稱〈生長中的默溫〉呼應鍾最成功的詩集《生長的房子》的緣由。
〈內篇一〉呈現鍾整個讀詩的脈絡,雖沒有其老師也斯及香港前輩詩人的名字;但事實上,鍾也沿用也斯所闡述的詩學觀點。在流馬與其進行訪談的〈今夜,我想念了自己一秒鐘〉裡,在談到仿也斯的作品〈傍晚在鰂魚涌〉裡,採用也斯style的時候,鍾提到也斯主張中國畫式的「捲軸式的線性鋪排」。
但說到楊牧的影響,則不單涉及到文字和技巧,還有詩中的節奏和語調。鍾獨愛其八十年代詩集《禁忌的遊戲》、《海岸七疊》和《有人》。談及《有人》裡面那首關懷社會題材的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時,鍾這樣說﹕
這於楊牧來說是屬於非常破格的詩,慷慨激昂與婉轉低迴處,俱動人心神,乃楊牧寫詩生涯以來極少數的主要以「氣」駕馭而非一味以技巧操作的詩。
個人認為,除語言外,楊牧的氣質也是鍾國強在詩作中孜孜追求的。也許,作為香港人,我們的地氣強一點,這也是我們可愛的地方。鍾國強的詩既有也斯樸拙的一面,也有楊牧婉轉、迂迴的一面。鍾國強繼以楊牧詩作〈在學童當中〉(收入《北斗行》)與葉慈同名詩作對比,點出楊牧創作時當時年紀(35歲)比葉慈寫該詩年紀(60歲)之別,有一種思忖不同年紀如何觀看童稚的況味。有趣的是,暮年的葉慈在詩中追憶青春,尤其是戀人的形象,而楊牧則更積極開朗。鍾國強也提到,雖然楊牧寫作此詩時人在美國,但詩中表現出他也不時回台灣教書,鍾也從楊牧該詩,看出楊牧警惕書齋生活的語句﹕「在書頁的擁抱裡,緊靠著文字/不見得就活在我們追求的/同情和智慧裡。」這也是鍾國強對一頭投進詩歌,忽略日常環境的警惕。
鍾國強也討論楊牧的另一首詩〈介殼蟲〉,詩中難得地描寫小灰蛾等待蛻變的忍耐,在〈內篇一〉另一篇文章〈哲思下的眾生——漫談辛波絲卡的動物詩〉中,鍾國強談論辛波絲卡詩作〈俯視〉時,再拿〈介殼蟲〉當中對於小昆蟲的同情,來與辛波絲卡的「俯視」角度對比。認為楊牧起碼以該種介殼蟲「長長的正式名字」來稱呼牠,然而關於辛波絲卡,他問道﹕「小甲蟲死得卑微,死得毫不足道,那麼人呢﹖作為大自然的成員之一,人的生死為甚麼更重要﹖為甚麼人的死亡要求更多關注(和哀悼)﹖」這正是鍾國強與很多華語詩人,尤其視人為歷史創造者,或受苦者的詩人同儕,有所不同的地方。
在〈生長中的默溫〉,鍾也談到默溫詩集《虱》裡面以動物為題材的詩〈給來臨的滅絕〉,然而亦如鍾說的,《虱》的主題是扣連越戰的環境保育,有一種全球的宏觀視角,而不是動物微觀。與默溫同屬深度意象派的希米克,反而寫了不少動物微觀詩,希米克喜愛尤其螞蟻的形象。在〈希米克的死亡書寫與黑色幽默〉裡,鍾這樣理解希米克對螞蟻的憐惜﹕「螞蟻的卑微、孤獨、猶豫、徒勞、沒有出路,一切消亡淪為無意義的遊戲⋯⋯不就是我們生存現實的寫照嗎﹖」
對動植物甚至小昆蟲的凝視和珍重,與鍾國強的本土詩風也有很大關係,鍾寫了不少歌詠小蟲和花草樹木的詩,鍾藉以抒發家庭之情,比如〈蚊蚋〉中以蚊蚋之聲比附母親的操勞。我們再細想,如果「本土」就是撇開那些飄渺的大觀念(比如面目模糊的國土、人民,或者負載民族記憶符號的紀念碑),珍視當下轉瞬即逝的經驗,而這些經驗與朝生暮死的花鳥蟲魚,又何其相似。在威廉斯詩選的譯後記裡,鍾更多著眼於威廉斯詩中的「本土」,威廉斯詩中的口語化和率性放任,無疑讓作為譯者的鍾國強深受感動,這一點,他在〈內篇二〉那裡談到蔡炎培不單以粵語入詩,還夾雜文言文、詩詞典故和鄙野的句子,並指出香港語言同樣夾雜粵語文白,亦可見鍾國強私淑楊牧詩風之餘,並沒有削弱其對本土語言的肯定。
威廉斯寫他祖母的詩〈致一片土地的獻辭〉,以鍾喜歡的家庭題材解釋了如何成為「本土」。此外,威廉斯在《春天及一切》中大量抒寫成長環境中的花草,和周遭環境的底層小人物,這種富同情的視角,也是「本土」的特徵。如果從文學發展的角度看,威廉斯是從他所追隨的意象派運動中,自覓蹊徑,與提倡本土詩的香港詩人也斯亦有相似之處。而本土之所以異於純綷文人風格,其關鍵於亦在對身邊事物抱持樂觀、持平的態度,而非透過事物的支離破碎,呈現文明毀滅或抒發個人憂思。雖然葉慈在詩藝上無可挑剔,但鍾仍比較喜歡楊牧〈在學童中間〉的樂觀態度﹔另外,在對比艾略特《荒原》的悲觀情緒和《春天及一切》的活力時,鍾國強亦肯定後者。雖然鍾因為翻譯的需要才細讀威廉斯大量詩作,但無疑在威廉斯詩中發現香港本土詩一個重要的詩學源頭。
梳理這些閱讀經驗十分重要,因為這可以解釋2015年前鍾在《明月》及《立場新聞》上發表該年中文文學雙年獎研討會的演講稿〈本土詩的一種面向〉一文,以及針對該文見解的批評文章,比如刊登於字蝨Kritik的〈本土詩歌風景:「興體詩」的路向〉。鍾的文章所針對的文本,是陳暉健詩集《關於以太》中的自動書寫。而批評者則認為,鍾在文章裡對自動寫作的批評,尤其是戲謔詩的舉動,令他們覺得不夠包容。〈本土詩歌風景〉鍾引用年輕詩人梁匡哲以洪慧詩作〈幸會〉的話作出的回應﹕「這樣的詩(指〈幸會〉),沒有四平八穩的結構,也沒有在一個集中意象中停駐和醞釀,不是落到實處的眼前所見之物,甚至鍾沒有相關的經歷」並認為鍾構成了意象詩和生活詩的對立,又引簡政珍對孫維民詩作〈夜色〉的解讀指出兩者可以並存。
這涉及到詩歌創作一些比生活詩與意象詩對立更關鍵的問題,比如脈絡、可感性等等。比如威廉斯的很多描寫花草或雀鳥的意象詩,單就意象而言並不紛繁,它動人的地方,就在於詩中所描述的意象能否感動讀者,還有詩中所關連的脈絡。我們都說鍾已死,能否感人,也得由讀者說了算;但這也意味著,詩不是一種紀念碑式造物,而是鍾、作品和讀者之間的連繫,而感受力或想像力不只是天馬行空的,當中也涉及大家的知性和經驗。
事實上,〈本土詩的一種面向〉並非一篇嚴謹立論或舉隅博引的文章,還帶點個人情感。然而它的重點,仍放在對鄧阿藍〈不要讓爸爸知道〉、關夢南〈傷口〉及馬若〈在床上寫一首詩〉三首詩的解讀上。鍾在2019年〈別字第二十三期〉發表的〈【詩人自道】暫時只能這樣說〉裡說得更具體﹕「我無意輕視格律森嚴、技巧精湛、意象韻律俱優美動人之作,甚而是神秘通靈、恍兮忽兮、馳騁萬象、內藴深遠的神品;但很多時,我還是會為一些表面上極其簡單、但在無聲無色的低調敘事中卻能慢慢滲發足以撼動人心的作品尋思出神:這,究竟是如何能做到的呢?詩得以建立的元素為何?有甚麼可捨去?有甚麼不能?⋯⋯」
比如鍾國強翻譯過的南斯拉夫裔美國詩人希米克,和希米克私淑的南斯拉夫詩人波帕(Vasko Popa),他們同屬夾雜荒誕、超現實和黑色幽默的東歐詩歌,然而語言卻極其簡潔,詩中的玄思得以更簡潔地表述。這當然不是抹煞那些意象紛繁而感染力強大的佳作,但就讀詩經驗而言,我們會更偏愛那些意味深長的作品,而波帕和希米克的例子證明,超現實主義同樣也做得到。
至於默溫的詩,對鍾國強大概也有類似的吸引力,與希米克小心打磨詩中意象相比,默溫是更純粹的聲音,默溫對純粹聲音的敏感度,正是讓鍾感驚訝的特質之一。談到默溫後期詩集《天狼星的陰影》第一首詩〈牧笛〉時,鍾國強引用默溫的話:「創作過程就是傾聽的過程」,認為「由此看〈牧笛〉一詩之所以那麼澄澈空靈,不摻感官雜念,或許正是得力於這種原初的、單一的純粹。」
鍾國強讀詩、寫詩、論詩,就像是一個生命的歷程,從追求卓越、紛繁、深刻,歷經反思、迷途與識途,到悟道、豁然開朗、整理回憶、破障等。默溫摒棄標點符號也是基於純粹聲音的需要,鍾作為讀者,反過來也可以自身經歷加以對比、引證。「生長中的默溫」雖標榜「生長」,但那「生長」也是一個語言和生命互相對話、引證的歷程。如果詩一直在「生長」,那麼本土詩對於意象並不是排斥的,但在「生長」它對其意象有所追求,這有點像一棵樹總是趨光的,但不代表排斥任何有益的養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