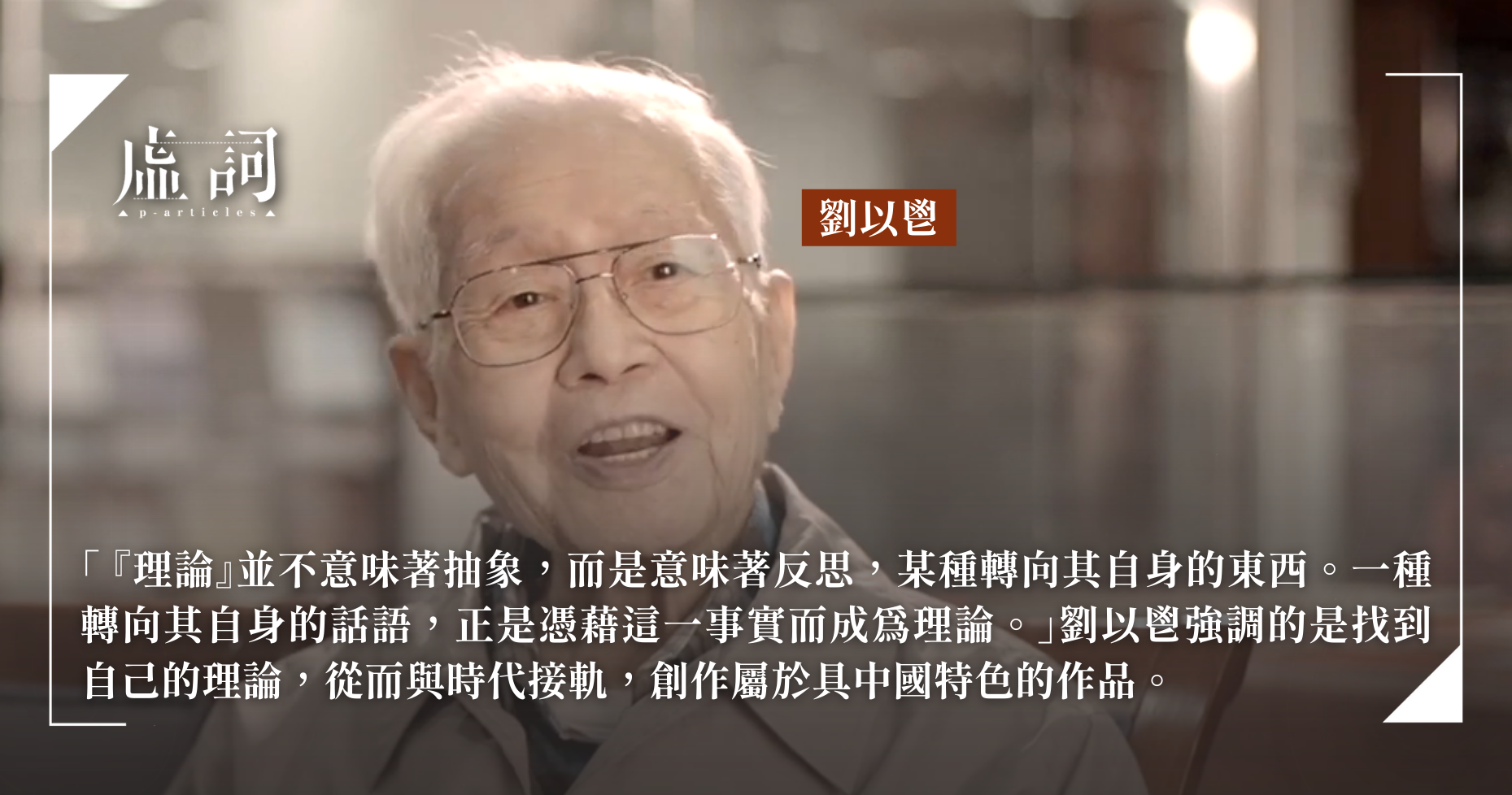談劉以鬯〈借來的理論與技巧〉如何影響創作
劉以鬯〈借來的理論與技巧〉發表在《蕉風》革新號上,使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書寫南洋生活為主的他,這篇「文藝沙龍」的意義不言而喻。1964年的《蕉風》革新號月刊,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其中最早一本在香港承印的星馬雜誌。它由香港友聯南來文人在1955年創辦,直到1999年出版第488期後宣告休刊。共488期的《蕉風》由吉隆坡友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負責出版,2002年續以第489期復刊,連載至今。雖說刊號上有歷史承接的意味,但其時《蕉風》已由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馬華文學館一力承辦,它是馬來西亞文壇一本嚴肅的文學雜誌。
「南洋」和「新文學主義」兩個對照物
劉以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新加坡逗留工作。他書寫南洋的作品概略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以南洋為小說場景,書寫南洋生活經驗的小說。另一類則是在書寫香港的小說中,以背景或旁支出現的南洋景象。他1957年返回香港後,持繼創作具有南洋色彩的小說,同時發表在兩地的刊物。顯然,踏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劉以鬯以香港為中心的敘述中,南洋並非唯一的對照場所。與「新文學主義」書寫形成對比的是,在他的文本中,傳統元素與現代手法是沿著互惠的路線運作的。
這裡必要關注的是,劉以鬯1957年帶著南洋經歷回到香港,藉小說以美化南洋的經歷,書寫南洋事物不足為奇,這是推動香港故事,啟發香港思考的關鍵之一。因此,從敘事角度而言,劉以鬯小說中的南洋主要發揮兩種功能。第一種功能,即是讓南洋成為救贖香港罪惡的工具,他寫出的作品仍是相當接近南來作者的常見主題,多包含對香港的否定,包括其名作《酒徒》以及《故事新編》之〈孫悟空大鬧尖沙嘴〉,對香港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商業社會的面向。這類作品已然包括「故事新編」的其他小說。
「故事新編」是歷史悠久的創作類型,在現代文學史上,魯迅《故事新編》和《野草》等都是代表作。「故事新編」,重點在於「新編」,並沿用原著的符碼,把古典故事置於現代社會之中,為傳統的故事或形式賦予現代的意義。因此,劉以鬯「故事新編」關鍵在於傳統元素裡面有現代的理論技巧,而《蕉風》革新號刊載的是他對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運動以來是一種「革」而不「新」運動的看法。之所以缺乏第一流作品應有的獨創性,理由是切斷優秀傳統的持續,同時還「自由地」,雖然不是盲目地借用了歐美的理論與技巧。
同樣是借用,劉以鬯返回香港後借南洋物件為對照,發揮小說中的南洋第二種功能,即是以南洋作為香港的對照物件,藉以突出香港的特質。這樣在過程中可以經常讓敘事者發現香港的優點,為理解深刻的香港提供契機。而劉以鬯之所以批評新文學作家在寫作時與外國作家相似,顯示借用理論技巧「蓄意的模仿」之下,不能產生高水準的作品。
進一步看劉以鬯《故事新編》之〈孫悟空大鬧尖沙嘴〉,原文發表於1964年10月31日《快報》,後收入小說集《打錯了》,是借用《西遊記》的故事來抒寫作者眼中的香港。借用《西遊記》的情節套路(取經途上遇妖、八戒闖禍、悟空變身等),來抨擊色情事業以及香港女子的崇洋媚外。透過改編,一方面令香港文學上接古典傳統,另一方面又藉以表達作者對本地社會現象的批評,把古典文學作品與香港本土社會結合。
基於上述論點,我們可以看到劉以鬯〈借來的理論與技巧〉與《蕉風》銳意改革,提高水準的旨趣互利互惠。
借用的理論須消化
劉以鬯在〈借來的理論與技巧〉文章中談「吸收」和「消化」的文藝概念,開篇即以1964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其中有一段相當客觀的評介:「作家們很自由地借用了歐美的理論與技巧,其中一部分作家曾留學歐美。西方文學的趨勢,普遍地反映在中國的,都是幾十年前的東西」來談蓄意的模仿。他以曹禺〈雷雨〉和茅盾〈子夜〉為例,說曹禺的作品有易卜生的影子,並認為曹禺的作劇方法明顯還來自優力辟狄斯(尤裡比底斯,前480年—前406年)的影響。甚至說他〈原野〉與尤金‧奧尼爾的〈瓊斯皇帝〉比較,兩者之間的相似,顯示「蓄意的模仿」。至於茅盾的〈子夜〉,「大英百科全書」說是受了左拉與托爾斯泰的影響。劉以鬯認為只說對了一部分,在他看來,茅盾受U‧辛克萊(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 Jr. 1878年—1968年)的影響似乎更多。
可以說,劉以鬯對中國新文學運動展開以來,對曾經喊出過「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口號的覺醒,曇花一現的主張難免惋惜。他覺得新文學在本質上仍舊依賴借來的理論與技巧支持著它的持續。從而不無感慨抗戰時期「文藝陣地」覺醒的那一次並不是真正的覺醒。作家們數十年來一直在探索,如今應該客觀地、冷靜地反思,如何走出模仿,創作屬於自己作品應有的獨創性。
劉以鬯進而對作家仍在模仿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名著,相當不滿。他認為有些人固執地認為「唯有模仿寫實主義的作品才是正統的文學作品」。這種觀念完全失去了文學革命的積極意義。
劉以鬯在文章中提到「借用」歐美的理論與技巧,固然可以革掉舊文學的命,卻不能產生民族意識極強的具有文學精神的作品,除了魯迅的阿Q正傳,他以「中國新文學的古典作品」來描述作者繼承了傳統,同時又吸收了西洋文學的精髓,創造出一種新的文體。
從歷史的必然性來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產生無可厚非,但這個「新文學主義」並不是積極的文學革命。開闢道路者急於有所表現,手上缺乏開路工具,倉促間只好向外國借用器材。顯然,當時新文學有勇氣「除舊」,卻未能徹底「佈新」。因此,一直因循下來碑帖的臨模者,卻沒有勇氣擺脫被臨模者的影響,創造屬於自己的藝術。概括而言,作品失去佈「新」的意義,而且沒有一種正確的引導,從而失去文學革命的積極意義。
其實,胡適在五四新文學運動時以西方小說觀念為參照系,對短篇小說確立的初步概念,理應作為有條件的接受傳統中優良法則的指標。然後站在新的角度去認識傳統,賦以新的意義,解除傳統的束縛,創造進步的、站在時代尖端的文學作品。或可以找到建立自己的理論與技巧。
「單靠模仿,不會獲得成就」
劉以鬯為文的旨意頗明確,就是「必須建立自己的理論與自己的技巧」,他還透過亞瑟‧保維對青年喬伊斯說的「單靠模仿,不會獲得成就」實例,來說明作品中應儘量保持民族氣質與民族芬芳,及必須具有獨特的風格、精神、形式與內容。以下為引文:
喬伊斯在十八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對文學應該做些什麼了。1900年,在發表於《半月評論》上的那篇〈易卜生的新劇本〉,他對易卜生的「當我們醒著死亡」一劇,推崇備至。從那時候起,他就下決心要追上甚至超越易卜生了。當他十九歲的時候,他對自己將來的成就已無懷疑。但是,熱誠並不能代替成熟。他寫了一個模仿易卜生的劇本,企圖為人類的一些基本問題找到答案。這個劇本早已失傳,據說是一個失敗之作。後來,喬伊斯對法國的諷刺文字極為醉心,有意將這種諷刺文字當作碑帖來臨摹。他的朋友亞瑟‧保維對他說:「單靠模仿,你不會獲得成就。你是一個愛爾蘭人,必須依照愛爾蘭的傳統寫作。借來的文體是沒有用的。你應該將你血液裡的東西寫出來,毋需寫你腦子裡所想的東西。
亞瑟‧保維這一番話真正為青年喬伊斯帶來巨大的影響。喬伊斯對屠格湼夫的寫作天份從未有過懷疑,後者的《獵人日記》書寫的是純粹屬於俄國的故事,這使人想到屠格湼夫在民主精神、人道感情和真誠善良的天性的驅使下,以其詩人的天才和「獵人」閱歷,真實地描繪出一幅幅俄羅斯農村生活的畫卷,顯示了生活的發展趨勢,否定了違反人道、違反自然的社會制度。因而,此書使屠格湼夫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文學巨匠。
劉以鬯認為從新文學的發展軌跡來看,混亂而蓄意的模仿,完全放棄自己的個性,就不可能超越臨模者已經達致的成就。從事新文學工作的人,如果不加選擇地將所有古典作品當作廢物,不但愚蠢,而且是一種巨大的、無可彌補的損失。那些保守的工作者受了錯誤的引導,始終在黑暗中摸索,亦步亦趨。
誠然,借來的理論與技巧並非阻力,相反既然向歐美借來理論與技巧,那就必須消化,轉化為獨創性,擁有中國自己的特色。這裡或藉羅蘭.巴特說的「『理論』並不意味著抽象,而是意味著反思,某種轉向其自身的東西。一種轉向其自身的話語,正是憑藉這一事實而成為理論。」劉以鬯強調的是找到自己的理論,從而與時代接軌,創作屬於具中國特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