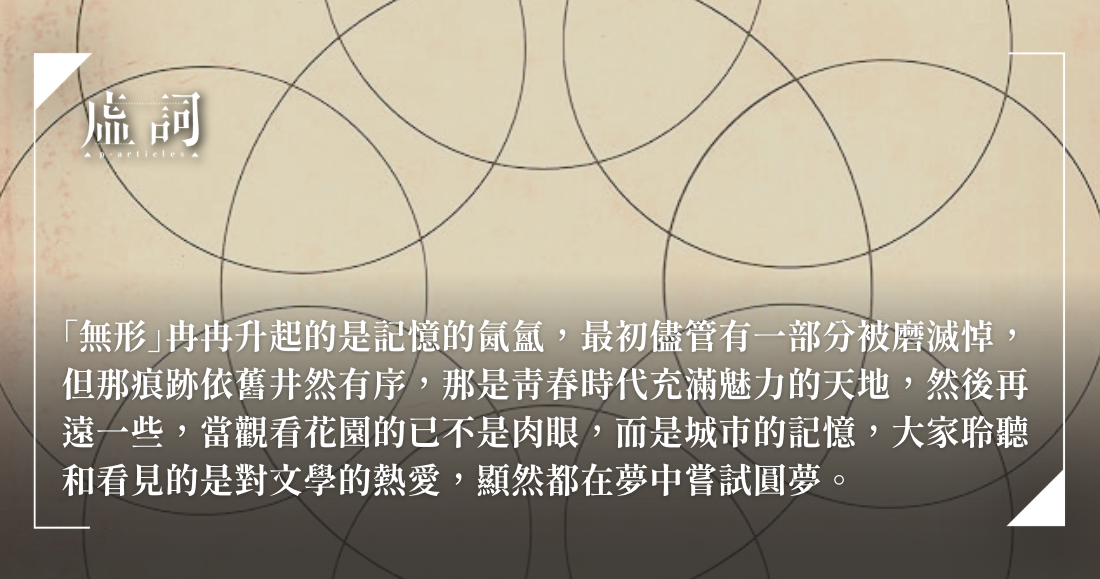【虛詞・◯】夢中圓夢
夜晚,狐狸出現,輕響,低語,微微喘息。
狐狸總在我們左右,恍如夢魘糾纏。
我們徘徊在過去的人和事:誰會被銘記?誰會被時空遺棄在歷史中?
用什麼方式被永久懷念?當這些從記憶之書消散,是否意味著書寫終結?
抑或步入另一個世界之河,飄浮、流離、浪跡,陷入無可追溯的忘川。
但無論步向何處,過了忘川之後,你不妨開始重組,而氤氳霧氣果然就在那裡,即便你從城內城外遠眺,文學風景都是一樣。一個同行人的感受:
剛剛去了台灣,
也看了「他們在島嶼寫作」:也斯東西,
雖然整套戲很長,兩小時多,但挺值得看。
不過如果對比在島嶼寫作的西西,西西較感人。
但也理解的,也斯涉獵範圍較多,朋友又多,難以像西西一樣集中。
真的很喜歡香港文學,喜歡也斯,喜歡陳慧,喜歡辛其氏。始終覺得台灣的散文不及香港的親近,但當然林文月余光中等等的文章還是很好看。
我喜歡寫文章,很是羡慕投稿「虛詞」中那些創意十足的作者們。
總是矛盾,覺得文學會讓自己感性得很疲累,但好像那麼多的耐心經營,看到了實績,往後卻看得並不十分清晰,彷彿渦漩運動,或者錯落接續的圓周。
我沒想到我會說了那麼多的話,也好像很久沒說那麼多話。
我也想說「無形」真的是能讓人圓夢。
時代轉變,文學理論家看到比實際多出許多的圓圈,彷彿是劇場舞台那個具魔力的圓圈和草地上跳舞時那些同心的圓圈。被樹木圍繞起來的草地或是小孩子們的圓舞,揮動手上的彩球,像漩渦一樣激烈的,好像在一個電影的特寫鏡頭中,女孩子們長長的金色鬈髮,特具氤氳效果,迷宮效果。喬治・普萊(Georges Poulet 1902~1991)稱之為「圓圈蛻變」。
「無形」就像是個花園,屬於三個類別的花園,但設計成同心圓的形式。如果不承認三座花園具有空間遠近透視,至少從時間的觀點來看,是具有遠近透視技巧的。讀者的眼睛首先觀察到香港文學文化現象的花園,然後稍遠一些是城市轉變前後文學創作的花園,接着是更遠之處則是歷史的花園。從這層意義上看,這三重花園居然成為整個城市的縮影模型,不過是從終點往前回顧。
我們似乎覺得,圓圈的重要性,不應該被時代所遺忘。「無形」冉冉升起的是記憶的氤氳,最初儘管有一部分被磨滅悼,但那痕跡依舊井然有序,那是青春時代充滿魅力的天地,然後再遠一些,當觀看花園的已不是肉眼,而是城市的記憶,大家聆聽和看見的是對文學的熱愛,顯然都在夢中嘗試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