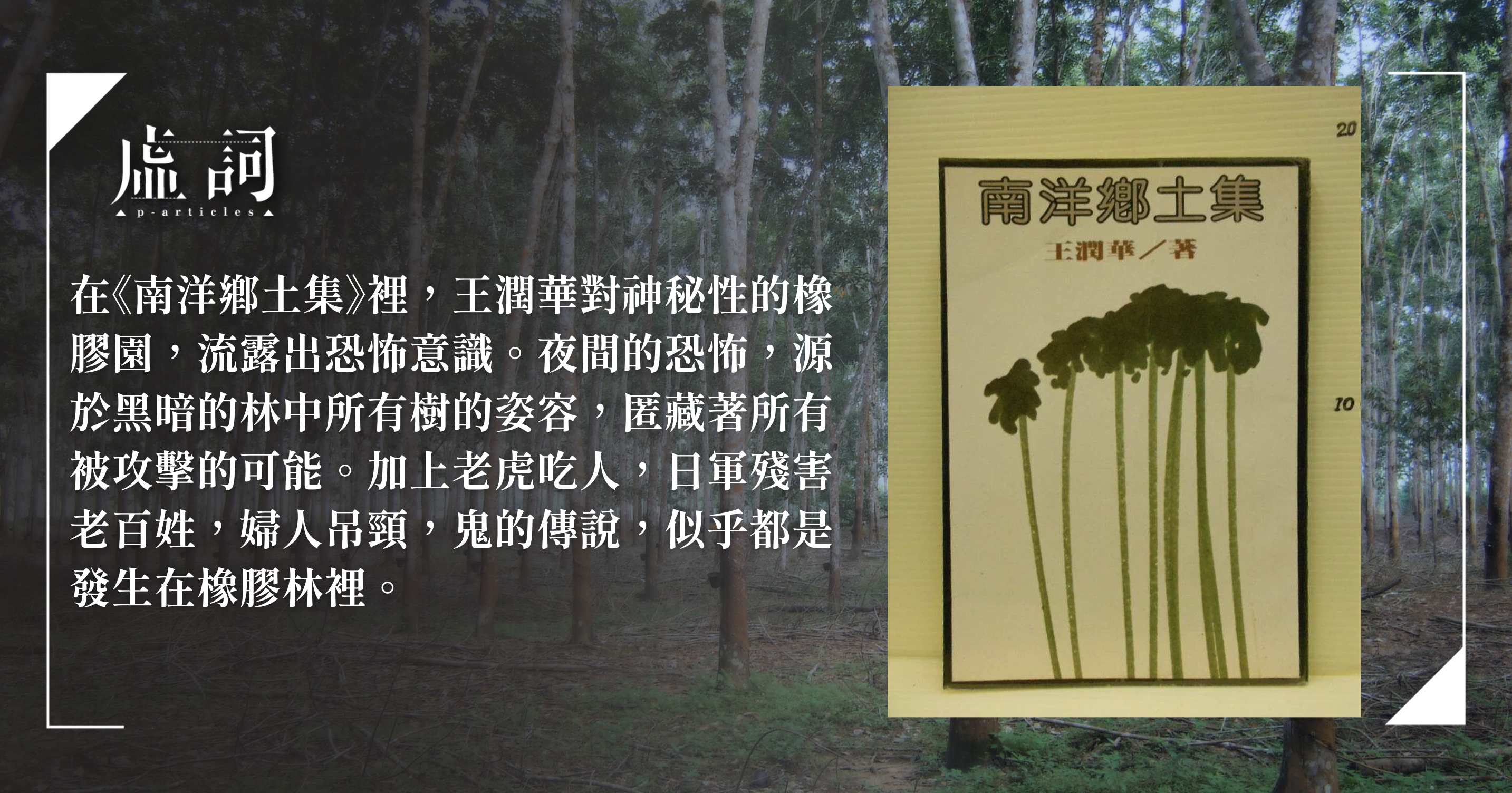王潤華「南洋書寫」中的記憶與空間
《南洋鄉土集》是馬來西亞南方大學中華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兼作家王潤華早期一本散文與詩的合集。集中呈現的具有南洋屬性的花果樹木,充滿熱帶風情的榴槤、山竹、紅毛丹、木瓜、波羅密、鳳梨、楊桃等應有盡有,展示「國族寓言」性質的鄉土文學。
「國族寓言」的鄉土特性
王潤華愛吃過溝菜,新馬華人稱它為Kagu菜。他用作隱喻:「我愛吃過溝菜,除了它美味可口,還有其以問號的生命形式來呈現」。脆嫩可口的過溝菜,在殖民統治的人嘴裡是如此美味可口!他以長得像個「大問號」,當地人餐桌上常見的過溝菜,抒發身為第三代華人移民的在地感情,梳理自己的家園被英國殖民、被日軍佔領時,肆意屠殺當地百姓,卻找不到真相的歷史情結。 長輩圍繞兒童書包中的作業問題,與家人圍桌共食的話題,有太多的悲劇找不到答案,及至「今天新加坡植物園的蕨菜 / 還是用像問號的手掌 / 捕捉陽光與月亮 / 逼它見證許多屠殺的秘密」。
在馬來族的生活中,煮米飯時必放一小片斑蘭葉,讓米飯益添芳香。斑蘭葉是生長在東南亞的一種香草,不只白米飯,各種糕點、紅豆湯、炸雞等食物,都可摻入斑蘭葉的綠色素與香味。但「自從英國殖民者 / 焚燒森林 / 種植從巴西移植的橡膠樹」,「慘死在巴冷刀後」的斑蘭葉,成為王潤華哀悼寄託無盡綺思的香魂。
在南洋野草果樹的氛圍裡,豬籠草、含羞草、黏人草、雨樹、橡膠樹、相思樹、合歡樹等都有各自的屬性。王潤華將自己比作樹,先開花後結果的植根於南洋的泥土中。他童年對橡膠林的印象記憶,恍如門房「廻蕩」着幸福堅韌而又帶些恐怖孤寂的氛圍。可以說在地志空間,作家居住和生活過的地方,同個人的成長和家庭的生活狀況、個人的身份有着密切的聯繫。
加斯東‧巴舍拉在《空間詩學》中有關空間的討論是一系列空間方面的原型意象,所有人類對於這些空間意象都有類似模式,顯現個別面貌殊異的心靈反應。這種心靈反應總結在「住居空間作用之實感」中,而實體的房舍、傢俱與空間使用的需求,反而要在這些心靈反應的脈絡下,經過巴氏所謂的「場所分析」,才會顯現其現實意義的來源。
我們透過巴舍拉所說的將想像聯結到作家童年誕生的房舍,以及在其中的幸福感的體驗,就像體驗到對世界的原初信賴感。這種原初的信賴感不可能不建立在一種「受庇護」或「渴望在其中受庇護」的秘密心理反應上,雖然現實情狀可能並不盡如人意,但這種心理反應是跨主體的。對家屋地窖、家園陰暗角落中感受到的恐怖感和夜晚時分對黑暗、暴力的畏懼,恐怖空間體驗雖說不一定跟個人過去的經驗有關,它或只是一條導火線,藉以觸發個人內心深處『廻蕩』的感覺,而產生共通的記憶樣式,卻能引起樣貌各異的原型心理反應。
王潤華書寫橡膠樹,華人就跟它一樣,在同一個時候被英國人移植到南洋土地上,然後紮根開花結果,為當地帶來文明與經濟繁榮。〈在橡膠王國的西岸〉裡,王潤華描述站在南洋歷史上第一棵橡膠樹下,內容提到一些具體的地點,這些地點往往勾起作家對童年往事和個人社會關係的記憶。這種情形似乎就如巴舍拉所說的把自己放在一個夢的狀態裡去,把自己放在一個日夢的門檻上,把自己棲身在過去的時光裡。也就是說,作家的記憶往往是與地志空間聯繫着的,而且是在生活的事件中存在着情節與人物的關係。因此,當他談論這個地方的時候,他就會唱起關於這個地方的思鄉曲,會寫下渴慕這個地方的詩句,就像一個戀愛中的人。
記憶負載著的膠林迷思
英殖民政府引進大量中國及印度勞工從事橡膠種植,使之適應南洋環境,從而改善馬來西亞民族的生計。許多華人及印度人曾經靠它養家活口。而膠林深處,也是馬共游擊隊出没的地方。這在不少的馬華作家筆下,經常以橡膠為意象,寫出作為「國族寓言」的馬華文學特色。而王潤華體驗到的無疑是一種膠林迷思,如〈夢裡的橡膠林〉:
「但這些日子以來,在無數個夢裡,我都曾回去當年黑暗不見天日的苦難鄉村,夜襲的鄉村還恐怖地響著,手榴彈爆炸時的紅光還亮著,還有面黃肌瘦的割膠工人。是在這樣的一個黎明時的暴風雨中,我默默的告別了陰沉沉的橡膠林,不久馬共的英軍的炮火就燃遍了那西海岸的橡林,媽說從此無名河常常飄浮著小舢舨似的屍體,年青的我不能再回去……」
無論是詩抑或散文,在氣氛營造上,膠林陰森不乏恐怖現實,像潮濕溽熱的南洋雨林、四面八方埋伏的凶猛野獸、被外人介入的生活、徘徊不散的亡靈。對王潤華的記憶而言,這是一種疲憊不堪卻又難以避免的存在狀態。黃錦樹認為「雖然童年的記憶是甜美的,這一點只從文章的小標題可以看出來,如〈回憶起神秘的叢林生活〉、〈雨季裡的打架魚〉、〈喜歡打獵和打架的豹虎〉、〈釣螞蟻記〉,在恐怖的現實中穿插甜美的記憶,藉著童年的記憶來驅走現實的恐懼,藉著回憶的治療,便更徹底的遠離林中的黑暗。回憶替代了夢,在往昔夢中的鄉土上。」
誠如王潤華認為的橡膠樹不但把華人移民及其他民族在馬來半島的生活經驗顯現得淋漓盡致,而且還同時把複雜的西方資本主義者的罪行敘述出來,也呈現了殖民地官員與馬來商人在馬來半島進行的壓迫等殘忍勾當。因此,橡膠園這一意象在馬華文學中,歷久不衰地成為作家結構華人移民遭遇與反殖民主義者的載體。
因此,橡膠樹幾乎散發着一股吸引力,它為作家蘊藏了巴舍拉所說的「庇護範圍的內在的存有」。而重要的是,就在這樣的背景之上,人文的意涵,生長了出來。位於膠林,抑或雨林,不管是時間或是空間,都孕育著一種超現實感。這對新世代馬華作家而言,在在提供了巴舍拉所說的「空間癖」(topophilia)的根源。
巴舍拉認為遙想的回憶,只會藉由給予事實以幸福的意涵、幸福的光暈,來召喚它們。一旦這種意涵被抹除之後,這些事實也就蕩然無存。某些非現實的東西,悄悄的滲入回憶的現實當中,而回憶其實是處於我們個人歷史和無以名狀的前歷史之間的灰色地帶,恰恰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灰色地帶,跟隨我們的腳步,童年的家屋走進了我們的生命來。巴氏的言論讓我們理解到作家童年的家屋其實無以名之。它似乎被失落在世間的一個地方,但又為作家成長提供庇護和心靈安頓。因此在空間的門檻上,在時間的斷代之前,我們其實是在對存有的取得與存有的失落之間徘徊。
文化記憶和傳奇混合體
有鑑於在馬華文學研究裡,橡膠並不是個受重視的議題,但膠林一度是比蕉風椰雨更為普遍的「馬來亞風光」。王潤華在這種前記憶的狀態裡,膠林經驗卻是紀實的。通過膠林書寫,雖然不曾在現場目擊,但試圖想像拼湊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父輩奮鬥、左翼鬥爭、國家霸權的壓抑、叢林中的反抗、庶民生活的悲慟等種種的事實具有回憶所賦予它們的意涵。起碼在王潤華認知中,橡膠林便具有美麗而恐怖的魔力。
在《南洋鄉土集》裡,王潤華對神秘性的橡膠園,流露出恐怖意識。夜間的恐怖,源於黑暗的林中所有樹的姿容,匿藏著所有被攻擊的可能。加上老虎吃人,日軍殘害老百姓,婦人吊頸,鬼的傳說,似乎都是發生在橡膠林裡。
「橡膠樹是我最熟悉最感到親切的熱帶樹木。」它經過某種想像的衝擊,而興發出一種存在上的改變,深深打動了王潤華。於是,如巴舍拉所說處在廻蕩的震撼之中,依據自己的存在處璄而訴說詩意。從巴舍拉的觀點來看,對於某個意象所產生的共鳴,比較接近精神上的奔放狀態,比較接近知性上的聯想,而不是存在上的整體震撼。這時候,詩歌和意象就徹底佔領了我們,深深打動了我們的靈魂,讓我們受到感動。
於是,我們跟隨作家處在廻蕩的震撼之中,依據自己的存在處境而訴說詩意。我們會以為自己體驗過這種詩意,甚至以為自己創造過這種詩意,有了這種深切的感動之後,所謂的共鳴才會接著出現,在發生共鳴和情感的反響之中,我們的過去被喚醒,我們把自己過去的
相關經驗跟小說和詩歌意象的典型特質,在知性上發現到這些特質其實潛存在我們過去的許多生活經驗脈絡中。
無庸諱言,王潤華這種「南洋書寫」本身肯定了生命的離奇經驗,其和地方生活、獨立人格的生成過程的深厚聯繫。這與帕特里齊亞‧隆巴在《羅蘭‧巴特的三個悖論》中評論羅籣‧巴特的想像世界,出現了好壞兩種意象的表述是相同的。他認為好的意象放縱在這個想像世界是一個有魔力的詞語,它充滿了個人與文化的記憶,在這個世界中,形式如波濤一般前行,包括生活的形式、自我的形式、人們閱讀、渴望以及書寫的短語的形式,還有生存現實的形式。
王潤華筆下的橡膠林,就是一個好的意象,當它處於文學上一個來來往往的意象領域時,就像一個在變幻莫測的舞蹈編排中跳舞的舞者,它具有積極的價值。同時,王潤華用自己的學術生涯來衡量南洋所有一切,也就是說,用他自己的寫作來衡量,而且他還賦予精神對
象或者是理論概念、實體對象或者現實形式以同樣的認知價值。我們似乎可將王潤華「南洋書寫」重視的「與膠共舞」看作拉康式的想像世界中最卓越時刻的「鏡像期」。(1) 亦如橡膠林充滿了王潤華個人與文化的記憶和傳奇的混合體,「都有一種不可測的夢境深度,而個人的過往會為這個夢境深淵添加特別的色彩。」(2)
(1) 拉康認為遠在一個嬰孩能在語言中識別自我之前,遠在能使用語言之前,它就能夠認得自己在鏡子中的影像。見其《我的功能的形成之鏡像階段》。
(2)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空間詩學》,台北市: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7月,頁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