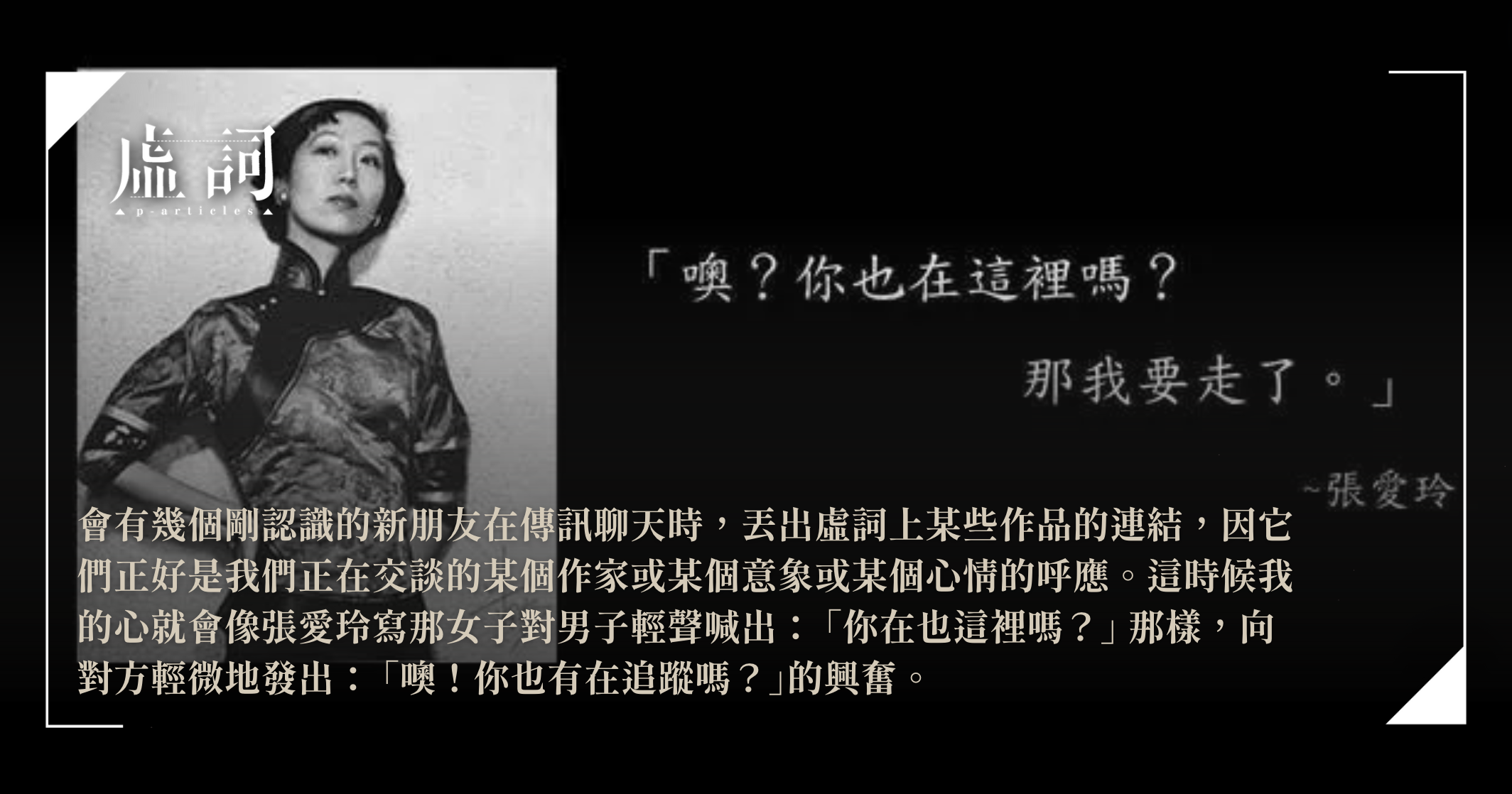【虛詞・◯】虛詞。是愛我們更多的那人。
散文 | by 張瀞 | 2024-05-04
我在台灣。初次遇見虛詞,是2023年的八月夏季某日,亞熱帶無風的教師辦公室裡,同仁正管教學生。我鍵入「辛波絲卡」。螢幕跳出數個搜尋結果,其中之一是作者雙雙為虛詞舉辦的辛波絲卡活動而衍伸出的一首詩——《新詩課上的白日夢》。當時被其中幾句詩句深深地打動,像開頭:
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上課時在窗外尋找電影裡的黑貓
勝過分析我偏愛的詩句
或中段
我是貓
一身凌晨的顏色
在籬笆安睡到醒時--------
貓於課室外牆上伸懶腰並輕巧走過的情景跳入眼前,並帶來凌晨的清涼。即便我的眼前並沒有貓也沒有清晨,而是試卷、汗水、正確答案、跟師生衝突。看貓,豈不比解析課文或句子對生命來得更有益處?我讀進了詩,詩也讀進了我。我再點選網頁上其餘的作品連結,意外地發現了一個高質量的登載文學作品的網站。於是在那個公教人員的下午,我按下臉書追蹤鍵像按捺下一個大拇指,此後演算法如潛意識般日日推送我虛詞上的文章,我很理所當然地在日常生活裡擁有它、被它啟發、並感到快樂。知道在這個星球的某處有一小群人天天都在寫出美麗的作品,也有地方可以刊載這些美麗與創意。這使我感到高興。
我收藏虛詞並沒有跟任何人說。當然。因我的生活中大部分人關注的並不在此。偶而,會有幾個剛認識的新朋友在傳訊聊天時,丟出虛詞上某些作品的連結,因它們正好是我們正在交談的某個作家或某個意象或某個心情的呼應。這時候我的心就會像張愛玲寫那女子對男子輕聲喊出:「你在也這裡嗎?」那樣,向對方輕微地發出:「噢!你也有在追蹤嗎?」的興奮。彷彿是在異星上兩個來自同樣星球的人的相認。我們的心靈來自相似的原鄉。
四月初無預警地得知虛詞的實體紙本劃下句號,把我一下子拉回2023年底在台灣經營40年的幼獅文藝熄燈消息時的低落心情。這個休止符來得突然,彷彿正躺著享受著音樂家的演奏呢,突然便金石人鼓聲俱歇。然而,幸好,虛詞的電子版運作仍在進行(這讓身處台灣的我鬆了一口氣)。因此我想,即便這個標點「。」標示了結束,但僅只是句子與句子之間暫時的斷點。只不過是這句與下一句的主旨或時機不同,作家用了一個「。」來分開,但文意仍然持續,劇情、人物、對話也依然在進行。「。」是暫時的停頓、像獅子撲擊時後腿的後退,那稍稍的暫停,是為了更大的力量蓄積。
而一個個連續不間斷的「。」也使我想起靜坐數息時,每一個深呼與深吸之間的停頓。每一個閃現過的雜念中的空白。而每個停頓與空白都將我們拉得更深、使我們與靜謐和真實更接近。2023年Jon Fosse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我也是從虛詞上得知的。當時,阮文略先生譯了四首詩,其中一首是《山忍住呼吸》。當天,我正在批改學生的英文翻譯,學生翻譯著一些乾巴巴的中文如:「你是不是對每天吃同樣的東西感到厭煩呢?」之類的句子。阮文略先生寫道:
深呼吸
於焉山佇立
於焉中山佇立
及中山於焉佇立
.
.
.
.
當天與海
撫和擊
山忍住呼吸。
我忍住呼吸,想像自己是座山。在選擇、填空、閱讀測驗、與英語教學間忍耐並等待。因為知道自己是誰,所以能夠忍耐。然後佇立。
生命中所流過的,就讓其通過吧。不論天陰、天晴或暴雨。無論有多少不喜歡的現實發生,致使人們必須後退、按捺、偃旗息鼓,但那不過是重振前的累積與凝結。
文學遭遇的現實使人氣餒,但編輯與讀者對文學的心意如山、堅持如山、信念如山。句號只是每一個氣息深吐深吸間的暫停,可以下潛得更深,在那裡,在乎的、真正重要的事物巍峨豎立、且永不塌陷。
最後,我想用一首同樣透過虛詞介紹所得以認識的詩人的詩句來作結——
威斯坦・休・奧登《愛得更多的那人》
當星辰以一種我們無以回報的
激情燃燒著。我們怎能心安理得?
倘若愛不可能有對等
願我是愛得更多的那人。
謝謝虛詞,以一種我們無以回報的愛燃燒,謝謝虛詞,是愛我們更多的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