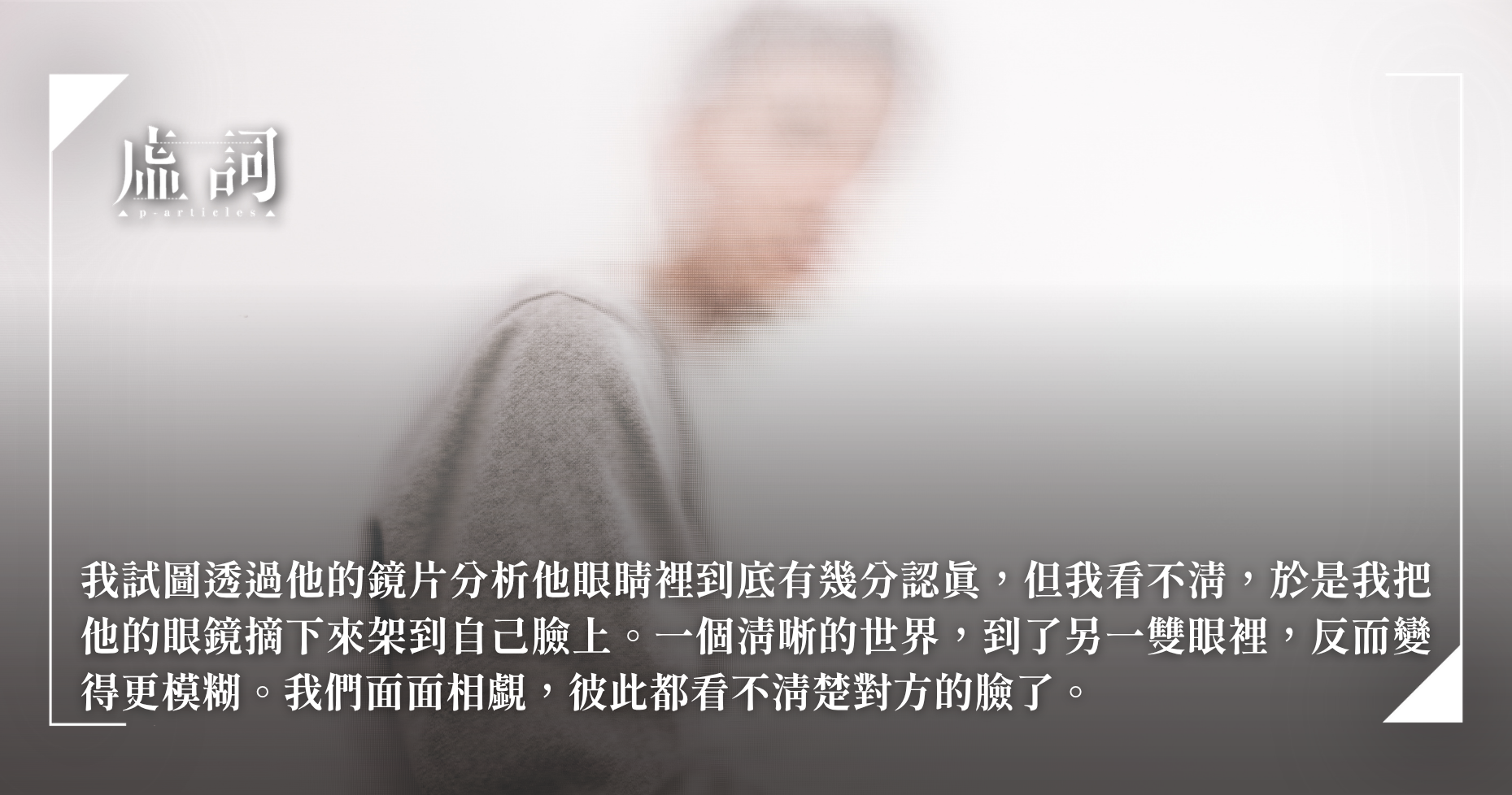Heathcliff
散文 | by 俞宙 | 2025-10-24
小時候最害怕測光了,總是對測光儀裡的山頂小屋有種莫名的恐懼。如果那一團紅色屋頂模糊,就說明視力加劇。成年後雖然摘掉了呆板厚重的眼鏡,乾眼症卻愈來愈嚴重了。
和他看的最後一場電影,是 1939 版的 Wuthering Heights。那天他戴來一副框架眼鏡,因為我上次隨口說好奇他近視的樣子。
「我已經決定離開這裡,去 T 城。」電影中途,他突然對我說。
(Cathy: Heathcliff, make the world stop right here. Make everything stop and stand still and never move again.)
我試圖透過他的鏡片分析他眼睛裡到底有幾分認真,但我看不清,於是我把他的眼鏡摘下來架到自己臉上。一個清晰的世界,到了另一雙眼裡,反而變得更模糊。我們面面相覷,彼此都看不清楚對方的臉了。
「和我一起離開吧。」他說。
「離開之後呢?」我問他。
(...Make the moors never change and you and I never change. )
「我們還在一起,會比在這裡更快樂的。你可以繼續寫書啊。」
(Heathcliff: The moors and I will never change...)
「要不要再養一只垂耳兔?」
「想怎樣都可以。」
「但我們兩個都只喜歡做飯,誰來洗碗?」
兩個人笑作一團。未幾,他的表情黯淡下來。
「你還是不相信我。」
(⋯Don’t you, Canthy?)
「你知道嗎?我好愛你的鼻峰。」我轉移話題。
(Cathy: I can't. I can't...)
「從來沒有人讚揚過我的鼻峰。」
「我好愛你。」
(...No matter what I ever do or say, Heathcliff, this is me now, standing on this hill with you. This is me forever.)
春天結束的時候,他像 Heathcliff 一樣永遠離開了我們的城。
*
一整個夏天我都在閉關寫作。在書店上上下下,試圖找到一本最符合心情的書,撿起一本粗略地從頭翻到尾,埋首於文學的斷簡殘編,使自己無暇他顧,同時妄圖在頁與頁之間抵達別處。譬如另一座城、精神力比多、生命之燃點,諸如此類,文學成為我最仰賴的戀人。
我的快樂朝不保夕,讀書是我防止自己繼續枯槁下去的干預,對抗畸零生活的笨辦法。偶爾也想起他來。等到這陣猝然的思念消彌,只剩下想要踡伏起來的困頓。
他剛離開的那陣子,我們互相匯報近況,接著無話。如此反覆,直至緘默和死亡一樣變成命定。
「最近好嗎?」
「還好啊。你呢?」
屏幕亮起蝕穿我的臉。如果不能擁抱,這輪對話不過又是一個新的閉環。
又在我們告別的小徑佇足。傍晚的公園森冷幽冥,幾乎把我抹去了。成群的飛蟲在路燈的光源傾瀉的範圍內四散又聚攏,我穿著黑色連衣裙裹在他的外套裡,又把小時候關於蟲子的噩夢講了一遍。影影綽綽間他總是在我右側,而我獨佔他的左肩膀。
晚風掠過膝蓋,抬眼他就不在了。忽然感覺好凍。想抽根煙,在包裡翻找半天,結果只摸到一隻打火機。
我揉了揉眼睛。一個淡出生命的人,就好像驗光儀器裡的坡頂小屋。愈是看不清,就愈要費力地瞪大眼睛。等到看清之際,眼裡已經迸出幾滴乾澀的淚水。
*
獨自去聽一場鋼琴音樂會。演奏者是一位日本鋼琴家,留著光頭,肌膚蒼白,一套寬大的白衣白褲在他乾瘦修長的身體上顯得空空蕩蕩,薄如蟬翼的襯衫清晰地印出他的肋骨。
他向台下的觀眾欠身,介紹接下來要表演的樂曲,靈感來源於他不久前做的一個夢。他在琴凳坐定,燈光霎時由明轉暗。一束慘白的聚光燈打在他的身上,整個人愈發透明,好像一不留神就要消融在光裡。演出開始,他近乎癲狂地捶打著琴鍵,赤足踩踏著踏板。有時整個人就要伏倒在琴案上,有時又猛地站起,脊背大幅度地佝僂,頭顱垂落胸前,雙肩在琴鍵反作用力的施壓下震顫。
我閉上眼睛,試圖一窺鋼琴家的夢境。我看到一個人在隧道裡朝前方出口的光源奔去,光源不斷在收束。那落跑之人的身後升騰起無數魑魅魍魎,就快要壓過他。最低音和最高音同時奏起,就快要奔向終點時,忽地落到最低音,出口消失於光點一閃間,整個隧道晦暗下來。鬼魂層層疊疊壓上來將他抽筋拔骨,風卷殘雲地吞併。
一曲終了。我睜開眼,跟著其他觀眾一齊鼓掌。坐在隔壁的西裝男子,突然湊過身來,與我搭話。此前我從未注意到他的存在。
「你也聽到了吧。」
那人的臉上露出邪氣的笑。
我盯著他鼻峰那截熟稔的突兀恍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