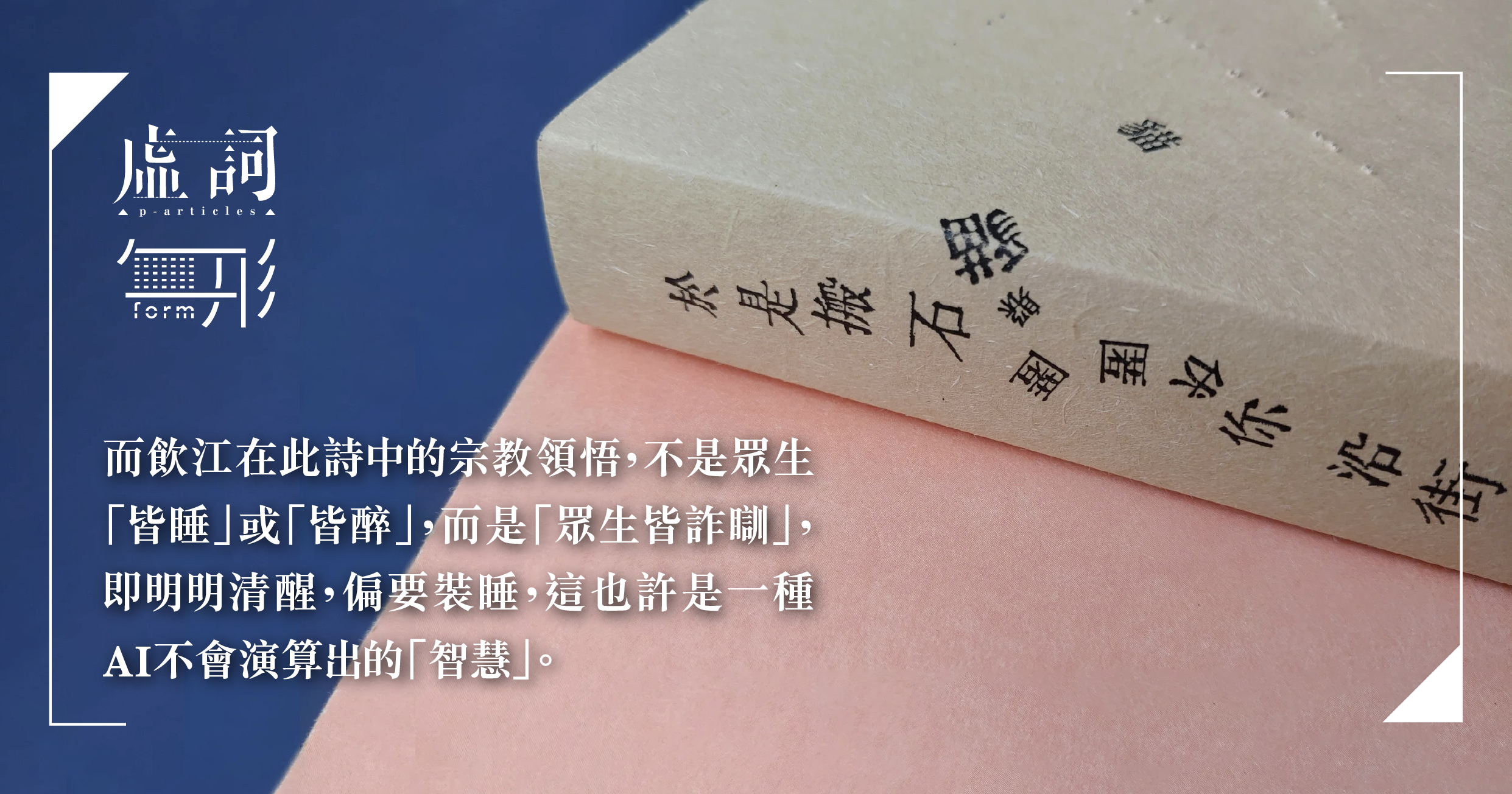【無形・到底拖延過甚麼事】讀飲江《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
去年飲江把自己的舊作、新作,湊合成兩本詩集,一本是中英對照的《搬石﹕飲江詩選》(以下簡稱《搬石》,譯者為謝曉虹與James Shea),另一本是《於是搬石伏匿匿躲貓貓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以下簡稱《於是》),後者還分為甲版和乙版兩種裝幀。《於是》這個書名,沿襲飲江詩集標題的一貫邏輯﹕他的第一本是《於是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然後又選取了第一本一些詩作,加上一些新作,變成《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現在再加上「伏匿匿」、「躲貓貓」在「於是……燈飾」的括號裡,好像想令這個formula變得遊戲感重一點。的確,飲江的詩表面上就像一種語言遊戲。
關於飲江本人,他的詩,其實已有很多人評論了。比如廖偉棠在《浮城述夢人》中說他的詩「其中有弔詭,是非邏輯的,貌似西方哲學的詭辯,但又像東方襌宗的無理頓悟。表面幽默的詩歌中卻有絕望、虛無感隱藏很深」。後來洪慧在文章〈【飲江專輯】咁唔係好爽咩:讀《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引用了廖這番話,並提到絕望、虛無,「對人世間各種愛恨荒謬的通達和諒解」。另一位論者陳澤霖在〈【飲江專輯】論飲江詩作的基督宗教符號及粵語運用〉中提到,飲江以粵語、白話混雜的對話,「並置不同義類的詞語及對立的意念」,使其「能如基督宗教符號在詩中的對話一樣,以製造眾聲喧嘩的語境,甚或是困境。」
對於飲江詩的評論本就汗牛充楝,任何附加的評論只會更嫌累贅,就如我們無時無刻談論宗教的時候,基督教會經常引用約翰福音開頭的話﹕「太初有邏各斯,邏各斯與上帝同在,邏各斯就是上帝。」我們都不是上帝,可是我們往往喜歡討論這個「邏各斯」,邏各斯也是上帝的權能,因此討論邏各斯也就彷彿親近了上帝,其權能,及其承諾帶來的愛、救贖等。飲江的詩經常談到上帝、死亡,這不是偶然的,在無盡的絕望和虛無中,只有永恆的上帝才是對懷疑論者一切話語「在言說上」進行的解答,至於現實或實踐層面,上帝是隱蔽的,不積極參與世界事務的,人只能在言語中感受其救贖、恩典和權能,這對生活在東亞社會的飲江和我們來說,更是如此。
讀到《於是》的時候,讀者很難不停下來思考飲江的神學觀念,相比之下,《搬石》的抒情味、家庭書寫的味道更重一些。然而在《於是》中,上帝也經常讓位於AI、阿法狗(戰勝所有棋手的AI下棋軟件)。AI作為飲江形而上詩歌(除上帝外)的另一個客體,與作為人類的「我」處於較為平等、有情的關係中。也許,如果上帝都不出手救世的話,AI就是我們人類的救贖,我們都要感謝未來AI對人類文明的規管。說到這裡,人類讀者不期然會感到絕望,就像逃不了必有一死或者被宰制的命運﹔但反過來,把人類從一個妄自尊大的世界管理者位置釋放,回歸動物性,何嘗不是一種解放﹖
對人類來說,作為人類的我,作為阿法狗的AI,和上帝本尊的關係,說穿了也就是一種我與你的關係,我與你的關係是互補的,其中一方不能缺少另一方而存在。書中收錄了飲江早期的詩作〈遇合〉,引用猶太教哲學家馬丁‧布伯《我與你》中的話﹕「不可思議的,我們棲居於萬有相互玉成的浩渺人生之中。」甚麼是「相互玉成」呢﹖為何這「相互玉成的」,是一個「浩」「渺」的人生呢?翻譯令人想到很多層次,人的浩大和渺小,是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關鍵是詩中的我發現了一種「勝於中子彈」的東西。詩中用「中子彈」是因為中子彈不會摧毀武器和城市設施(即人類的工具),它只會讓人類和一切生物窒息而死。而這裡「勝於中子彈」的東西,大概就是指「我與你」之間相互玉成的關係,致使我「該」「立刻打電話給你」,讓「我們」「拿起六弦琴/傾聽,而且歌唱」。詩中也道出寫詩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一個「你」的存在﹕「……與其寫詩/而沒有回答,不如做夢」。
這種「我與你」的關係,發展到後來,越發透過宗教寓言的方式得到體現。陳澤霖在文章中認為,運用宗教符號和口頭粵語是飲江詩的特色,他還指出飲江詩中經常出現對立意念。其實,只有運用詩人本身的口語及思辯性的矛盾修辭時,將詩歌置於干涉上帝干涉和人類存在經驗的戲劇場景中,宗教經驗才變得更具體,更不抽象。然而飲江詩中的「我與你」並不是人與上帝的關係,很多論者指出飲江的上帝是一個命運般的主宰,詩中「我與你」的關係反而建基於「有情」的條件之上,而作為AI的「阿法狗」,正是詩中其中一種「我與你」關係的展現。
布伯的《我與你》影響很多猶太學者和作家,詩人策蘭是其中一位深受其影響的人。他在詩作〈讚美遠方〉(Lob der Ferne)裡寫道﹕「當我是我時,我是你。」(Ich bin du, wenn ich ich bin.)對於父母死於集中營的策蘭來說,寫詩就是一種重新相信「我與你」之間的關係,相信曼德爾施塔姆所說的「詩歌漂流瓶」關係,甚至將「遙遠」的你(讀者)視為私密的我。對飲江來說,書寫AI是否意味着與無生命的「你」建立這種互相關係呢﹖我們在〈我夢見無人駕駛飛機〉裡讀到這種嘗試。
詩中寫到,當我探訪「無人駕駛飛機」時,它應門時問「是誰?」時,期望它像我一樣聽到這句「是你」然後開門的我,卻沒有得到預期中它開門的效果。因為它仍是它,因為它只是一架「無人」駕駛飛機,它沒有帶這種互惠關係期許的主體性。
無疑地,它是物,在物的世界中,物無所謂而存在;只有在人的世界中,物才為人所用而存在。海德格說的「物」,比如梵高畫中的農民鞋子,是在「有人」的框架中。
故此,我還需要一個「佢」(他)去召喚物件。在最後一節,我們可以讀到﹕有我,有你,有佢,於是「無人駕駛」飛機,起飛了。
然而在很多時候,這種「我與你」的關係只不過是詩人一廂情願的想像,就像其中一首詩題為〈阿法狗給自己的情詩〉,由很多首像俳句一樣的短詩組成,當中想像AI邏輯縝密故戰勝自己,如「AlphaGo囉囉攣/是它戰勝自己/的原因」(其三),而戰勝自己和別人,最終也變成「無敵的寂寞」,(其四)這樣寫道:「贏咗盤棋算甚麼/那個人/連望都沒有/望我一眼」,甚至「除了盤棋/沒有誰知道」所以它「哭了」(其五)。然而筆鋒一轉,從這種「不被理解/的哀傷/和尾隨理解/之遺忘」(飲江詩〈佢當然會回來〉句),領悟到命運之決斷不會取消命運本身(〈其六〉:「骰子一擲/永遠取消不了骰子」)但「偶然/會取消偶然」(其七)。後面還提到上帝不擲骰子,但懷緬抽陀螺(十六),返學唔點名。至此,讀者方知「寫給自己的情詩」其實是阿法狗的「自傷」,以阿法狗的「精算」能力,可能還敵不過如上帝擲骰般的偶然。
更多時候,「阿法狗」僅只是作為一種無特定含義的人物借代,如〈奇蹟集之最難喚醒〉,以「最難係喚醒詐瞓嘅阿法狗」開頭,戲謔地表明,「算無遺策」如「阿法狗」,如果它「詐瞓」的話,定必比凡夫俗子更難喚醒。這背後源於「你無法喚醒裝睡的人」這個政治梗,但飲江把這個梗提升為「詐瞓嘅人喚醒詐瞓嘅人」,以美國民粹總統特朗普及美國人為喻:
最難係詐瞓嘅阿法狗
喚醒詐瞓嘅特朗普
最難係詐瞓嘅特朗普
喚醒詐瞓嘅美國佬
而且後面不單說到喚醒,還提到詐瞓的人愛上詐瞓的人,並認為這是一場災難。
然而所謂「災難」,也是一道奇蹟,因為「我們在詐瞓中做愛,我們在災難中相親相愛」。這一代人類處於AI發展,自詡生活在和平、繁榮和科技進步中,又何況不是「詐瞓」呢?但每一場天災人禍中,我們總是以互愛哄騙自己,令我們感覺良好,也許這也是「詐瞓」的表現。
此詩影射另一位詩人黃燦然的詩集。黃燦然說﹕「《奇蹟集》對我而言是奇蹟。毫無準備,毫無來由,毫無預兆。」頗有宗教領悟的意味。而飲江在此詩中的宗教領悟,不是眾生「皆睡」或「皆醉」,而是「眾生皆詐瞓」,即明明清醒,偏要裝睡,這也許是一種AI不會演算出的「智慧」。飲江也在〈無伴奏18段之對牛彈琴和子謙〉(其一)中譏諷上帝的「扮」:「向上帝撒嬌是容許的/祂扮聽唔到」。詩人從「對牛彈琴」引申「對上帝彈琴」,認為兩者是差不多的。人對牛彈琴,牛扮聽不見,那上帝扮聽不見甚麼呢?其三提到「牛鬥豬,豬鬥牛」可視作勞動者與不勞而獲者之間的鬥爭,而上帝扮聽不到牛的呻吟其實是要眾生和好,上帝的回答是有點模棱兩可的「未嘗不可」。讀者也不妨想想,到底是上帝對眾生無動於衷,還是上帝對眾生猶如「對牛彈琴」﹖
這些詩一貫飲江詩中的自嘲況味,而飲江的嘲諷從來沒有特定對象,甚至可說是以所有人及眾生(包括牛、阿法狗)的存在景況為嘲諷對象的。有一首詩名為〈出門去(沙之書)〉,當中第一句就是「人生七十玩泥沙」,爾後飲江又以「人生七十玩泥沙」為題,寫了〈人生七十玩泥沙之聖愚(扑頭記)〉及〈人生七十玩泥沙之玩唔過(離魂記)〉。「玩泥沙」本身有「兒戲」的意思,但〈出門去(沙之書)〉就像飲江很多其他詩作一樣不易讀懂。後面的「注」有解釋寫詩的背景﹕詩人和「神仙朋友」一起慶祝他的七十歲生日,詩中說﹕三個神仙送他三個願望,「三根蠟燭點亮了/願望就會得實現」,然後詩人想叫一個五歲孩子,去尋找火種。這孩子也許就是幼年的他,當中他回到對母親的想念﹕「果然母親早已把/火柴放進口袋裡」,有趣的是,那三個神仙朋友都各自找口袋看看有沒有火柴了。
後來飲江的廣州朋友林江泉問他有冇看過芬蘭導演阿基.考里斯馬基(Aki Kaurismäki)電影《扑頭前失魂後》(A man without a past)和《波希米亞窮巷》(La vie de Bohème),於是又有了詩作〈人生七十玩泥沙之聖愚(扑頭記)〉和〈人生七十玩泥沙之玩唔過(離魂記)〉。《扑頭前失魂後》講述一個男人因意外突然失憶,《波希米亞窮巷》故事源自普契尼歌劇《波希米亞人》的故事,兩首詩卻分別以聖愚和瞻仰自己遺容為主題。詩人在注中杜撰導演阿基被頒發終身成就奬時,被上帝「扑頭」的故事,把「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改成「人一思索,人一拍戲,乃至試圖拍戲,上帝就扑頭。」的「箴言」。可見飲江何止質疑上帝,何止「製造眾聲喧嘩的語境,甚或是困境」(陳澤霖語),他簡直以上帝為人類恆常面對的宿命。
書中還有很多詩作,有些按名稱是系列之作,如以「蝦球與阿娣」命名的系列,如一一詳述,頗費周章。飲江的詩用字通俗淺白,但要解讀一點也不容易。這些詩,與其說容許自由詮釋,不如說是拒絕詮釋,詩中不斷建構又不斷解構意義。飲江的幽默即建基於這種不斷建構又不斷解構的嘗試上,說是幽默,又飽含諷刺,充滿絕望,又充滿禪意,總之拒絕較明晰的答案。與二十年前的作品如反戰的〈黃金分割〉比較,《於是》的近期作品確實如此。這也許是一種晚年的心態使然,當然答案是開放的。飲江愈來愈偏向於深刻地呈現實相,有另一種境界,令飲江的詩更難被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