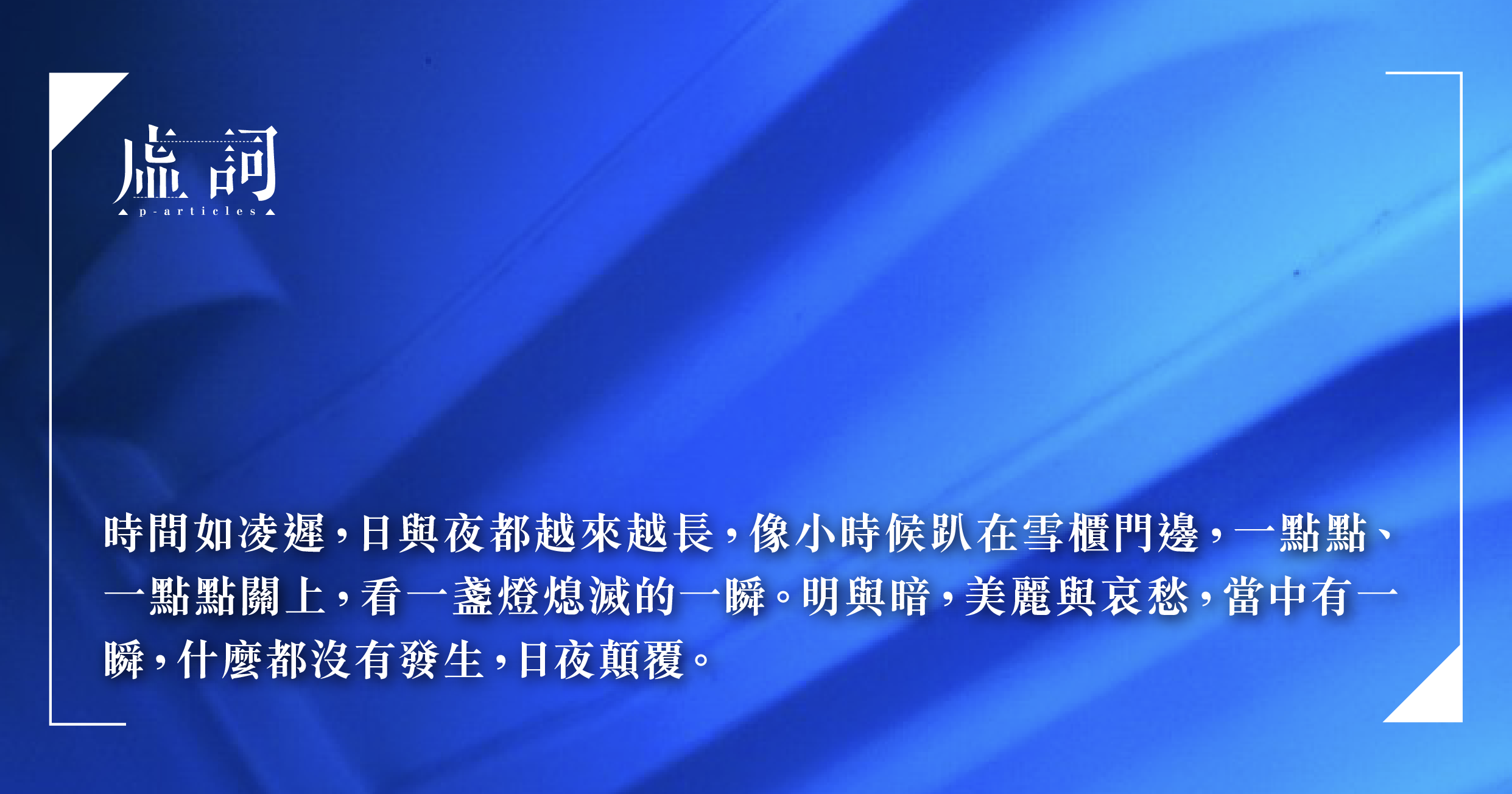【虛詞・到底拖延過甚麼事】還
哪吒析骨拆肉,還父還母,小時候我聽過這故事,好痛。我想這終究會發生,只是我一直拖下去,像欠交一份功課。
我想摸一朵花。我在畢業前後開始夢到,花瓣透明,長在窗台外牆的縫隙裡,伸手過去,它的花瓣會貼過來摩挲指骨。我每天夢醒就趴過去看,母親在後面吸一口煙,說,日日望,望乜撚,養你咁撚大就係等你日日望窗。她穿吊帶小背心,風吹過時鼓動。我見著她從三十歲到五十歲,瘦了好多,皮膚像放久了的蘋果一樣逐年乾癟。這些我們家一般不會丟,由它放到爛。其實店裡辭她那天她看起來和平常一樣,收工時蘇姨給了她厚厚一疊錢,裝在信封裡,沒有說其他話。她那晚買了盒燒鵝回來,第二日沒有去上班,躺在床上,一整天不開燈。
我該找一份工作。但我讀垃圾科系,不知道可以做什麼。
齋叔偶爾會上來。小時候在骨場,等鐘的時候他會過來教我做功課。有時回到家,他在廁所裡沖涼,哼着歌,聽起來很愜意。
出來見到我時會主動寒喧兩句,畢業了打算做什麼,哎呀你阿媽終於等到你大個,之類的。我嗯啊應答,轉頭看父親,他坐在輪椅上,看著窗外,好安靜。
後來我還是找到一份文職,在一間大公司,朝九晚六,負責處理購買物資。每種物資都要準備四份文件:原收據,會計的出數單,經理的審批紙,物資的登記報表,然後一起交給經理簽名。我的座位在辦公司的最角落,看不見窗,日夜之間沒有過度,像關一盞燈,嗒,世界便暗。有時覺得餓,便知道快收工。
那個夢越來越頻密,密到有時我分不清,以為自己睡醒。
每天早上,我見沒有花,便推父親去洗澡。他虛胖,肥肉鬆弛,掛在骨上,吊吊揈。記憶中從小他就是這樣。小時候參加學校軍訓,教官要同學與父母蹲在地下,手搭肩走路。他坐在石壆,擺擺手說,我太肥啦。教官繑手站著,像沒有聽見一樣,大大聲訓示其他蹲著的人,一、二、一、二。我轉過頭看他,他整個人躺下,肉攤在壆上像化掉的雪糕,我便低頭專心蹲着走路。
好像他就是一個又肥又老的人。我生來見他已是這樣。
最後一晚,每個家庭圍著自己起的爐火,要說心底話。
他說,「我爲咗你先過來呢度受苦。你知唔知,我以前膊頭有三條金線,在海上,手下有兩隊人。」
我說,「我早幾天和小東絕交了,因為他講阿媽壞話。」
他說,「大洋船,你有沒有見過,三根煙囪,幾十噸貨,那些死窮鬼在下面搬貨,眼巴巴地看著我,幾時輪到我要踎係度行。」
我很少跟他說話。自他跌斷膝頭後,要我幫他洗澡。骨縫癒合後,他都走得不太好,醫生說這很難復原,他便要整天坐輪椅上,晚上睡在旁邊的沙發,方便挪動。幫他洗澡他會開始說以前行船的事,「南非那些窮鬼地方最好,你有無做過,十口靚(1)歲的雞,下面啲毛細細」,滿頭泡,他睜開眼縫,說,如果不是你出生,我還可以玩多少年你知道嗎。我搓洗他的陰莖,短小軟爛,像稚子。
早上的地鐵,擠在人與人的夾縫中,我百無聊賴翻電話相薄,它有個位置會播起以前的照片。原來軍訓那年,他頭髮黑黑,笑起來紅光滿臉,不顯老的樣子。我忽然在想,他現在一整天會做些甚麼。
我的頭莫名開始痛。
我刪除了那張照片。
頭越來越痛。單據的數字混在一起,我揉一揉眉心,得出去買藥。經理在門口剛送走他那個來巡視的高層,見到我出來便問,你進度怎樣?我頭太痛,有點敷衍地說,差不多了。他戚眉,你知道我還有兩個星期要上總部匯報你手頭上那堆報表,我現在還甚麼都沒見過。我痛的沒辦法,點點頭,路過他便推門出去。
吃完藥很暈,回家那一程車,頭皮神經跳動如舞鞋踏地,影子晃動,到處是喧譁,巴士外面是海,浪潮沉默,我閉目皺眉,很專心地想像顱內痛楚的實質形貌,這樣會好受一點。
繞過陰冷潮濕的走廊,門內罕見地有聲音,我聽不太清,像我父親母親在吵架。我記得他們好久沒有說過話,有預感或有甚麼要發生,只是此刻我只覺得這天好長好長,十分渴切地想睡一睡,我開門後就徑直走回房間,他們像沒有看見我,繼續吵。一躺上牀就昏睡過去。又夢見那朵透明的花,好遠好遠,我見到有個我拔起那朵花,一片片捻下花瓣、枝葉,地上又長出新的一朵,我又再拔。我低頭,看不到自己的手、腳或身體,只能遠遠見到有個我,蹲在那裏,來回拔花。
好像有聲巨響。
詭異藍光在眼斂游動,我緩緩清醒,不知怎的好悶焗,脣乾舌燥,汗微溼,衣服粘身如繭。我內心忽爾莫名驚恐又欣喜,不想起身又睡不着。我瞇眼,門底縫隙透光,一切安靜,他們吵完了?腦裡一潭死水,一思考便覺渾濁。我躡手躡腳下牀,慢慢推開門,母親坐在窗邊,低首吸一口菸,廚房那盞燈在她側臉,微弱閃動。
父親坐靠牆邊,嘴角到衣襟大片大片的血跡,混合唾液鮮紅遲緩地流動。我慢步走出門,他一見我,憤怒又焦急地嚷叫,嘴裏都是血沫,語言粘連,滿是嗚呀嗚呀的聲音。
「報了警,警察和救護車一會就到。」母親坐在窗邊,點一點菸頭,菸灰簌簌落下。
我站在父親面前,看着他坐在輪椅上。他好小好小一個。我伸手抹他臉上的血,放在鼻尖前,腥的鐵鏽味,我舔了舔,問他,痛嗎?他有點呆滯地看着我,像突然忘記怎麼說話。
母親被警察帶走時什麼都沒說,雙手小小地環抱著自己,如此嫵媚,一瞬間我以爲她回到三十歲,剛做骨妹的時候。
醫院打給我,說,沒大礙,嘴內壁割破,屬皮肉傷,倒是進來後一直說自己有很多貨在越南等上船,這裏都是海盜覬覦他的貨,臨牀診斷有精神分裂,建議入院治療。
我心想,他不記得自己老了。嘴上說,好。
母親保釋候審,有禁制令,不能接近這裡。蘇姨知道這件事後在附近給她找了個地方,裡面只有一張按摩床,枕頭位有個洞那種。怎麼,現在覺得我有兩分姿色了?她說。
蘇姨說,我沒別的意思,你安心住。
頭一直痛,吃了好多天藥都沒有好的跡象。時間如凌遲,日與夜都越來越長,像小時候趴在雪櫃門邊,一點點、一點點關上,看一盞燈熄滅的一瞬。明與暗,美麗與哀愁,當中有一瞬,什麼都沒有發生,日夜顛覆。經理經常有意無意就走到辦公室裡,跟同事說日子怎樣怎樣近,還有這些那些未準備好。同事們一臉惋惜,說在努力了都在努力了,待他走後轉過頭撇一撇嘴,說,對這裡數他最忙,忙到天天過來告訴我們他多忙。
我想像父親在精神病院裡,他在追悔玩少幾年雛妓的日子,然後看到我現在在這裡聽他們說話的樣子。這樣想可太快樂了。
有晚好夜有人敲門,開了門,齋叔兩手搓磨地站在外面。見是我,問,你媽呢?我說,她搬出去了,沒跟你說嗎?喔是這樣,他遲疑一會,遞給我一個信封,說,那你幫我交給你媽。說完就走了,急急腳。我想,怎麼離棄一個人的方式都這樣媚俗。
因為這封信,我得去找我母親。她爛泥一樣躺在床上,滿地都是空的威士忌酒瓶,細小房間,到處是厚濁的泥煤味,聞到想嘔。她看到我來,幾次想撐起身來。我說你好好睡,我走了。她說,那怎麼行,兒子難得來看我,好歹要給你做頓飯。
她搖搖晃晃去了廁所旁邊,用電爐煮了幾隻急凍水餃。我把東西給了她就低頭吃。她打開,看完後沒說什麼,雙手到處摸,摸到酒瓶就往喉嚨倒,有些剩幾滴酒。她摸到一瓶滿的,扭開蓋子開始灌。別喝了,我說,她停下,打了個嗝,繼續灌。我伸手去搶,她甩開我幾次,見我沒有停手的意思,她隨手拿起一個空酒瓶丟過來,我側頭,酒瓶撞在我身後的牆上,碎裂,一塊很小的碎片劃開手指,滲出一點點血。
小破孩,你又是什麼爛臭B,也配拿我的酒。絲兒盡會吃豁皮,拿抓兮兮的小破孩,不是你?如果他媽的不是你?
她的眉漸漸扭在一起,反胃幾次,然後嘔了一床。我坐下來吃完剩下的兩個水餃後,扶著她去廁所。水管漏水,嗒嗒聲,燈泡滿是黃垢,滲著稠渴的光。我褪去她的衣服,她的身體越發瘦削,到處是骨骸形跡。好像自我出生以來,她的身體就不住地瘦下去,一直向內塌縮。
收拾乾淨酒瓶與床單後已是凌晨四點。我抱著一箱威士忌回到家。三小時後要上班,坐在沙發上托著頭,外面月光清寂,風好香。
我看著外面的夜逐漸隱約,被煙霾淹沒般的灰色。涼水與月、沈默與暗室、思索與遲疑,日光一點點噬咬暗處影子,天便越來越明亮。
我一直無法看見,便以為日夜這不過是開一盞燈。一種來臨永遠要蠶食與掠奪原本的存在,生命日漸薄弱。
如今我見到你。
那天上班的路很輕快,頭不再痛。所有的單據文件忽然都變成一種舞步,中午前我就整理好拿去經理房間。他不在,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個圈,見不到他。我回到辦公室,問近門口的同事,他頭也沒抬,說,董事之後有事,他一早就過去總部了。
他面容瘦削,嘴唇很厚,穿著一件過大的灰色西裝外套。我想起了,第一日上班他跟我說,他叫David。
我在經理的房間放下文件,拿起背包便走了出去。經理剛剛回來,在門口叫接待處的人幫忙組織來年工作展望的會議。他眼裡目光興奮,我想像到那是一場順利的匯報。
他見到我路過他,徑直走出去,他看一看錶見還未到食飯時間。喂,你去邊,一陣要開會。我回頭微笑,大叫,我祝你今天生活愉快。
回家那程巴士我好倦睏,窗外大海微微翻動,水色幽藍,上面有好幾艘大貨船緩慢行駛,一箱箱貨五顏六色地堆疊。我遠遠見到一個又一個的自己,在碼頭點算四張不同的單據,父親站在船上,戲謔地看著我笑。
到家後我喝了好多威士忌,世界遲緩,我想點菸,火機在窗臺位置但我怎麼伸手都夠不到。我笑了。電話響起來,一個陌生的號碼,我按開擴音,父親的聲音,他的聲音壓到好輕好輕,喂啊仔,今晚我會坐貨車走,到附近時你記得來接應我。我無法遏止我的笑意。
「我話你知你唔好以爲咁就甩難啊!你欠我咁多!你還一世都還唔清啊!」他忽然咆哮,然後電話裡的聲音越來越遠,一邊叫着放開我。電話掛斷,一陣嘟嘟嘟的聲音。
我走到窗邊,灌了一大口酒,嗆到,酒灑到整件襯衣都是。我叼着煙,去摸火機,打了幾次都打不著,我甩了甩火機,再打,火一下竄上來,襯衣猛烈燃起。
我慌亂地把它脫下來丟到一旁。
我像老狗一樣趴在窗邊,遠處有光,我眼睛好澀,打不開。好久,再睜開時,低頭看去,嘴裏的煙不知什麼時候掉下去,以奇異的姿勢,夾在一朵花中。夢中那朵透明的花,花瓣如指骨,在外牆中微微搖曳。風吹過時,煙口亮起餘火的光。
我緩慢地退後,坐到地上,模糊裡,日光如煙,周圍一片清冷。我大口大口喘息,漸漸息止。
微弱的,啪嗒啪嗒的燃燒聲從屋裏傳來,像有人在細細囈語。
我看天,這天甚暖,是個好日子。
1)因網頁字型所限,「口靚」一字以拆字形式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