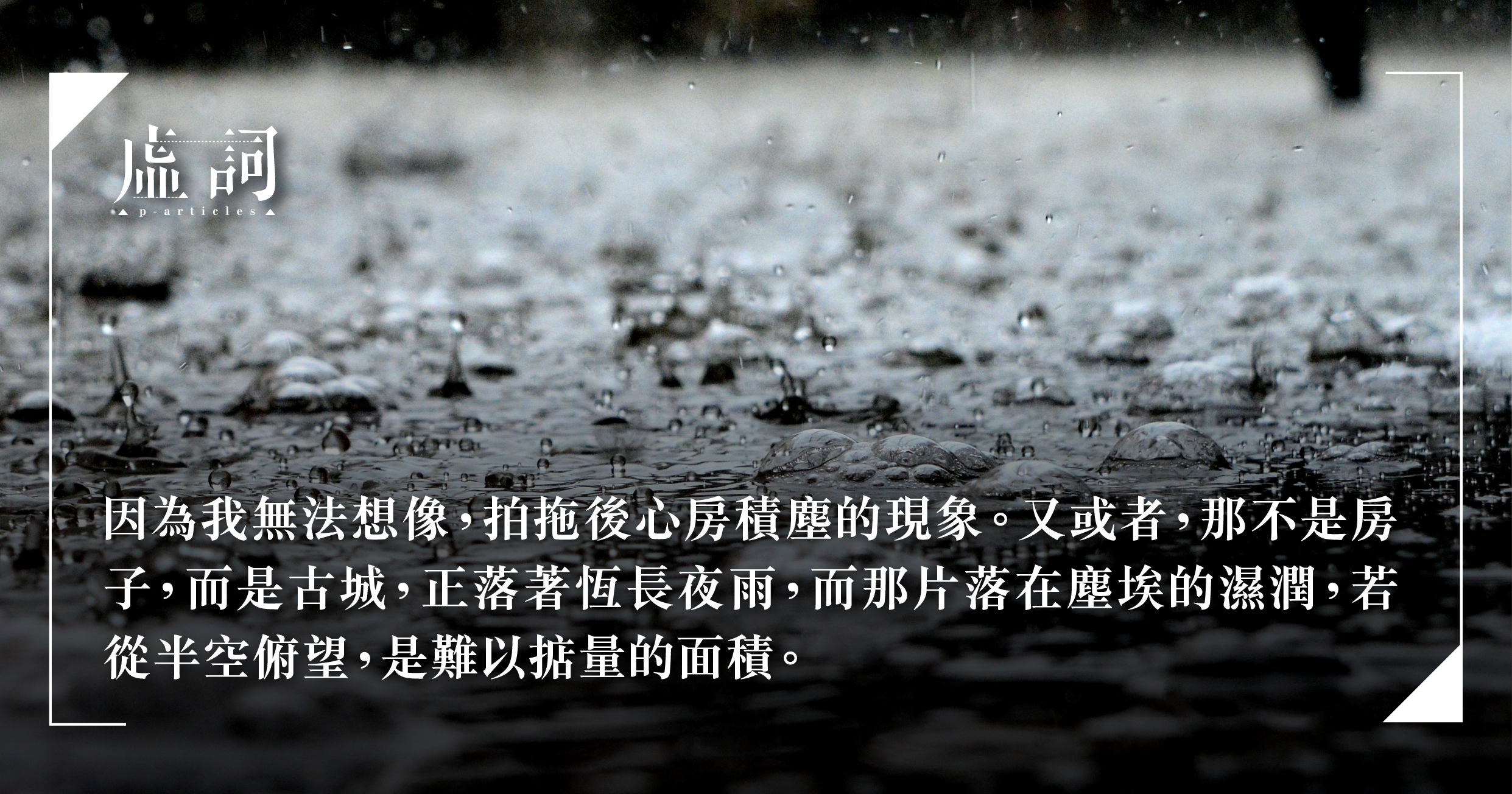姊妹
男校男生的愚笨,之所以顯露赤裸的本質,是沒有異性的緣故。未能戀愛,運動便成了消遣。下課鈴響,他們跑到地下的室外籃球場,我則在課室外的走廊,望著陽光下,他們肌肉的鍛鍊。肌肉的牽扯,是源於大腦向身體發送訊號,所以我總認為,隨時而過,他們腦內的神經也會不斷撕裂、變厚,最後堵塞,接近中風。譬如,在中三的地理科長洲實地考察,三日兩夜,他們朝我與F居住的二樓雙人房的窗扔碎石,為的,是想試探他們的妄想:打擾我與F在夜晚發生關係。無論是這件事,抑或流傳於同級之間,我與F的戀愛謠言,都是朋友B告訴我們的。對於扔石的行為,F的反應是,「我後悔無叫得大聲啲。」他在走廊叫了幾聲,銷魂地,像被劏宰的雞,我們笑得胃腹絞痛。朋友B認為,相信謠言的人很荒謬,因為他覺得我與F會「撞號」,沒有戀愛的可能。
原來於某些人眼中,戀愛,就是性的意思。這讓我憶起那班讓我徹夜失眠的扔石者。
所以有時,我想念女性的敏銳,無論那是出於直覺,還是觀察所得的結果。偶爾,天會藍得很乾淨,連雲與太陽也被抹去,但我們仍在,在教員室門口,與高中中文老師笑著東拉西扯。當扯到我們身上,她說她一直覺得我們「糖黐豆咁款」,似姊妹。我與F愣著對視,莫名興奮傻笑,大概是因為,她在我們以這段關係的答案為恥之前,主觀承認它的輪廓和存在。而對我而言,姊妹的關係,宛若兩片唇瓣,之間滿是說不盡的話,但又可選擇長久地抿著,陷入類似睡眠的狀態,而這反而是最親密、自然的時光。所以,這兩片唇是不分上下的──只要將視角扭轉九十度,就能看見,在牀上依偎的兩個人,正一左一右地寐睡著。
到十八歲,我與F畢業。我要重考DSE,他升大學,不久便戀愛了,各自地戀愛。他與二十多歲的男上班族拍拖,我則戀上一個三十出頭的男人。F說,他有種聯覺:我心動即他心動。我有同感,就像以靈魂的方式,參與原本僅屬兩人的戀愛。這是我們經常相約見面,分享與對象的發展進程和聊天內容的緣故。後來F開始抽煙,我大概猜到他是跟誰學的。而我,只敢想像自己也會從胸腔呼出煙霧。有時是柴郡貓毛髮的顏色,質感美幻,幻後的結果卻是,褪成霧白色,如塵灰,彷彿我也不自覺地抽起真正的煙,在這潮濕帶罨味的空氣裡。起塵,不全是積存已久的緣故。因為我們想宣洩的,正是塵埃本身。
我還是比較擔心F。因為我無法想像,拍拖後心房積塵的現象。又或者,那不是房子,而是古城,正落著恆長夜雨,而那片落在塵埃的濕潤,若從半空俯望,是難以掂量的面積。所以那傍晚,商場的天台花園,當F提到男友想在三十歲前結婚,請原諒我不可置信的反應。F享受與之親密,認為結婚是延續關係的需要。於是,我幻想自己出席婚禮:當站在F身邊,無論他穿的是白婚紗抑或黑西裝,我「姊妹」的身份,名銜上又會多複製一層,卻帶著全然不同的意義。日隱天沉,我挨著觀望台邊緣,盯著F近十秒,他不迴避,對視之間的眼睫隱沉著墨紫色,在撲動、呼吸──有能力翩飛,卻選擇停駐的,一抹輕雅的生命。我一陣戚然。與不捨無關,只是,我疑惑那個他是否適合與F廝守偕老。我記得,當F告訴對方自己想做老師,對方卻直言F反應遲鈍,難以應付,「有學生想跳樓點算?你救到佢?」過分赤裸的言辭會造成挫傷,又正因,那只是挫傷,於是血只能在軟組織下,沉默地發紫。出於公平原則,F沒批評我的愛,我自然也沒資格勸說甚麼。旁觀者清的道理,F怎會不明白。
F形容過我與他的人生觀。他自言是火車,眼前是鐵路路軌,偶爾遇著分岔路才會考慮轉換方向。至於我的世界,F說那是一片地,沒有路。他沒強調我的存在形式,但他說,自由是我的本質,這讓我生起飄蕩的幻想:浪花煙雨冥王星,我可以成為任何物事,到頭來,又可能甚麼也不是,連同我視野所及的一切──包括婚姻。我未能想像,會否有那麼一個人,會讓我變得像F,願意來回越海渡洋,為的,只求一紙透明婚書。
後來F結束了一年半的感情。煩惱,離我們很遠很遠。
某晚臨睡在枕邊碌IG,看見一個帖子說,舞台劇《短暫的婚姻》會在明早出售「終極尾場」門票。當刻轉發給F,是源於直覺,現在回想,大概是出於對婚姻話題的延伸。又或者,我只是想將非真實的悲劇揉進自己的創傷。情緒的無形與彈性,有時會讓人產生短暫的共享錯覺,哪怕這是一種貶抑,因為當某些物事能與他者共鳴,就代表自己已屈服於與眾同等的平凡,縱然事實是,任誰也背負著獨特的故事。這種褻瀆會對不起自己,又稍微,放過了自己,正如待劇目亮麗謝幕,我的悲傷多多少少會連同劇場的燈渾然熄滅。而F或許也有這種需要。
過了一陣,F facetime致電我。那端的他穿著白背心,天花的燈泛著便條紙的黃,附在他的身,肩膊反光,臉有點黑,但隱約能看見他皺眉。他問我有沒有看清公演日期。1月15號,禮拜日,又是夜晚,可謂完美。「OK!姊妹決裂!」F按著太陽穴搖頭。我沒有頭緒,開始思考1月有甚麼特別日子。忽然意識到甚麼,才用手指算數字:24號,減9……我恍然,F笑道,下年一定要立即記得他的生日。這句話,他由中一說到現在大四。但我知道他會明白,對於不擅記生日日期的我,從自己的生日為始,再以扣減的方式記得他的出生,已非常難得。F對生日有份堅執,二十多年來,他生日正日都要與親人在家度過。但F說,下年的廿二歲生日是特別的,因為待年輪又轉一圈,他就不再是「十八廿二」。
「我同屋企人諗住生日嗰晚BBQ,想叫埋你同你屋企人。」
「我唔要雙方見家長。」我笑言。我偶爾會與他家人碰面,但兩個家庭相聚還是頭一次。F的家庭有七位成員,都很友好,只是熱鬧得讓我有點不自在。若再加上我父母親,我大概會下意識嚴陣以待,演變成災難,或者戰爭。
「你記唔記得我阿媽之前講過咩?」我耐不住笑,知道F在指甚麼,「佢話你可以同我一齊啊嘛!」幸福得荒謬,縱然他母親搞錯了對象。這次F向我補回一些細節:當時他和母親在銅鑼灣SOGO附近等巴士,母親應當是看到F傳自拍給我,才說出那句話。也許在她眼裡,此行為令人暇想,就如中學同學有過的想像。只是,當人懷抱著的是善意與祝福,這反而讓我重新思考,我與F有沒有愛情或婚姻的可能。
F的母親覺得,F與我相處時很快樂。但按照我與F的經驗,愛情,至少是踏入婚姻前的愛情,是女性面部的敏感肌膚,一直在發作與治療之間徘徊,期間不時撲粉遮瑕,而在卸妝之前,對方卻一直以此為美。F在拍拖時說過,比起戀人,姊妹反而比較親密。前者的存在是薇甘菊,嬌細無害的外觀,藏著入侵性的佔有慾。於是隱瞞成了手段,為了讓薇甘菊覺得自己是唯一。而餘下的問題僅是,到底能瞞騙多久。F的經驗算不上美滿,我的情況則是,在結束前來不及開始。所以我們茫然,到底有沒有一種愛,是熱烈而沒有隔膜。
我與F偶爾會聊起,待人老珠黃,又「無人要」的話,要一起住姑婆屋。至於地點,暫時的共識是將軍澳近海邊處,相對路闊人少,特別是夜晚。網上的地產廣告介紹過該區有兩層的獨立屋,不知道如果由現在開始儲錢,還來不來得及。我想二樓有露台吹風,在上面種茉莉薄荷百里香,還有怕醜草,閒時逗弄一下。回到屋內,有兩間睡房比較好,縱然F說,我們平日staycation也是同睡一張雙人床,但我次次都睡不安穩。而且以後的F和我,應該會有鼻鼾。一樓,會有大廳廁所,空間應該足以讓寵物活動。我想養東奇尼貓。F想要豬仔,想親吻牠粉色的鼻子。我已經能想像貓逗弄豬仔的樣子,至少小時候會。豬應該大得很快,我怕牠會無意中壓死我的貓,還是希望牠們感情不要太好。要不要將豬鎖在露台呢,但我怕牠會吃光那裡的花草。F說,他會阻止我屠宰他的豬,但他應該忘了我怕血。我頂多會與街市的肉販混熟,再等F某天外出時,讓肉販將豬運走……而實際上,我們連最基本的房價也未問。
應該是,不敢問。
也許當我與F老去,住進這棟房子的生活,會趨於平淡。這其實接近於一般年邁夫婦。所以,這會否是一種跳過愛情,更接近老年婚姻的狀態?不會發黃、起皺,或面臨被撕扯的短暫命運,因為,我們的婚姻不是紙造的。我盯著電話螢幕的F,低炒的視角,他沒有望向鏡頭,手一直噠噠打著鍵盤。接著,停下,舉直雙手往後伸。他大概在寫FYP。
「好唔OK。姊妹點拍拖。」F重新和我聊起先前的話題。
「……Lesbian?」
「係亂倫。」我們失笑,在凌晨近五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