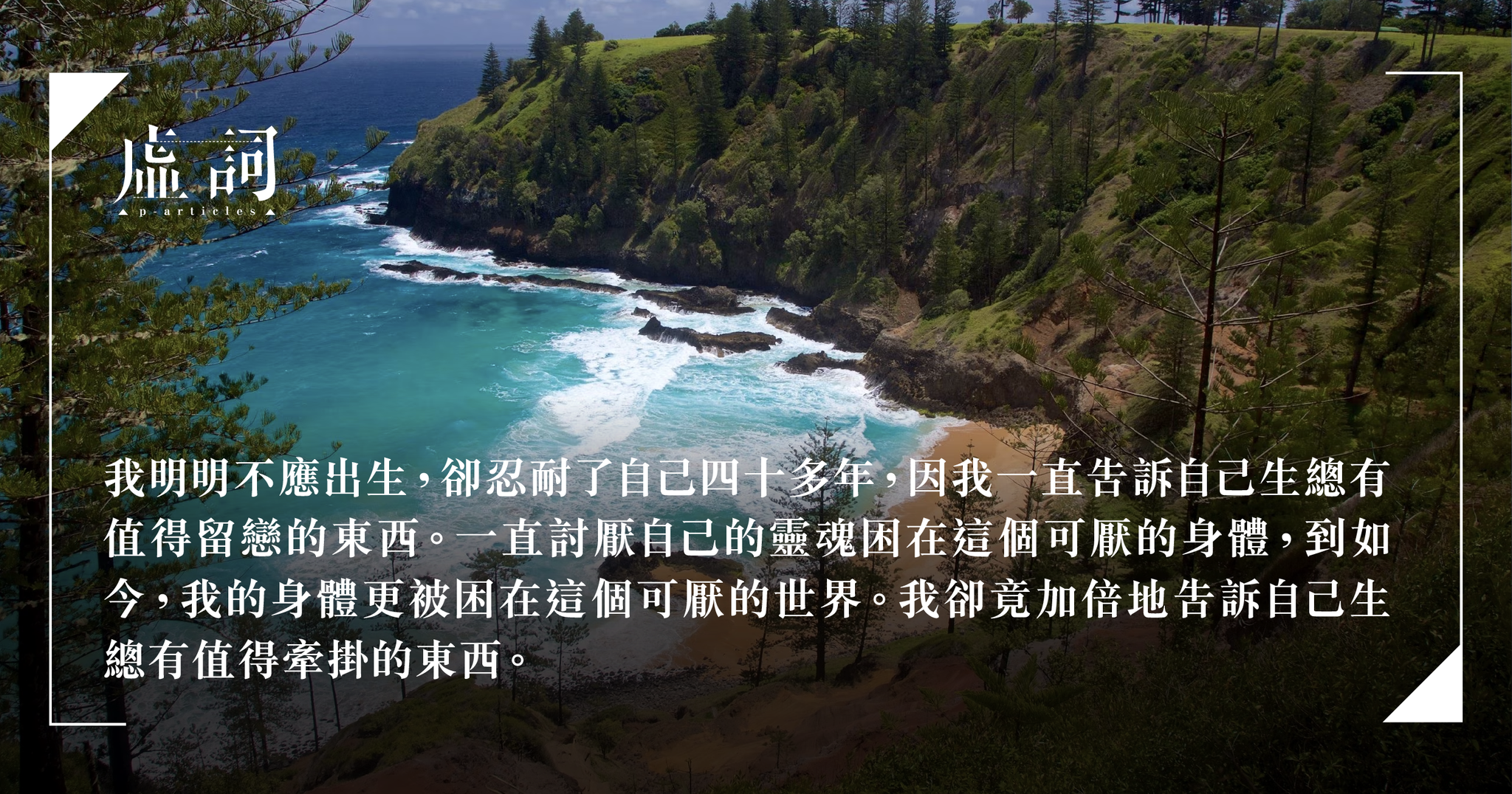冷風院灣
我醒來時,正在結半跏趺坐。我已厭了讀一份閹割了的報紙,報導另一份報紙如何被閹割,然後明天對換。與其往圖書館,看原本有書的地方變成空洞,然然透過這些空洞看另一重又另一重書架的空洞,我還是喜歡看地圖。
我剛發現了一個地方叫冷風院灣。
便領了一把刀,帶了一本書前往。讀書時看H城地圖,灰色的是巿區,上有道路、大廈、公園,復有名字和五彩的標記。綠色的是山脈和郊區,藍色的是港口與水塘。灰綠相間,一切都合乎比例,這是我心目中的H城。以外的地方,我知道H城以北是白色的;往南即賊灣以外,應是甚麼都沒有的汪洋。
許多年後,我發現賊灣以外,還有一列群島。群島之後才是汪洋。群島的其中一個叫冷風院灣,正倉院、三千院、平等院,冷風院是多麼迷人的名字。於是我便帶了一本書前往。
我買了一條生豬腿,穿進上臂,便走進水裏。生豬腿可當作浮泡,餓了可以咬一口,但這樣會減低浮力,是一種下沉與另一種下沉之間的選擇。長輩說那時陸路有機關槍,許多人這樣走水路來H城,變成了殘肢。殘肢在水裏會發漲、漂白,像現在H城的樣子。
我沒有帶任何東西。我要帶一本書來作甚麼。我情願帶一把刀。帶一把刀可以做很多的事。修行七七四十九天不動,那是電視騙人的情節。你道騙人蒙昧良心,有違專業。待此等蒙昧良心的人走後,必無人願意再作此等蒙昧良心的事。但事實願意蒙昧良心的人如此之多,此落則彼起。我已厭了在充滿謊言之世辨識謊言。
修行需要住與吃,最好是帶一把刀。但與其帶一把刀,他們說不如帶一本書。他們說,知識就是力量,沒有人能摧毁一個信念。於是我往圖書館,發現信念原來註銷了就沒有,書架都變成了天窗。所以與其帶一本書,不如帶一把刀砍樹、打獵。
最後我有沒有帶刀呢?請你告訴我。這關乎我日後是否會被起訴的大事。而更大的事是,我恐怕會因為帶著一本書,面臨更嚴重的起訴。因為他們說,書是有力的東西。
*
冷風院灣這個島並不大,甚麼都沒有,只有岩石和樹木。我擇了一塊平地,清除了四邊的樹,建立起一個曼荼羅。曼荼羅裏有草。我坐在草圈的中央,結跏趺坐開始修行。
曼荼羅外邊的樹生得很快,一天可生七點二米高,幾天後我的天空只剩下了一圈,再幾天後只變成一點。我的修行漸漸變成了砍樹,再變成忙於砍樹。我只有一把刀,曼荼羅的圈變得越來越細。
我就像坐在極深的煙囪裏,成為了燃燒之物。樹上落下黑色的果實,掉進我的壇場內。有時一天八十三顆,有時如雨點擊落。下地的果實又旋即生出枝條。這都不是我坐忘就能夠解決的事。留下的話,我想坐忘,不是坐化。我能做的就只有不停砍樹,不停摭拾妖樹的種子,拋出圈外,看著它一下地便旋即生長。
書顯然是沒有用的。掉落的種子,可隨時長成書的模樣。
*
然而我這樣子又怎可以回家。大閘每晚在恥笑我白天忍受自己做隻豬狗,換取以一個人的樣子回家對著孩子。晚上在家裏告訴孩子這個世界有善意,卻在白天裏讓他們離家。任何有點深度的東西,這個地方都已配不上擁有。出街隨時會被崩壞的東西擊中,可以是實物,可以是一個意念,連簷篷也有機會塌下來。他們便索性召來壓土機,把堆積物包括屍身,碾壓成今日平整的路面,成為見報的治績。
討厭自己,與討厭這個世界同一原理;討厭而不作為,也是同一原理。我明明不應出生,卻忍耐了自己四十多年,因我一直告訴自己生總有值得留戀的東西。一直討厭自己的靈魂困在這個可厭的身體,到如今,我的身體更被困在這個可厭的世界。我卻竟加倍地告訴自己生總有值得牽掛的東西。
餵鳥的時候,我被人票控。原來昨天起這城市已不准餵野鳥。昨天我還告訴孩子要有善心,要與社區動物共存。明天起,餵野貓將變成了禁忌,後日是狗,野豬早在去年已經被妖魔化,半年前是猴子。明天我便要提堂,最高刑罰是坐牢一年,罰款十萬。
我喜歡動物。我不喜歡人,不喜歡群居。小時我的志願是一個動物園館理員。我很清楚污穢的工作不只是打掃糞便。還要定時協助獸醫檢查身體,把手臂伸進動物的泄殖腔內;又要協助動物繁殖,套取牡物的精子,然後打進牝獸的陰道;也要處理動物傳染病、傷口以至收拾屍體等。最難過的莫過於看著自己一手養大的動物,只因獸醫一句沒救而處死,而我因地位卑微,只能在旁束手無策,以不作為作為共犯,然後待何時終於寬宥了自己,告訴自己如果我有錢,我可以建築一個地方,讓這些動物活到善終,只可惜我沒有。
大學畢業,我便懷著滿腔熱情前往動物園,應徵管理員。總管見我合適,問我有沒有考本地法律。我問照顧動物需要考法律嗎?他說是的,然後便沒再作聲,擠出很理所當然的樣子,如同打了安樂死針的動物。
我當然沒見成這份工作,以後也不會。我坐下,看著猿拉得過長的臂,我開始懷疑伊甸園也有圍牆。
我明明沒有餵過鳥,我要怎樣回家向孩子解釋明天的裁決?為自己羅織罪名,讓孩子仍然相信世界還是安全的;還是告訴他們我沒餵過鳥,讓他們活在困惑痛苦之中?
這時,林中出現了魔鬼,我在聖經中見過牠。這是我修行的第四十天,魔鬼把羸弱的我帶到樹冠上。
「離開冷風院,回到H城,你便可得溫飽。」
「吃了麵包,就應活得像一個人。」
「反正你也沒甚麼特別,何不接受略施研磨?」
「要把一個人的特徵磨平,必然是向庸才靠攏。」
「活得像一個人,總需要別人為你負上或多或少的代價。」
「不做甚麼與做甚麼一樣,都有代價。」
「代人透支勇氣,有違你所信奉的個人主義。」
「面對惡甚麼都不作,才是徹底的惡。」
「例如代別人祈求寬恕?」
「成就別人必要的犧牲。」
於是魔鬼笑了,顯然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話,牠連試探我的必要也沒有。牠離開了我,我和妖樹種子一同掉下,重摔在曼荼羅裏。
醒來,我發現我被膠紙一橫一豎地貼在舊地圖上,當是我趁我入定時把我自己貼上去的。那時的H城肌理分明,海岸線仍未貪饕的肥腫;大廈尚未怠惰,順著南風彎下一腰贅肉,形成異變的等高線。地圖上建築物的輪廓,就像我記憶中佈滿了伸出牆外的霓虹招牌,呈各自獨特的形,發出各自獨特的光,往整條路的前方不斷堆疊,深邃而和諧。狗臂架和鋼䌫的剛健,那時無人會擔憂它們哪一塊會何時掉下來。
但在數十年後,它們被獸醫斷定為有潛在危險,在一夜之間通通被拆了下來,有橫的招牌、有豎的招牌、有如菜刀的招牌、有如匙孔的招牌、有不規則的招牌、有如梅花鹿的招牌,都委迤路上,等待焚燒。道路上變得空盪盪的,至再無可拆,便開始滅鼠、捉流浪貓、砍樹、掘路、拆樓、大清洗,同時加入道路監察系統,管理交通。在沒有糙面雲的日子,人們在街上可看透腐爛的天空。
我相信我這些經歷都是真的,我多渴望你告訴我它是假的。但魔鬼沒有答話,牠離開了我,我和妖樹種子一同掉下,重摔在曼荼羅裏。
*
醒來,聽到林中傳來呻吟聲。我不覺得那是幻覺,我只是回到了回憶中的那個時間點,只是我無法確認回憶是真的。我來,是請你告訴我時間並未過去,還是我無法前行。是我三十年的苦行仍未走出回憶,還是我的現實只在回憶裏,此後的三十年都是虛幻。此時呻吟聲越來越烈,由急促變得乾涸嘶啞。我變成了一隻不會吐絲的盲蛛,在腹股溝間滑行,我發現了你那顆痣,像一個門鈴。
我不願醒來,否則我只會看見一道永遠不再開啟的門。回憶之貴,在於它並不發生在如今。
*
樹沒有放棄長高,最後的洞天已經關上。我已失去了舊日,也失去了與我相干的雲層,這裏變得一片黑暗,樹從四方八面向我壓迫。
倘立心去睡,不用為夜分得那麼仔細。正如進場看電影,就不會介懷關了燈有多黑。
期待畫面的光,不關燈又怎麼看電影。
如果開著燈看電影,就看不見虛假的正義。
同一個世界,進入電影院是黃昏,離開是黑夜。戲院外,到處都像貼滿了便利貼,到處都是偏離常識的疑問。我不知自己處身於黑的哪一個圖層,只知道我的一舉一動,例如買了哪張戲票、乘甚麼車來、何時離去,都成為了別人的數據。我以為來到冷風院灣就能隱身,逃避那些不屬於我的罪名。
這時來了一隻巡捕船,把我押解下去,罪名是非法入境。冷風院灣不屬H城管轄,正如H城也不再由己,漸漸如珊瑚白化。他們說在我身上起出了刀子和書籍,我不知確實有無。我知我的回憶是假的,我來是請你來確認,甚麼時候的人最喜歡看甚麼的電影。
每個人的樣子都怪怪的,他們都像人。我覺得這只是我的幻覺,請你告訴我那的確是假的。我想請你告訴我修行的人會有不同的相貌,但我已經知道你必將無棱兩可的答案。堅持並無識認,沒有人會記得你堅持過或沒堅持過。修行完我發現自己除了修行,原來一事無成。
23-5-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