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ARCH RESULTS FOR "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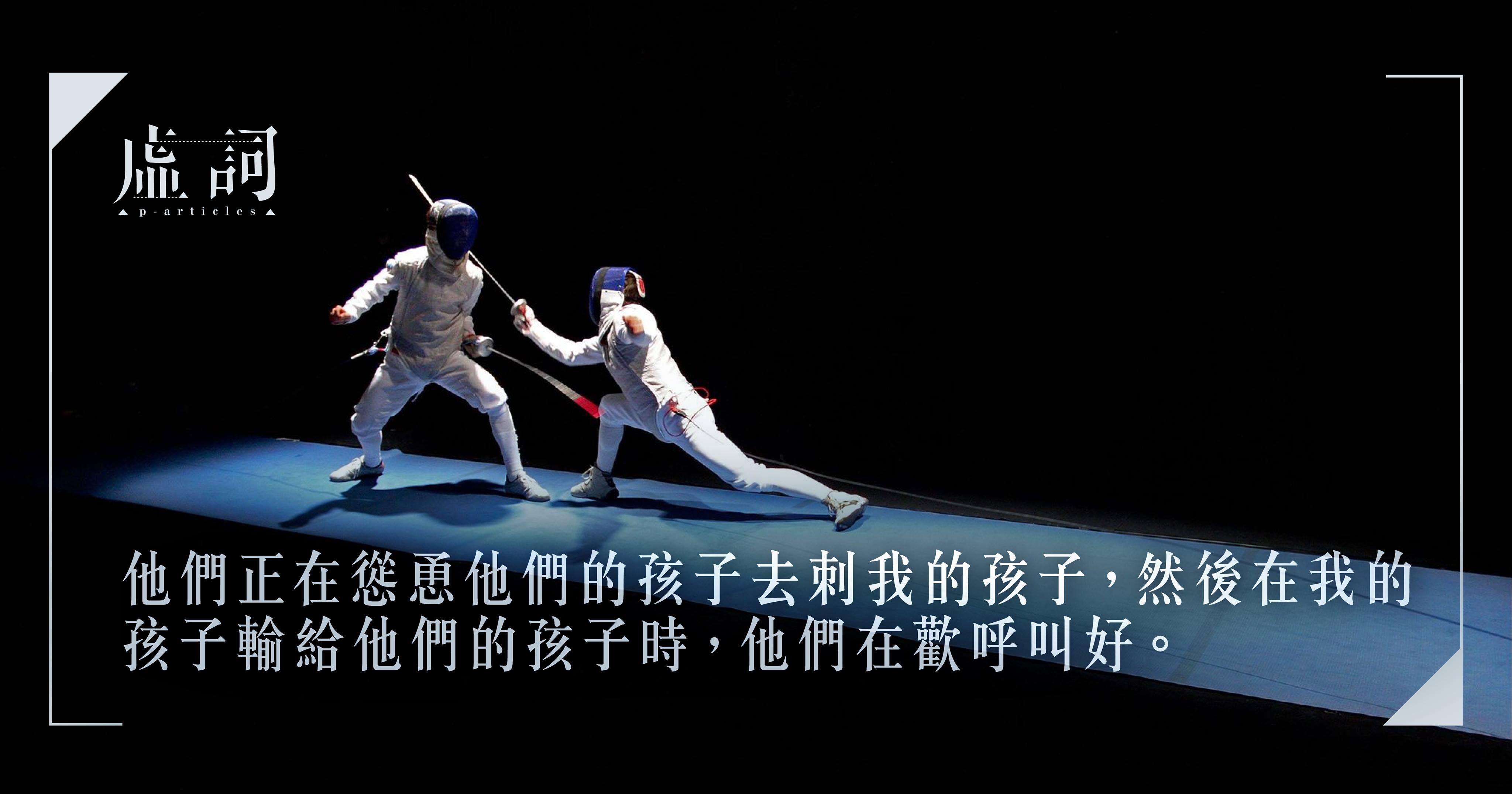
【教育侏羅紀】女兒去學劍擊的啟示
教育侏羅紀 | by 跂之 | 2021-09-24
你有沒有考慮你子女的感受和成長的需要?孩子要的不是勝利,他們需要的是快樂,或者在得一劍和失一劍之間,希望你們沉默。在他們沒有要求你鼓勵的時候,作為家長,又可否沉默一點,讓他們自己去經歷?有時家長會認為無時無刻的鼓勵對子女好,其實任何事情,都只有適時與適當與否,不論讚賞與責備、獎勵與懲罰皆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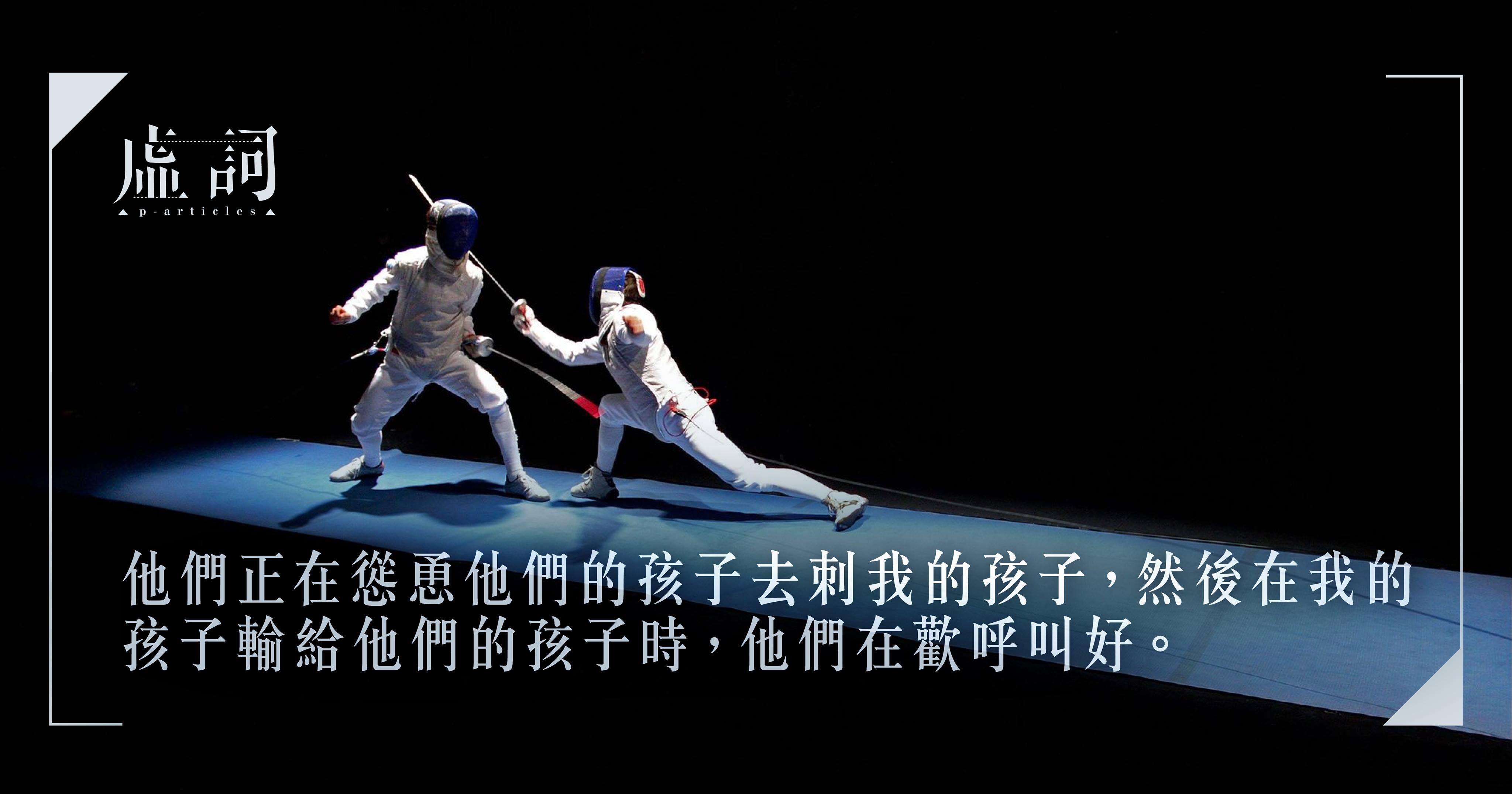
你有沒有考慮你子女的感受和成長的需要?孩子要的不是勝利,他們需要的是快樂,或者在得一劍和失一劍之間,希望你們沉默。在他們沒有要求你鼓勵的時候,作為家長,又可否沉默一點,讓他們自己去經歷?有時家長會認為無時無刻的鼓勵對子女好,其實任何事情,都只有適時與適當與否,不論讚賞與責備、獎勵與懲罰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