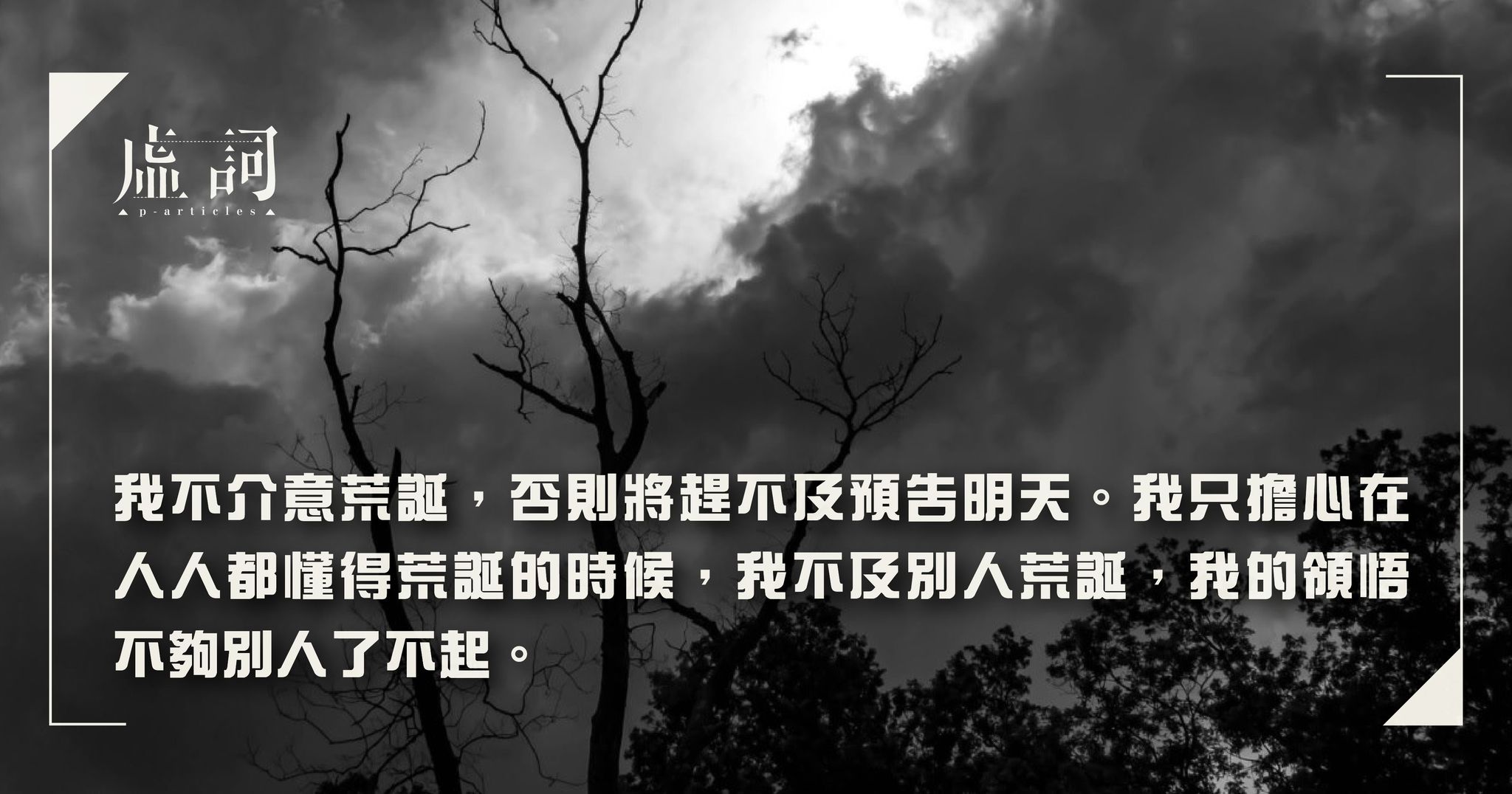當人人都懂得荒誕的時候
對上一次見到他,是三年前他見報後三年後的今天。再次我突然想起他,在網上找他的名字時找到他的照片。他的三肢已完全萎縮,腰板已說不上是坐,而是攤在輪椅上,只剩左手能夠活動。照片中他正激動地揮動他的左手,面目扭成一顆乾棗。計算一下,六十歲的人不應有八十歲的樣貌。
再對上一次見他,是上網剛剛普及的時候,我把牢記著的他的名字輸入。這次他在巴士站前拍照,新聞內容是指他被巴士司機拒載的問題。他用自己的經歷為其他輪椅人士申訴,尋求社會關注。
相片中他大約四十來歲。室外陽光照射下,他的臉尚可辨認,只是苦成了泥土。非止愁苦,而是委屈,一種面對毫無道理可言的委屈。
同樣是訪問,二十年前那張相片,他穿著長袖裇衫。是次這張相片,已幾乎不能說那件是衣服。他的輪椅困在一間擠迫的公屋的正中央,幽暗而污穢。對於一個只能移動左手和面部的人,還能要求甚麼的潔淨。
報道說,每天有醫療工會到他家裏,協助他沐浴時反一反身,然後便沒有了。令我想起我第一次見他,他呼叫護士為他反身,那時他的聲音是親切而有活力的,令我也安心了一點。護士順便拿來抹布為他抹背。他反身後,我發現他後開的醫院服根本沒有綁好,一反身便露出了背部,已潰爛出幾個洞穴。三十年前的公立醫院環境相當惡劣,污穢的外牆、無數的病床、虛設的床簾、擋不住的惡臭、永遠人手不足而無禮的護士,晚上有阿伯終夜在喊救命。這裏只存在恐懼,莫說療養。
二天我便要求出院,因我恐懼。但他仍留在這裏,而他也比我早很多就在這裏,我也不知道他何時出院。
在那兩晚的經歷中我發現,無禮的護士對他似乎特別好。是他年青、富幽默感還是甚麼。後來我長大了總算明白,是因為同情,覺得他的無辜使人震驚。但我知道,這種同情再強烈,也是有限期的,也會因緣份而輕易結束。舊的護士離職,過她們的新生活時,還會回來看病人否。這種關係是萍水相逢,沒有保證,世上亦無甚麼關係和事情有保證。新的護士看見這樣一個長期病人,離他的病因亦越來越遠。
正如我,也只是他長期住院的其中一個過客。他不會知道我仍記得他,我亦不會主動去聯絡他,他能在我身上獲得些甚麼。
他在好市民奬狀上得到甚麼。他領獎的相片沒有甚麼欣喜,只有委屈。三十年後我知道,他那時跟我說的話的確影響了我三十年的人生,但在他個人而言,他正經歷一種樂觀與悲觀的交替。他極力想保持樂觀,因此靠安慰別人去尋求自我的肯定。我知道這樣的構造只是築在沙上,這樣的肯定必然會敗北。
那時我十七歲,讀中六,來年便要高考入大學。我是學校空手道會的主席,下個月便考黑帶。但某天一次普通的自由搏擊練習,把我的下巴打碎為四塊。我吐了滿口鮮血,在鏡中看見下巴已完全彎曲。我盡力嘗試把上下的門牙對齊,告訴自己沒事,但下巴怎樣也無法再合上。
那時沒有手提電話,父母上班後難以聯絡上,又要趕回家替我收拾入院物品。他們來到時我已在急症室獨自折騰了三小時,送我來的教練已經走了。
上病房,我竟被領到一張小孩也躺不下的牆角病床,牆上貼著「dental」字樣。恐怕是像我因「dental」入院的症不多,「dental」科只分到這樣的半張病床。我已撕裂了一吋長的牙床傷口已止了血,我沒事可作,便唯有從書包拿課本出來溫習,那是一本歷史科參考書。
手術是在第二天清早。無稽的我被送到「dental」手術室時,醫生跟我說安排不到麻醉。你這手術本應半身麻醉,但麻醉師要幾星期後才排到期,你的顎骨那時已開始埋口。到時才做手術就要重新折斷它,否則下顎就會永久變型。我現在可以替你打脫牙用的麻醉針,手術過程會很痛、很痛。
醫生好像是在給我選擇。那的確是一個選擇,荒誕的是即使你已沒有選擇,你從來不會沒有選擇。
首先要處理那個一吋長的裂傷,那麼就必須無端脫掉我一隻健康的臼齒。脫嗎,脫。拍的一聲便失去了。然後是縫針,我竟感受得到針頭來回刺穿我的牙床。是的,醫生一開始用麻醉針圍著我的上下牙床打了十數針,但根本完全止不住這種劇痛。他們看到我的拳、我抽搐的腿,他們也明白用一毫米粗的鋼線刺穿我上下顎的牙床,然後扭緊是有多痛。手術的目的是要把我的下顎與上顎固定,讓它用三個月不能張口的方式癒合,而這樣需要動用二十多條同樣的鋼線刺穿我整副上下顎然後扭緊。扭緊的時候是拉扯著牙根與牙根之間毫無抵抗能力的牙肉。
這些全是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進行。手術做了三個多小時,我虛脫了,終於能在失眠了一夜後胡亂睡了一會。睜眼看見此後不久便離家出走了三十年沒再回來的姊來看我。我看見她,我竟大哭起來。剛才做手術我沒喊過一聲痛,但現在我大哭了起來。我是很不忿氣,為甚麼傷的不是傷我的人。為甚麼我口不能張,像盂蘭的鬼。為甚麼我平白沒了一顆牙齒。我不知道來年我怎樣考大學。我不忿為何我的床那麼小,為甚麼沒有麻醉師,而我就這麼大哭起來。
她走後,我又迷糊的睡了一會。起來,旁邊那個病人突然用他親切的聲音跟我說話。剛才的他都看在眼裏,水平的看在他眼裏。
你昨天有想過今天會在這裏嗎?
我別過頭,沒有作聲。他用同樣親切的聲音跟我介紹了自己。他是跆拳道黑帶教練,因幫手捉賊被悍匪在後頸打了一槍,以致身體及三肢癱瘓。
若我有機會再見他面,我不必問他如果有得再選擇的話。
如果他當天不從他的貨車上走下來,他不會拿到好市民獎,妻子後來不會跟他離婚,奪去他大部分恩恤金,把兒子帶到外國不再回來,然而她每從外國回來又會住進他公屋裏長期被她上了鎖的房間,不瞅不睬。若果人的關係有承諾,他的妻子理應願意照顧他,不會在他受傷不久後便離棄他。他卻在離婚後把大部分的恩恤金都贈予她,說是作為對她不起的補償。
還有,如果他不和那個賊交鋒,這個被判十七次終身監禁的悍匪三年前的假釋便與他終生癱瘓的身體無關,與他這三十年的遭遇無關,跟他激動地揮動的左手無關,跟他被巴士拒載無關。
這三十年我讀了很多的書,現在書櫃裏只塞滿最安全的書。也許我們要信教,那麼我們讓洪水浸死時也會感恩。我不介意荒誕,否則將趕不及預告明天。我只擔心在人人都懂得荒誕的時候,我不及別人荒誕,我的領悟不夠別人了不起。不夠荒誕的人只合做平凡的人,像被擠進同一軸承裏的圓珠,滿身是油,為大軸的轉動而摩擦,卻無法摩擦出一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