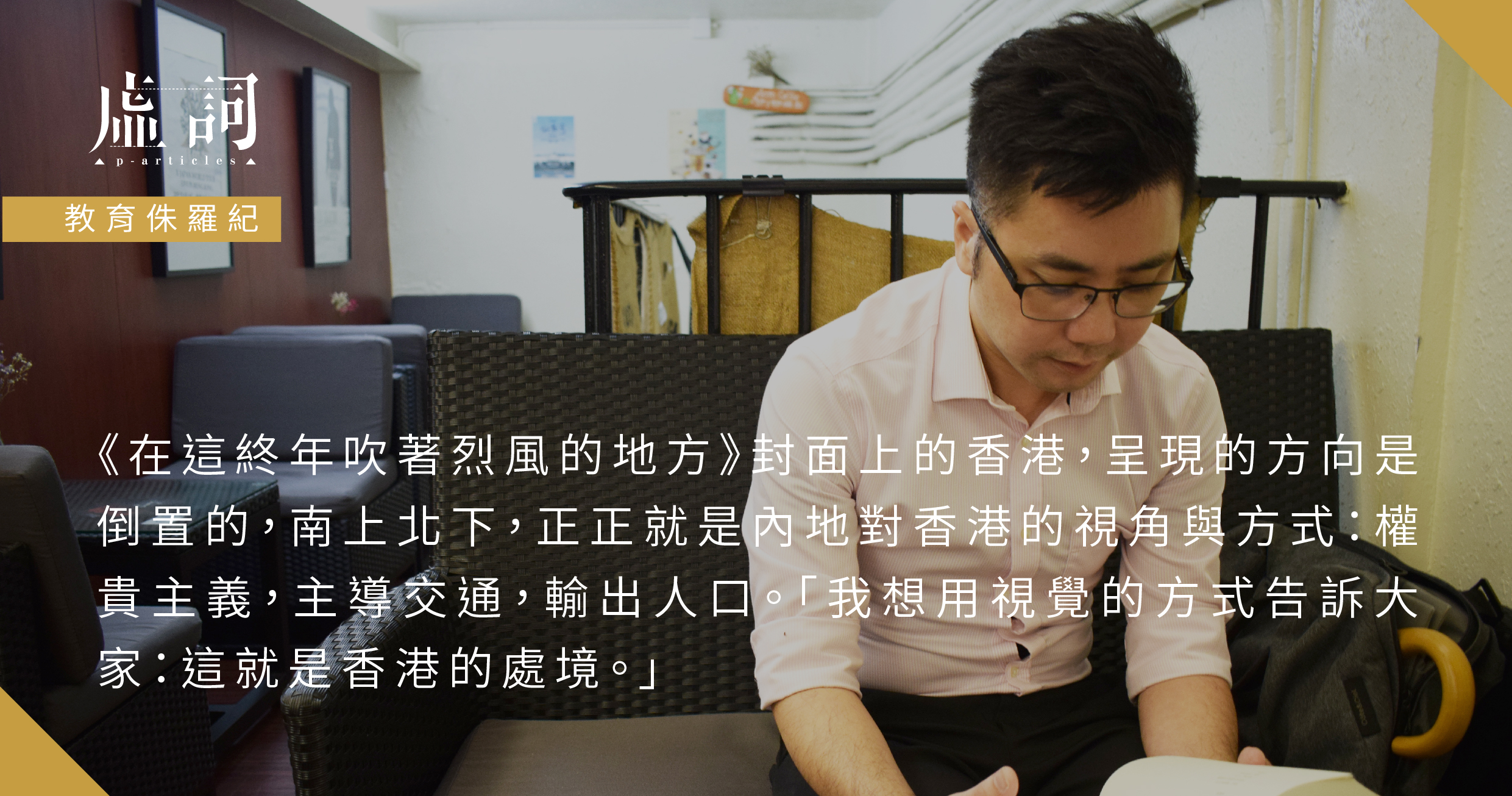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詩人老師跂之:下一代需要有希望的未來
「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詩人都深明杜甫,習慣厚積薄發,以靈動的詞語,低調堅實地言述世間風景;而為人師表的,春風化雨,孜孜不倦,不計回報地滋養學生,從這角度來說,老師,也是這種無私精神的踐行者。
跂之,是這兩種人的結合。作為詩人,他作風不算高調——2013年,出版詩集《白蘭花》。六年後,自費編印《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限量一百,全不對外發售,只是贈予好友;而作為文學老師,他的坐姿非常板直,端正的身影,給人沉重厚穩的感覺。
「寫詩與教書的身分,必須分得好開。」跂之聲線低沉,話卻說得篤定,散發溫柔的光芒。在現實急躁的香港,做一個詩人已經不容易;要做一個寫詩的老師,就更加是一件艱難的事。到底跂之是怎樣在生活的吊索上,平衡好這兩個身分,肩負起寫作、教育的責任?
現實與理想,夾縫裡游走
「我從不會在學生面前講自己的作品。」在互聯網發達的年代,學生隨便搜尋,就能發現自己老師的詩人身分。即使如此,跂之還是執意要在學校裡隱藏光芒。「教書,絕不能將自己的preference放在學生身上,在日漸變差的社會,我們最需要的,是緊守自己的專業,提供需要的技能、價值給學生。」
跂之不是一開始就想成為老師。1999年,他在港大中文學士畢業。「本科論文就是寫沈從文,可是那年頭經濟不好,港大master收生不多。」在中大讀兩年碩士,再當了一年教科書編輯,面對不再十八廿二的年紀,找工作變成無可避免的事。2003年,他投身教師行業。「香港這個社會很有趣,讀得書愈多,出路就愈狹窄。只是比妻子遲幾年入行,老師的人工已經減得很厲害。」
要滿足生活,才有成就理想的條件。跂之教書,也寫詩,中間要取一條不著痕跡的平行線。
「無數的paper、行政教務,又要處理學生成績、情緒、家庭問題;政府批了幾多錢,學校就一定要用盡,活動不斷地增加,老師工作愈積愈厚,時間永遠不夠。」下班回家,還需要分擔家務,照顧女兒功課。跂之坦言,他每天只睡五小時,經常感到勞累不支。「好多事抆住自己,父母、妻子、女兒都需要我支撐,說真的,有很實在的焦慮。」
跂之經常寫魚,也像魚,努力在日與夜的夾縫游走,抓緊寫作的機會。「轉堂行樓梯,我就會自言自語,在腦海構想詩句,可能已嚇走不少同事。」他輕笑道,幽自己一默。訪問前一晚,他想撰寫一篇影評,於是趕快改好學生練習,完成備課。誰料一坐在電腦前,就倒下睡著。「忙了十多小時,可能只有二十分鐘的創作時間。」
叩問實相,生而為人的責任
跂之喜歡思考複雜抽象的事物,還讀了一個佛學學位。「明明在駕車,也會忍不住想:『我到底是誰?』」何謂自我,何謂實相,何謂存在,都是他在新書《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裡反覆思考的命題。「我常常覺得:真實無法言說,只能呈現。」在詩作〈致失去〉,就可讀到他對「失去」的思考,呈現出的圖象:
「如果擁有都是虛無
失去必定有形
否則我們如何感到
失去的重量
和掏空的形狀」
有關「失去的重量」,跂之本人,他的父親,他的家族,都有深切的體會。「爸爸在農村長大,沒有讀書,經歷土改、文革,失去了很多家人。」跂之從沒有見過自己的嫲嫲。父親來港後十多年,才知道她是何時離逝、因何死去。
「點解啲人講到上邊咁好,但遭遇可以咁可怕?」逃過浩劫,跂之父親不禁對自己、對家族的命運反覆思考,主動閱讀。「他開始自學,讀《明報月刊》,看文學作品,開始寫小說,投稿去《香港文學》,又讓他成功。」不知不覺走上了寫作的道路,轉眼間,父親已經出版了十多本著作。幫助他父親結集的,是獲益出版社的東瑞。
幾年前,跂之父親得了大病。書中的幾篇〈入院記〉都有描寫父親病重的狀態。「爸爸身體一向健康,但在糖尿藥的影響下,身體突然變得好差。母親與我,不忍心看他受盡煎熬,一度想為他的生命作決定。」父親康復過來,除了因為如跂之所說,「是一個好硬淨的人」,更重要的,是一份「我還有說話未講完」的使命感。「我好記得他講:『個天留條命畀我,我就要珍惜,履行我的責任,將時代紀錄下來』。」這種感人沸騰的精神,亦超越世代,被身為兒子的跂之繼承下來。「寫作,是要為當下的認知負責。」
迎接命運,烈風裡尋找出路
是詩人,也是兒子;是老師,亦是父親。多重複合的身分,讓跂之更能認清社會現況,他坦言,十分憂心下一代的出路。
新書《在這終年吹著烈風的地方》的封面,是一張印有「賊灣」、「春花落」、「琵琶洲」等古地名,來自明代郭棐《粵大紀》的廣東沿海地圖。值得注意的是,這幅地圖上的香港,呈現的方向是倒置的,南上北下,正正就是內地對香港的視角與方式:權貴主義,主導交通,輸出人口。「我想用視覺的方式告訴大家:這就是香港的處境。」
未知過去,焉知未來。跂之相信:生而為人,必須對所在的地方有所認知,有所感應。他喜歡看地圖,理解城市的沿革,連結歷史。「名字消失了,就失去意義。再沒有人會記得那地方的過去。」他常鼓勵學生外出、行山,認識自己的社區。「想學生有人文情神,但他們都很缺乏幻想、想像力。就連放學都無人霸籃球場打波。」俗語那句「皇帝唔急太監急」,就大概刻劃出跂之的無奈。
教育,要讓下一代有promising的未來
身為文學科老師,跂之一直站在教育問題的最前線。自新高中學制開始,文學科的應考人數愈跌愈多,再過幾年,就可能失守一千人關口。「從舊制的必修科目,變成了選修科,學生大減,不少Band 2、3組別的中學都不再開辦文學科。」他坦言,即使任教的學校屬Band 1組別,但有興趣、有能力讀文學科的學生只佔少數,很多人都是因成績遜色,無奈地選修。「和名校生一比,就會『墊底』。」
跂之認為,文學科的考核方式,限制了學生獲得好成績的可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意慾。為鼓勵創意,新學制文學科的公開試成績,有近三成都屬創作範疇的分數。「考試是一個獎勵勤力,反映學生能力的機制;當創作分太重,成績就有了不穩定因素,mismatch了學生的能力。」
談到有「死亡之卷」之稱的中文科,跂之更感嘆,「能力導向」的教學宗旨,帶給香港教育、一代學生深遠的創傷。「新學制頭幾年,中文科取消範文背誦,學生不用背書讀書,就連Band 1仔都是考試『吹水』。」知識無法累積,學生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達到水平」。「學生不是天生喜歡補習;是教育制度出了問題,他們才這樣求助。」他坦言,即使制定課程的人從善如流,虛心聆聽意見,重設範文;十多年的語文教育問題,仍無法在短時間裡解決。
面對文學教育、語文教育、甚至香港未來的困局,跂之堅守為人尊長的職責。「教育,是要讓下一代有promising的未來。」無論學生能力興趣,他都會盡力施教,保障他們希好成績,希望他們的人生有更好的選擇。「如果學生成功了,或真的走上寫作的道路,千萬不要回來多謝我--這是他們自己的努力。我的角色,只是負責提供土壤,給最好的選擇給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