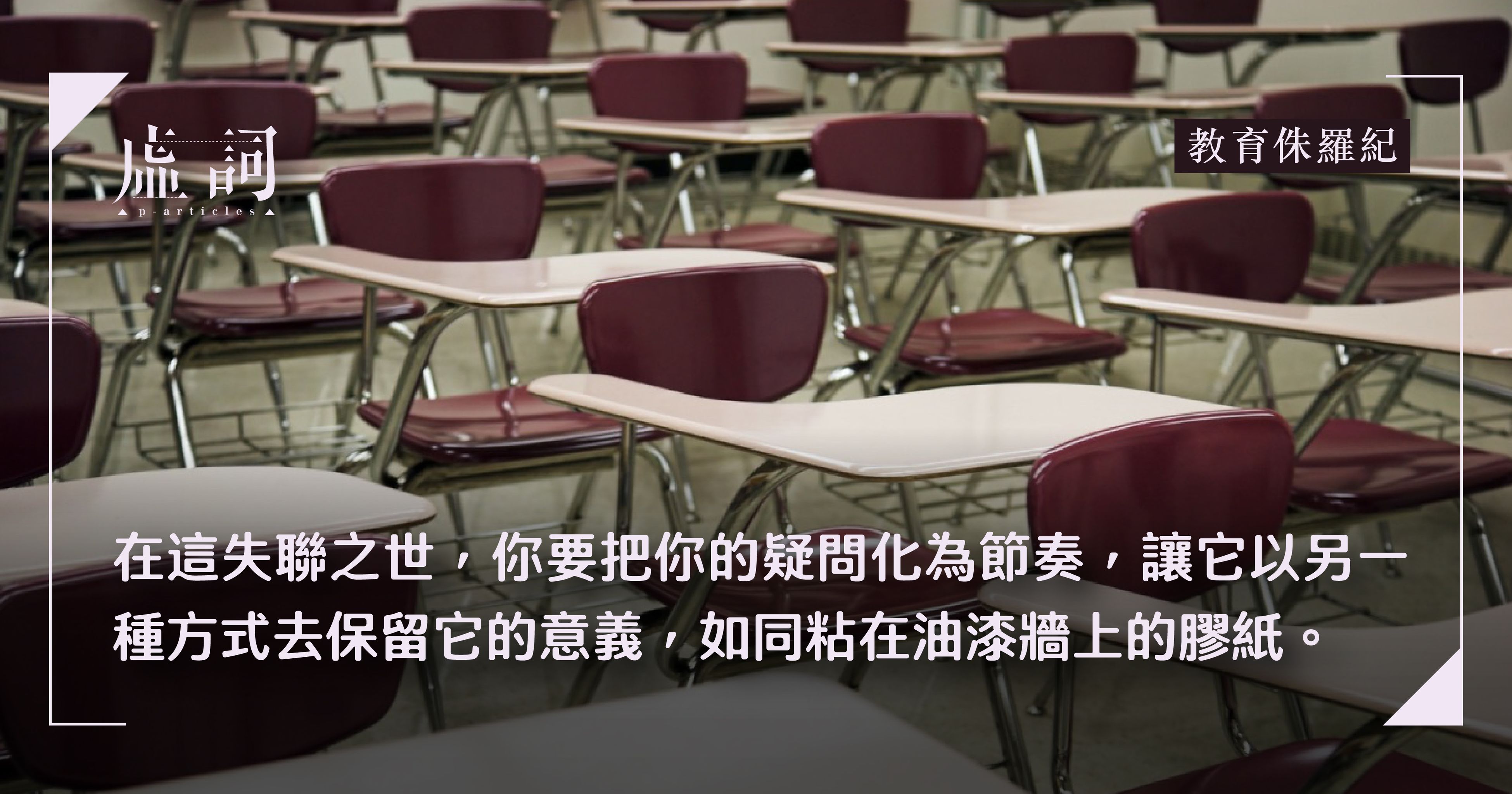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問答
在我問問題的時候,我想起了數十年後他問我問題的模樣。老師一直以為我有自閉症,他在家長日時也向我的母親透露過這點憂慮。我的確是全年上課沒發過一語。這時我不知來了甚麼的勇氣,把右手舉起來。我很在意舉手時沒有把右肩縮起,像個傻子的模樣。而是舉得很優雅、很堅定的樣子。老師驚異於差不多到了學期終的這種天啟,立即把全班同學叫靜。老師是學校的元老,同學都服膺於他的權威,氣氛一下子便靜了下來。
這種靜又不禁使我聯想到,到離開這間學校前,我還是一樣的寡言,只是進步了一點。我不是害怕權威,我只是有種適應的困難。到我適應過來,幾年的時光早已過去。現在教我的是一位溫柔敦厚的老師,但他的溫柔是堅定的、充滿學識的,比剛才初中那一位更有權威。他從不責罵學生,因為他一進課室,就沒有學生會越雷池。
要去問他,需要一點勇氣。他不罵人,我也沒做錯事,而我也不害怕權威。我從一次他提及六祖,把他的老師說成是達摩時,我知道老師並非完人,有錯我不必直接向他指出,也無損我對他的尊重。將來我們不會記得老師教過甚麼,只會終身記得他的態度和作風。誠然,那次我鼓起勇氣到他的教員室去,我已忘記了問過他甚麼,大約是另一條關於陶潛的問題。我只記得他無法把我解明,最後我裝作半明的謝謝他,因為他已盡了力,反覆用不同的角度嘗試把問題言明。這與一開始那位老師有點差別,他是不懂的,但他選擇供給我一個想像出來的答案。那時我剛進中學,同學和這位老師都訝異於這道他們無法想像的問題,而結果是,老師用胡謅的方式過了關。同學們每一個都相信了這個權威的答案,但我並沒有相信。這個問題我一直收藏在心中十多年,至我去到另一間大學,有足夠的資料可以翻查,才解得開答案。我知道除了我自己,沒有人能給予我答案,我要克服的問題是我自己。這位老師不知道他的想像變成了一條絲線,我像自閉症一般頑固地把這個鈎咬著十多年。不論他的答案對與錯,我必須感謝他為我提供了一個可以詢問的安全環境。在這環境下,不論老師答錯、不懂,也無礙把學生培育成材。
不像我小學那兩個老師。數十年前的屋邨小學過的真的有點魔幻現實。狹小的六層校舍突然會擴大和升高,據說是因為後來的移民人口大增,但過幾年後卻完全荒廢。一切就像太陽老化,膨脹成大紅星,然後突然圮塌,被自己的重力壓死自己。半數的老師不是老師,而是把你視作仇人的人。在孩子眼中,那時校園變得那麼巨大,拉闊的連同是學生所感到的怨恨。
我說,魔幻現實才是真實,你們考完公開試,建議你們去看馬爾克斯,或者另一位拉丁美洲作家馬奎斯。考公開試是為了現實,看馬奎斯是為了魔幻的現實。這時,有一條魚從鋁窗游了進來,一直在教室上方徘徊,撥動著教室內柔和的空氣。大部分學生都睡著了,只有很少的,會保持彼拉多來前的警醒。
大概是問題太深,他解不明白我是完全諒解的。後來我回想起來,我應該是問他《歸去來辭》中「既」與「奚」句意上無法產生連屬的關係,這兩個連接詞如何產生關連。我知道這位老師是看得起我的,我是那種不作聲的古怪學生,一發問便要見血。他起初教我的時候,作分組報告,我單人交了一篇四千字的議論文,論證李廣田並非每篇文章都與時局有關。那時的學生,閱讀遷移的能力是不言自明的高,讀完一篇《花潮》,便覺得篇篇均應如是解讀。時代不明便須存疑,上大學第一次聽到「知人論世」這個詞,我初中已知道這種方法。我也知道,時代的呼聲往往是激情的,但必流於枯燥淺薄。表達時代,要看到當中的永恆。老師對我這篇文章是讚賞的,他只在我的習作上批了甲等,然後寫上「有高見」三字。這三個字,就把我像魚一樣從絲線上釣起。有時我很懷疑坐艇釣魚那些人,魚這麼肥大,魚杆這麼幼小,怎樣拉得起一條不成比例的大魚。後來我看電視發現,除了魚杆和絲線的構造,漁父的技術和經驗是最重要的,太鬆魚會甩鈎,太緊的話,多韌的絲線也會扯斷。
於是我在他上一篇文章寫下了這樣的評語,「留意節奏」。甚麼是節奏呢,我沒有解釋。我知道他應該不會來找我,但他會一直留意著這個問題,直至他自行找到答案,或需要一點指引時,克服了自己的他便會來找我。是的,他並不會害怕我這個權威,他要克服的是他自己。
魚游進來的是鋁窗,從前的是鐵窗。我記得我與一個全級體型最龐大的同學打架,差點被他從鐵窗掉下去。我是全級最瘦小的,但我一點也不害怕這個同學,我也並不如老師認為般那麼默不作聲,我也不是他們所認為的自閉症。從我現在對過往的展望,我估計我將會患上輕度的阿士保加,因此固執、難以適應,到了中學中期會見消退和好轉,這些特徵完全吻合。只是未來根本再沒有阿士保加這種病的定義和稱呼,但這種病是一直存在於部分人的精神內。我對於同學反而是過分的多言,無法控制;但對於上課,我是頑固的認真,同樣是無法控制,而不是能夠克制。我認為問題不是隨便問的。我不害怕老師的權威,我只是恐怕自己問得不好,會令自己被自己侮辱。
這是一種個體內的失聯。我不容許自己輕易發問,也不容許自己輕易回答。自問自答都是孤獨、憂鬱的人,而我內中是一片拉伸的荒漠。對於對答,我是徹底的執著。我時常在思考問與答成功的機會率,結果是零。因為有些話,實在並不好說。
幸好我那時沒有像魚一樣游出鐵窗外,否則我便沒法在學生第二篇文上寫上相同的評語。自從我介紹了馬奎斯,便出現了一篇令我意想不到的仿作。
我希望他知道,有些時候,不是你問,就必然會有人給你答案;不是你說,別人就一定會警醒。因此,在這失聯之世,你要把你的疑問化為節奏,讓它以另一種方式去保留它的意義,如同粘在油漆牆上的膠紙。正如我也想像不到,我今天需要用馬奎斯作為教材,要你們特別留意當中真實與虛幻交換的節奏。文學上,一種被隱藏在節奏裏的內容,的確較無韻的呼喚更易保存。他會來問我,我是預計在內的。因為評語是我寫的,魚也是我所幻化的,我要用更精密的方法把牠釣起。
以上其實是教學法的比喻。現今教學,老師不再是單方面的傳授知識者,更應該是啟導者,啟導學生自行尋找答案。
如果我是文中的第一位老師,我會選擇說不知道,而非眼球一轉,說出一個幻想出來的答案。畢竟在那個時代,家長不會時常投訴,老師說不懂是安全的,社會不會因此質疑你的學歷。當我在中一回望研究院那時,我知道我所問的的確很深,要老師答得到是強人所難,但他完全有不回答或說不懂的權利。我問:為甚麼桃花源裏的人的衣著會悉如外人?
那位很有權威的老師答,這是,因為魏晉人的衣著與秦代的衣著無大分別。其實他大可說或許源裏人一直與外間保持有限而秘密的溝通,啊,文首那條很可能就是秘道,即像第五十一區,一直默許它但又隨時不承認它的存在。又或許可以利用生物的演化理論解釋,說既然桃花源與外在的環境非有極端的差異,本是同根,衣著也不會差得太遠。何必扯上歷史這複雜的問題。
高中我首先翻查《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已否定了老師這說法。我已了解到兩種事實的差異,我所欠的只是一個合理的說辭。這時我意識到,所謂事實只是兩個答案之間的疑問,只是腦細胞之間的突觸,是一種創意,也可以隨意的挪動。老師說無大分別是對的,難道魏晉的衣服是單袖衣,秦代的衣服會露出私處。
於是高中的我發覺,我在研究院所找到的答案是多餘的。沒有人需要這些,即使需要,知道了事實也沒辦法填飽肚子。而且當事實與另一種事實衝突,會正如物質遇上暗物質,會炸毀半個地球。因此我喜讀陳寅恪的《桃花源記旁證》,一下子把秦晉縮成了當代,把兩端的答案縮成了一個,移除了問題,簡直是神來之筆,像把樂譜上兩條小節線擠壓成一條,變成了「1」。
於是我告訴他,這樣的譜只保留了拍子和節奏的記錄。他聽我用了這麼長的篇幅,去說明文學的手法,像手風琴般由「1」拉開成一張皺摺的弧,又一下子把它壓縮成一個「1」。於是他處身於明與不明之間,處身於答案與問題之間,處身於可問與不可答之間。這就是真正的問答。
在街上拉琴時我想起了另外兩個老師,在我被衛生幫驅逐以前。小學那個老師,不知為甚麼這麼討厭我。有一天我被另一位老師帶進教員室,經過她面前,看見她看著我很鄙夷的笑,她幸災樂禍的樣子我到現在仍然記得。到底她為甚麼這麼討厭我,現在看來,可能是我小時的阿士保加。我對我自己說,千萬不要成為你討厭的人。我數學很差,但差成這個樣子,又與另一個小學老師有關。我讀的是好班,自然大家都很著緊成績。他宣讀考試結果,最高分的有幾多分,是那一個;至於最低分那個呢,他低聲說,就三十六分。我無法忘記那一刻他刻意壓低的聲線。他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仍令後來獲發三十六分那份試卷的我羞愧得無地自容。自此我便無法計數。中一我仍舊被數學老師叫出去,站在教師桌旁大聲羞辱。她只道我是壞、是懶。
我們沒有問答的空間。我只能答,不能問。
直至我遇上我的補習老師。有一次他著我證明兩個三角形相似,我做出來的答案,結論是兩個三個形不相似。他看著我的答卷,忍不住哈哈地笑,但笑得很溫和、很親切,我也忍不住跟著笑。然後他留我下來,很耐心地教曉我,天已入黑。
23-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