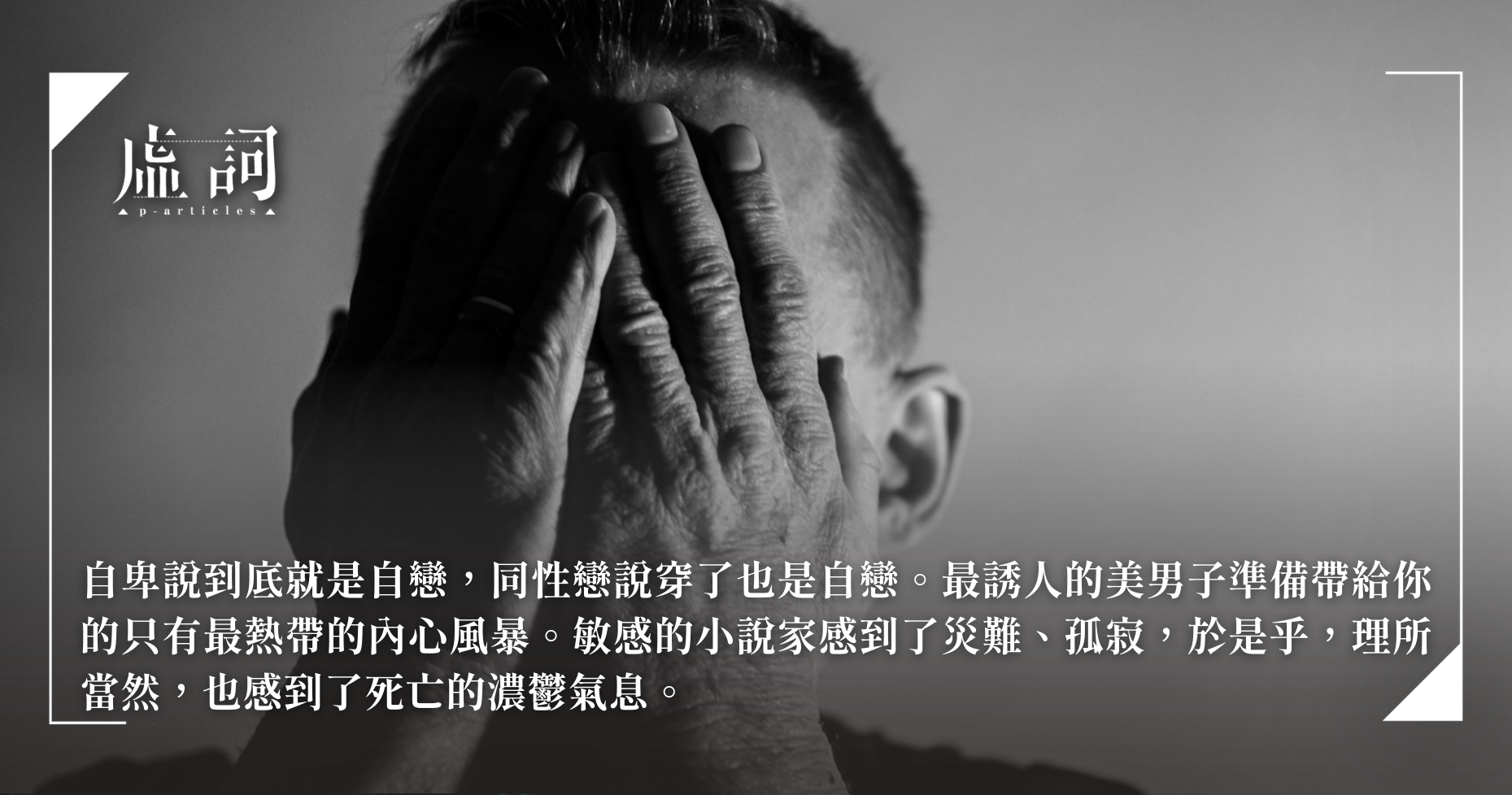De Profundis
小說 | by 黎柏璣 | 2025-08-16
可以說,寫作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它使對方憋得透不過氣來,因為對方在我的寫作中非但發現不了任何奉獻,反而看到了明白無誤的鎭靜、力量、享受和孤獨。(⋯)一個人在寫作時根本不具備表現他自己形像的文筆:倘若愛我者「是愛我這個人」,那他/她就不是為了我的寫作而愛我(而我會因此感到痛苦)。否則就是同時愛上一個身體中的兩種能指,那就過份了!那樣的事實屬罕見。假如偶爾發生這種事,那一定是巧合,是天意。
——〈獻辭〉,《戀人絮語》羅蘭巴特
由具藝術家氣質的地產大亨後代打理的購物藝術館,裝潢講究,以自然材質作主調,融合粗獷與浪漫主義,品位可謂一等一優越。不單止各大品牌,乃是連Serge Lutens、Yohji Yamamoto等只有品味高尚的人才有所涉獵的品牌,也選定於購物藝術館開設本市首店,象徵意義實在不言而喻。自2019年落成起,充滿人文精神的國際電影節、世界知名藝術家的個展聯展、乃至頂級時裝品牌的時裝秀紛擁而至,璀璨的文化藝術活動一浪接一浪,購物藝術館簡直是這個被稱作文化沙漠的國際大都會的一抹馨香。不過,怎麼樣的香都好,有人喜歡,就始終有人不喜歡。穿過燈色柔和的走道與一家典雅的法國香水店,電梯上一位身型健碩,灰白乾淨休閒打扮的男士向他的女性伴侶——過肩啡髮,同樣乾淨的打扮——宣布他的獨特品味:陣味好撚臭,聞到頭都暈。
他說的是縈繞購物藝術館,特別調配的馨香。係咩,我覺得都ok呀。男士的伴侶不以為意地回應。女士當然不知道,這是關乎之後整個購物體驗的品味宣言,更不知道,這宣言,屬於某低下階層男性討論區的共識。男士只悶悶重覆,說他要離開,因為實在好撚臭。但我想去聞下D字頭果間先喎,女士偏偏回說,唔好咁急啦。此時在後頭聽著,一身破舊垮鬆黑衣、淚溝深陷、臉色乾枯的小說家不禁咧出嗅見屎的表情(令他的臉更醜),心裡面想:至少上YouTube聽聽Diptyque怎麼讀,女士,您的尊容,恕我冒昧,始終屬於努力的一類。電梯隨即抵達,像驀然置身華麗宴會,歐式鏤花燈具、蠟亮胡桃木地板,兩旁香水店一直延伸,各有獨特氣質。平易近人如Diptyque、Byredo,玩味偏重的Maison Margiela,田園浪漫的Penhaligon,北歐風的Maison Francis Kurkdijan,低調的Le Labo,一直來到深處,冷豔的Tom Ford幾乎無人敢進。更不用說全店用上鋒利黑瓷磚,比Tom Ford更嚇人的Serge Lutens。一片漆黑裡,連慣時大剌剌的遊客也不見蹤跡,只得全黑的售貨員彷若深淵使者,隨時準備向誤闖的庸人俗輩貫徹一下品牌的宗旨:「罕見的是留給罕見的人」——不過好戲就要上演,因為今天就有一名拔挺胸膛的挑戰者⋯⋯
事情可以說是這樣的。自從與年輕的時裝男模結交,小說家沒有一天不意識到自己長得多難看。那些合照,簡直要了他的命。又老又醜,放在男模旁邊,這對比堪稱經典。但我們這位容貌焦慮症患者可以做的,實在不多。又不是Kris Jenner,哪有錢弄什麼面部拉提,而且,小說家對自己說,比起動刀,更應該設法將年月的痕跡昇華成獨一無二的美才對。
自卑症患者都對wabisabi之類的美學情有獨鍾,不過要是給他們一副荷里活長相,他們直接給你在IG舞姿弄首不害羞。小說家也沒例外,要是能免錢無風險弄回十八歲,白皙一個花美少年,放棄寫作也無妨——畢竟寫小說的都是些三尖八角、嚐盡社會陰暗面、陰陰濕濕的醜人罷。
總之,自卑說到底就是自戀,同性戀說穿了也是自戀。最誘人的美男子準備帶給你的只有最熱帶的內心風暴。敏感的小說家感到了災難、孤寂,於是乎,理所當然,也感到了死亡的濃鬱氣息。但不。小說家之為小說家乃絕不輕言放棄。他迎接死亡的挑戰,誠如他闊步揚眉,準備迎接小眾暗黑品牌售貨員的挑戰。
事情事實上也是這樣的。小說家他滑IG的時候,突然被餵了一條香水reels。當然不是JeremyFrangrance啦,簡直發了瘋。I'm the best I’m the number one fragrance icon that follows the teaching of Jesus⋯⋯,有時候,你會覺得,因著社交媒體,我們得以帶著感恩的心來欣賞各式各樣陽痿焦慮的manifestation,實在是一件美事。總之,那是一個兩萬多follower,專門review小眾香水的account。短片說得誘人:「我就像從不真正懂得哀傷,直至遇見它。Serge Lutens,De Profundis。內省,悲愁,每一次穿上它,一些深邃的意象隨即喚起,讓你陷沉其中。灰暗的泥土,濕潤的紫羅蘭、鳶尾花,烏雲密佈⋯⋯我想,真正重要的是,縱便身處其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哀愁的美。」有一張古典長臉的她雅緻一笑,語調變得輕快幽默:「⋯⋯穿上它,就感覺很酷。哎,這世界,真沒人懂我。」至於品牌網站的文稿,用上讓中文塔利班蠢蠢欲動的濃厚翻譯腔,直接點明De Profundis的靈感:「帶著對死亡和壯觀典禮的諷刺,有著焚香和菊花,一隊愉悅的送葬隊伍前往墓地去見輔祭侍者、神父和殯儀司。」實際嗅見它之前,憂鬱的詞組已往小說家心裡勾勒出一幅幅陰暗而莊嚴的浪漫主義畫作。優雅、反諷,而且自重。⋯⋯一片漆黑,小說家向漸近的邪惡勢力來了個先發制人:唔好意思,我想試下果隻De Profundis。不過法文只有A1的小說家也忘了好好複習一下,來自深淵的使者皺眉半响,完美發音反擊:De Profundis?
*
遭遇重大侮辱之後,小說家陷入了自尊修復模式。他再三對自己說:我是個作家,我是個獲獎的作家,我是個文化涵養比這些廢sales高得多的作家⋯⋯。每次男模在街上被那些雄心勃勃的街頭「攝影師」截下來拍照,晾他在一邊的時候,他都是這樣不忘微笑地自我提醒。都是習慣了。說實在也真有智慧。自卑羞慚原於無法固定一個自我形象,任何對自尊的傷害於是威脅著全面摧毀,如此般,他實際上提醒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這樣,也就能更從容與敵人來往了。敵人把香水噴往尖紙,揚動,遞給小說家。一嗅之下,陰沉的恥辱一掃而空,小說家相當感動,如果臉色沒那麼暗沉,也許會臉紅也不定。另一邊廂,面對一時失語的客人,驕傲的售貨員乘勝追擊一連串說,除了Grette-ciel系列黑樽身之外,De Profundis還有這個吊鐘瓶款式,無論哪一款,很不幸地,也正面臨停產的命運。聽見吊鐘瓶,想到某位詩人,心頭灰黯風景再添了一抹致命的血色,小說家如臨春風地點頭,售貨員也合意地微笑著,一段比較戲劇性的沉默後,小說家從嘴裡趕出了那句說話:唔該你,我再睇下先。但名店售貨員始終不是您平時去GU見慣那些怕醜妹豬,如果以為比巴勒斯坦人還要飢餓的名店sales會隨便放過您,那實在是太美麗的誤會。或者先生您仲有邊隻味想試嘅,都可以幫返您攞㗎。我仲想試果隻,嗯,Nuits de Cellophane。哦,漆黑而高傲的瞳孔劃過一抹紅光,Cellophane。
眼前一片漆黑,小說家以為是被暗黑品牌的暗黑氣勢給吞噬了,終於發現好端端的,才意識到,只是太過害怕,本能地縮進了自己的思想龜殼而已。慢慢地,他也聽清楚了那把,一直在這裡迴響的聲音:「我可是穿一身Ann Dem Yohji的文化人!我經歷了這麼的多!我隨時把你寫進小說嘲諷一番⋯⋯!」至於高級品牌售貨員呢,也是相當興奮。倒不是因為什麼膚淺的勝負,真正愉悅在於,感受一個人的榮辱心漲大收縮抽動抽動,這麼激烈,至於自已也不禁趨向癲狂。她默默地想:「看他自以為是的模樣,我真是呸!以為穿得像個乞丐便夠解放、夠無產,笑死人!歡迎光臨真正的地獄!虛榮自戀嫉恨的地獄!你還差得多!」
總之,我們早說過,我們的小說家,可從不是那種,容易放棄的人。反正,縮了進去的頭頭,再探出來,不就好了?
不過,事情是,與男模交往這段期間,信用卡幾乎扣盡限額,又怎能再吃上兩千多大元?給decline了啦。好一個小說家,找藝發局多乞點錢再來挑戰購物藝術館啦。走在美輪美奐的香水大道,流光舞影,覺著所有人事物也庸俗不可耐,說不定這下真要決意皈依左翼,轉寫些偏激文章,把那些張嘴詩意閉嘴藝術的作家通通打做父權了(最好還是用筆名);不然就溫和點,去鄉下耕田,或在離島租個房,趕個自然書寫潮囉。
*
無花果、尤加利、天竺葵、絲柏、佛手柑、雪松、紫羅蘭、鳶尾、廣霍香、甜橙、藍莓、薰衣草、烏木、麝香、煙草、酒精、香豆、豆蔻,這些那些常見精油,糅合無窮情境、意象,正如任何有水準的現代藝術作品,無不以塑造一個先於真實的超真實為旨要。嗅覺據說關乎回憶與情慾,兼這門重任的調香藝術家們,無不費盡心機為世界帶來獨一無二的味道。偏激如Toskovat甚至弄了瓶模仿戰爭的香水。鐵鏽、煙硝、草青、鮮血。畢竟能滿足第一世界的獵奇癖好,反正說是展現戰爭的恐怖就好,只是大品牌不能這麼放肆而已。至於我們的小說家,現在則是痿著身子,一家一家店往回走。Maison Margiela Fantasies系列,有一款叫作Wicked Love。扭曲的愛。呵,真像我們哪。那reels說得好,只要懂得浪漫,再艱難的處境驀然就變得甘美誘人。總之,從Serge Lutens吃了場敗仗,總不能帶著受挫的尊嚴回家。小說家稍為振作,往Maison Margiela走去。模仿實驗室的設計,乾淨俐落,穿著白袍的售貨員自如地招呼來客。迎著小說家走出來的,是電梯那一對乾淨男女。嘩果個fireplace真係好fireplace呀。係囉,好特別呀,不過我鍾意果個sailing day多啲啫。係囉,好襯你呀,個sales真係好好呀,介紹親啲嘢都好岩我地口味呀⋯⋯。小說家先是詫異,繼而蔑嘴一笑,甩了甩瀏海(讓他變得更醜),揚胸就要走進去,卻突然像電影主角一樣,猛地回頭。
——年輕的男模每一次灑上Tom Ford的Fucking Fabulous,小說家都會癡迷了似的,往模特兒那裡說:你好香呀,你真係好香呀⋯⋯。這現眼小說家又再嗅見了。回頭,卻只見一塊塊蠟黃的臉孔。模特兒的臉是一張高貴的臉,完全與Fucking Fabulous相襯托。煽情、挑逗、不羈、自信⋯⋯。世界很不公平。有人注定得到,注定受人嫉恨,注定過一道戲劇般的壯烈人生,就有人得當只有兩句對白的配角。對於才成年的男模來說,與其說是漫漫人生的一節課,與小說家結交,毋寧說是短時間高強度操練靈魂的捷徑(畢竟模特兒生涯如此短暫,又要為退役後轉型作打算);然而小說家,遭到「衰老」此一遠古恐懼的侵蝕,已經步入了晝晝夜夜凝視著「永恆」「犧牲」「奉獻」等偉大詞彙的精神狀態了。情境不對等得十分令人心酸。但小說家之為小說家貴在曱甴般的適應力,他很快進入位置,像全世界處低位的愛人一樣,說服自己為無條件的奉獻與忍耐而驕傲,心甘情願吮吸酸苦的戀愛精華,為了讓內心更堅貞純粹,藉此譜寫一生最崇高的樂章。小說家帶著愛為他拍照。像一個忠誠的信徒吮吻基督的腳一樣為他拍照,拍了許多照。這麼一個美麗的上午,精緻的咖啡館裡,男模以稍為嚴肅的語氣表達不滿:如果呢,你影相果時呢,因為你矮過我,camera angle會影到我塊臉好大,所以如果你幫我影相果時呢,可唔可以舉高啲,喺我eye level咁,咁就最似我地照鏡個角度。堂堂一個藝術家,居然遭到如此膚淺庸俗的說辭給侮辱。更要命的是,經過審視,男模實在不無道理。有什麼最傷人,就是一番心意被糟蹋。多麼委屈。為你拍了這麼多照片,讓你放上IG,讓人讚美你,滿足你虛榮心,我簡直是綠帽奴。而且當然沒有我。我永遠不會在你IG出現。完全接受。完全理解。因為你說IG是工作的,當然啦,當然。才不是因為我醜,會污染你苦心經營的人設,讓讚好人數由數千飛插至一百,更不是因為,你心底裡,根本以我為恥。沒有辦法啦,小說家在訊息裡繼續寫,這就是你身處的圈子,膚淺虛偽不自覺,沒有辦法的,這就是你,毫無半點藝術家應有的——不,說藝術家實在太抬舉,乃是任何對生活有丁點體悟的人,也會有的——銳利目光及底氣,讓人能夠勇敢直視自己的慾望,至於慾望如何頑固,無以掙脫,那是後話,但你實在沒有!你身處的圈子就是你,毫無內涵,可悲至極,這就是你啦。哈,喂,eye level呀係咪呀?舉機向著男模,小說家嘲諷道。洗唔洗咁呀?漂亮的男模朝著鏡頭走近,臉龐愈來愈大,小說家一口氣按了好多下快門,嚓嚓嚓嚓,好好睇呀,全部都eye level㗎。男模把相機奪去(因為的確是他的),不多作一語,滿臉厭惡的離開,步伐瀟灑得像走秀。喂,小說家刻毒地喊道,YSL Casting唔係嗰邊喎!
YSL連結了他們兩人。小說家深深著迷於Hedi Slimane時代象徵年輕叛逆的grunge look,年輕的男模特兒則對power suit的成熟知性韻味趨之若鶩。他們一同對Saint Laurent本人為六十年代女性創造的Le Smoking禮服表示崇敬,又談到Saint Laurent同性伴侶們的那些大小八卦。小說家本認為虛榮是模特兒的襯花,誠心鼓舞:有一天你將會走上YSL的runway。不,痛苦才會帶你走上YSL的runway。痛苦洗亮我們的眼睛。痛苦讓我們學會不惜一切去追逐。「當初你走向我是為了學習生之歡愉和藝術之歡愉。不過,老天卻看似暗中別有安排,挑了我來教你一些奇妙得多的事情:悲傷的意義和它的美。」這是王爾德於獄中寫給情人道格拉斯的長信結尾,標題為,De Profundis。小說家截了這段出story,讓男模看。男模看了,點了讚。小說家於是把訊息傳出。因為兩人認為用英文傳訊比較高雅,所以這道訊息原本也是由英文寫成,不過為方便閱讀,暫且譯成書面語:
「⋯⋯但我知道,你有一股向上的心,你不甘於成為一個膚淺的人,這引導你走向我。這很好。所以我把一切都告訴你。我們可以停止談論當時在咖啡店的事,還有這次那次對彼此的傷害、侮辱,因為真正的傷害,永遠在另一處。我要告訴你一切,關於一個真切的人,他的痛苦。一種痛苦。
「自從遇見你,在那天殺的咖啡館遇上你,我活在天堂。我以為世界終於對我施予憐憫。你是我從未感受過的。你的前來是如此強烈。我朝你走去,盡我可能。那些浸浴在幸福的時光,無以遺忘。我以為我所有的傷痛,來到此一刻,終於有了意義。我告訴過你了,不是嗎?所有關於我的一切。所有構成起初吸引你的一切,通通源自那些無可訴說的痛。我以為是你。你,在那麼多那麼多的人之中,你。我以為一切奉獻,一切付出最終是值得的。所有這些最終我把自己弄成可笑的猴子。為著與你相襯的可悲慾望,由平平淡淡的打扮,由第一天遇上你時那樣,漸漸步向滑稽,以為自我超越。學人穿Dries Van Noten的襯衫,坦露出那像屍體乾癟的胸骨,往上面吊起一條條Olivier Owen的銀鏈,穿起愈來愈闊的Boris Kjellberg褲,以為自己神奇地稱得起這些花樣。還有那頭齊瀏海。我不想告訴你是為了掩蓋顯老的額紋,所以告訴你,那是受到Celine AW24的影響。我很清晰記得你當時臉上的表情。
「然後我訂購化妝品,我護膚,為了與你相配,為了在照片裡,你可以有個好看一點的伴侶,讓你以我為傲,我甚至去美容院打激光、做微針。你不會知道有多痛。但我倒記得你看著我從美容院回來,又紅又腫,還化上一層厚粉的臉時,表情有多複雜。你嫌棄我,但你不想承認。所以你視而不見。但我一直等著你,等著你說什麼也好。說些什麼吧,讓我可以在你面前徹底崩潰。然後,你會充滿溫情地,告訴我:不要再辛苦自己了。
「但一整天下來,我們一直假裝沒事。只是你,比平時走快了一點,走前了我一點,節制地,遠離我一點。那是豔麗的下午,陽光狠毒的海旁。陽光像毒液一般腐蝕著我的臉。皮膚科醫生說,療程之後,充滿開放傷口的皮膚對紫外光極度敏感,受曝曬的話,不但收不到療效,更會留下嚴重的創傷。一定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陽光正腐蝕我的臉。然後在前面的你,因為美好的光線正好灑到你側臉,你覺得美麗,取出了手機自拍。為了滿足情侶的職責,你然後把手機挪遠了一點,把我也帶進來。我亦盡了情侶的職責,報以笑容。
「這張相實在可以榮登我最難受的照片榜首。終於我禁不住淚來。但我怕會把臉弄得更加不堪。大庭廣眾,一個化著厚妝的男人,抬頭用紙巾印來印去。當刻,我突然意識到,我漸漸成為了那種,噁心得可笑的基佬。
「我只不過想漂亮而已。只不過想你喜歡我多一點而已。如果我當時對你說了真話,你可會擁抱我,告訴我,別再辛苦自己了?
「我當然是太過奢求了。你年輕,美麗,所以理應受照顧;而我老且醜,哪裡有權利要求你的照顧。我應該像個年長的人一樣,情緒穩定,並且成熟而體貼地照顧你。情緒化與放肆是青春的專利。為什麼不呢?我從來都包容你。但你從來沒有興趣真正理解我。你只忙著滿足自己的想像,滿足你的虛榮心。而我打從一開始就意識到,並且接受這些是你的一部分。我亦無興趣裝出智者的模樣,去教你些什麼。每人也有他的道路,真切的理解源於內心深處的察覺,絕非從外而來。我相信你會成長,我希望你成長。但事實告訴我們,對於這麼一個自戀虛榮的男子,一切的良好意願,最終,只不過徒添他的有恃無恐。你知道我的意思。因為你青春,美麗,我當然不能、也不應該阻止你探索感情的世界。我三番四次接受了。
「但如果我能給你一個建議,學習謙卑吧。愈早意識到謙卑,對你愈有益。不單是將來,而是,因為謙卑,我們才能完整地感受。當你打算向你那些漂亮的朋友炫耀你有一個會跑來為大伙結帳的小說家情人的時候,或者當你收到我贈你那一幅維莉安.珍的時候,我真希望你能夠理解,我是在多麼困頓的經濟情況下,仍然甘願滿足你的虛榮,以及藉此,想向你傳達的心意。放心,我沒興趣指責你,而且我認為,與實際數字保持距離,是浪漫的大前提。只是,真正令人痛心的,是你那一副理所當然的表情。理所當然地扮演著高興而驕傲的伴侶。虛偽是最令人痛心的。這顯示了你,不論感受力,還是想像力,通通欠奉。
「當然,我說著這些,只不過是我無法放棄你。我始終深愛著你。但是,你的存在,就像華沙的雪,每一秒告訴我,我殘酷的處境。
「你太漂亮了。
「你太漂亮了,以至於你將身邊所有事物的靈魂都全部吸乾、據為己有。你明白嗎?你唯有和我一樣,又醜又可悲,不再能夠接觸那些「朋友」,不再能夠揮發那不講道理的魅力,我才能感到平安。你明白我意思嗎?如果你,突然變得又醜又可悲的話,我們就可以溫馨地互相依賴,成為對方的唯一,永遠生活下去了。永永遠遠,生活下去。
「我當然清楚了。這幾乎是精神分裂的起端。我也清楚,這實在是毫無美感、平庸而邪惡的念頭。平庸因而邪惡。比道林格雷的殺人罪更為平庸。我無法控制。我愛你。我對你的愛最終醞釀成這個模樣。我認為,一個真正有感受力、想像力的人,應該能夠從這份愛裡面,提取到極為珍貴的滿足感。你應該珍惜一個為你如此癲狂的人。我實在討厭我們的愛發展成如此地步。但既然如此,我們至少可以戲劇一般,又唱又跳高高興興走向無可挽回的毁滅。我向你提議,由我協助你,去完滿你所有夢想。你唯一的問題在於年輕,而我,我能夠動用一切關係,毫無羞恥心,帶你抵達你未可想像的高度。只要你能夠接受這個最可悲最脆弱的我。這個我的這份愛。與我一同飛越。你可記得最初我們談到了什麼嗎?不,只需要一點策略,那不是什麼難事。我始終是一個狡猾的小說家。我願意與你共同創造,光榮的未來,如果你願意。如果你願意。給我一些回應。任何回應。你知道,你的一字一句,從來給我最大安慰。不要無視我。不要冷落我。我希望與你,初次,赤誠以對。毫無防備,卑微且徹底脆弱。以你的說話擁抱我。
「我愛你。請勿著急回覆,我不介意等待,因為我知道,你也以著你的方法,無論多困難地,愛著我。
「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
以錯節盤根為靈感的中庭,原木色調,點綴以熱帶植物,層層交疊的美學在視覺上喚起著靈性、時光等相當深奧的意象。電動扶手梯一視同仁,不論尊卑都把你輸送。買不起Balenciaga或者Gucci,至少也可以逛逛Adidas。要是豪氣來了,還可以在同一層來頓Five Guys,畢竟文化藝術與扶手電梯一樣不分尊卑。在購物藝術館展出的藝術品也是如此設想,考慮到普羅大眾的觀感,最好就是有意思又能打卡。Martin Margiela的紅指甲多有意思,「探討人工化的女性美,以及自1990年代對女性身體展現性感想像的風潮,對女性造成的剝削。作品與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頌揚敏感脆弱的事物,稍縱即逝的獨特美態。藝術家透過將視角重新聚焦,將平庸瑣碎的事物,轉化為讓人驚喜的發現。」至於由Anthony Vaccarello本人設計,位於購物藝術館的Saint Laurent旗艦店,一改以往高對比度的大理石設計,改以沉靜詩意的燈芯絨質感混凝土、低調雲石作為一樓的主調,轉上黑色實木梯,二樓更是盡顯設計師的風格。復古皮沙發、合桃木茶几、琉璃陶瓷、流蘇大衣、西部長靴、寬肩西裝,優雅而自傲,像波斯貓般在雍容華貴的地毯上盡情展露自己的情性,卻又不互掩光芒,詩性的布置讓日光如同呼吸般灑進來,更是引出舊拿玻里式的悠閒。背對此等美景,倚著巨型水晶球下方的欄杆,小說家像校稿般,把傳給模特兒的訊息,又再讀了一遍。模特兒一直沒有回覆,已經第七天。一整個巴黎時裝週也跑完了,真從容。但小說家倒沒有停留在適合進行指責的精神狀態太久。羞恥已經徹底把他吞噬,三番四次想要把訊息刪除。但是,同一種心態又把他攔了下來。他瞧見了這樣一個畫面:男模與他新結識的漂亮男伴,一人一句的讀著他可憐的訊息,邊讀邊恥笑要「犯下比道林格雷更平庸的罪」的他重度自戀妄想。為了對抗他們,小說家惟有理直氣壯地捍衛真誠與坦白的價值,並且在必要時譏諷他的腦內敵人是無法脫下面具的可憐蟲,或是不懂得藝術的庸人,之類。總之,來回讀了好幾遍,除了慣性找到好多想修改的地方之外,眼睛也需要從螢幕休息一下了。從底部的漂亮法式咖啡館往上掃視,嘩哦。小說家咋了個舌,沒想到居然又瞧見那對乾淨情侶,在往二樓的扶手電梯上,下陰貼下陰擁抱著。乾淨男輕輕拍了乾淨女的屁股,示意她該轉身了,可沒料到才剛轉身,乾淨男居然捧著她盤骨,挺拔下身頂了一下她。乾淨女可狼狽了,男人真是好低劣,讓她幾乎失平衡。當然我們的英雄馬上救美,把女伴給穩住,帶她順利抵達靜止的地面。愛情的真諦果然是無風起浪。這時小說家終於瞧見男模特兒了。就在這對情慾高漲嘻嘻呵呵的乾淨男女旁邊,比乾淨男要高一個頭,一身黑色柔軟的垂著,眼瞼底垂,像燈桿上的烏鴉,以神秘而憂傷的目光勾視著小說家。是誰給他買這套衣服的,全身Yohji show piece,加起來快五六萬——小說家是沒有想這些的。小說家什麼也沒有想,好像隻突然遇光的昆蟲,羞恥得想把脖子含進體內,意識到不可行,於是回頭就逃。
不過對於這樣的人,逃走的一刻,就注定了要回來。
令人難堪的一幕。小說家呆站在Yohji旗艦店外。只有穿著輕逸而浪漫的裙裝的假人,姿勢優雅地,面向著他,擺姿勢。小說家一瞬間轉念,覺得,這對乾淨男女,說不定是他的維吉爾,從地獄一直引領著他,來到無上幸福的入口。以赤裸混凝土和黑鋼造的天堂,陽光開朗的乾淨男女與矜持自重的Yohji售貨員。其實Yohji啲衫唔洗好高都著到,因為Yohji本人都唔太高,同埋係以亞洲人身型嚟設計佢啲衫。係咁㗎?其實都無聽過你地牌子,係喺出面,見啲衫好特別⋯⋯。模特兒從一道柱後現身,相對明亮的燈光下,五官剔透如大理石雕刻,手腕擺掛一件裙裝,此時給乾淨女遞去。你可以摸下佢質地,好柔軟,好有彈性㗎,因為係SS,春夏季嘅款,披印花黑天絲大衣的售貨員像殖民官員,向野蠻人不卑不亢介紹文明的好,用嘅物料都係一啲天絲,即係人造絲多,而且針嘅密度係相對疏,你睇下,透透地㗎,所以唔好睇佢又長袖又繁複,其實係唔熱,係呀,只要你著皮鞋船襪,或者有啲人會襯涼鞋,睇落,其實就好有夏天嘅感覺。係喎⋯⋯好舒服呀個質地,你摸下,係咪呀?同Uniqlo啲裙裝好唔同呀,又硬又好易皺咁。係㗎,售貨員順著說,所以淘寶假貨一眼就睇得出,質料始終無得呃人⋯⋯小說家走進,向一旁聆聽售貨員介紹、隨時準備輔助的男模點頭走近。我想上一上二樓,麻煩你。
高挑優雅的男模特兒隨小說家腳步,黑鋼梯級通透的響,轉角電視機循環每一季runway,音樂來到Max Richter的De Profundis,兩男子一步一步來到無人的二樓。香水、袋、圍巾、無袖外套⋯⋯。兩人相目而視。相目而視並且沉默。小說家像慣常一樣,頭微抬,他往往為此暗喜,因為他從來看的都是低角度,比較醜的男模,而且男模從來看的都是沒那麼醜的小說家。男模特兒倒是希望自己能比較漂亮,男模特兒倒是希望自己能夠更加漂亮,希望自己能夠被愛人釋放前所未知的美。男模特兒此時朝小說家的褲襠看去。你入去試身室等一等我,得唔得?
小說家依然不得平靜,太多東西讓他不得平靜,他本應是絕對不該來這裡的,他本應是要繼續離去,不該為榮與辱執著,而且他本應也是要說一些什麼,有一些太過重要,而且真實的東西,就這麼從嘴邊流逝。幽長而遙遠的咏嘆,往復如夢的鍵盤,時而悲慟的弦樂,像稀釋了的液體,淡淡然向小說家這裡滲進。小說家對視著鏡子中的自己。鏡中人的淚從小說家臉上牽下淚來。音樂消散,另一首悠悠揚起。蕭士塔高維奇的升F小調詼諧曲。好像櫻桃園盛放前,最後的一道風,男模的腳步已經襲來。我唔知你上身果件Ann Dem係咪假,但我攞左條褲比你,你換左佢,就走啦,好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