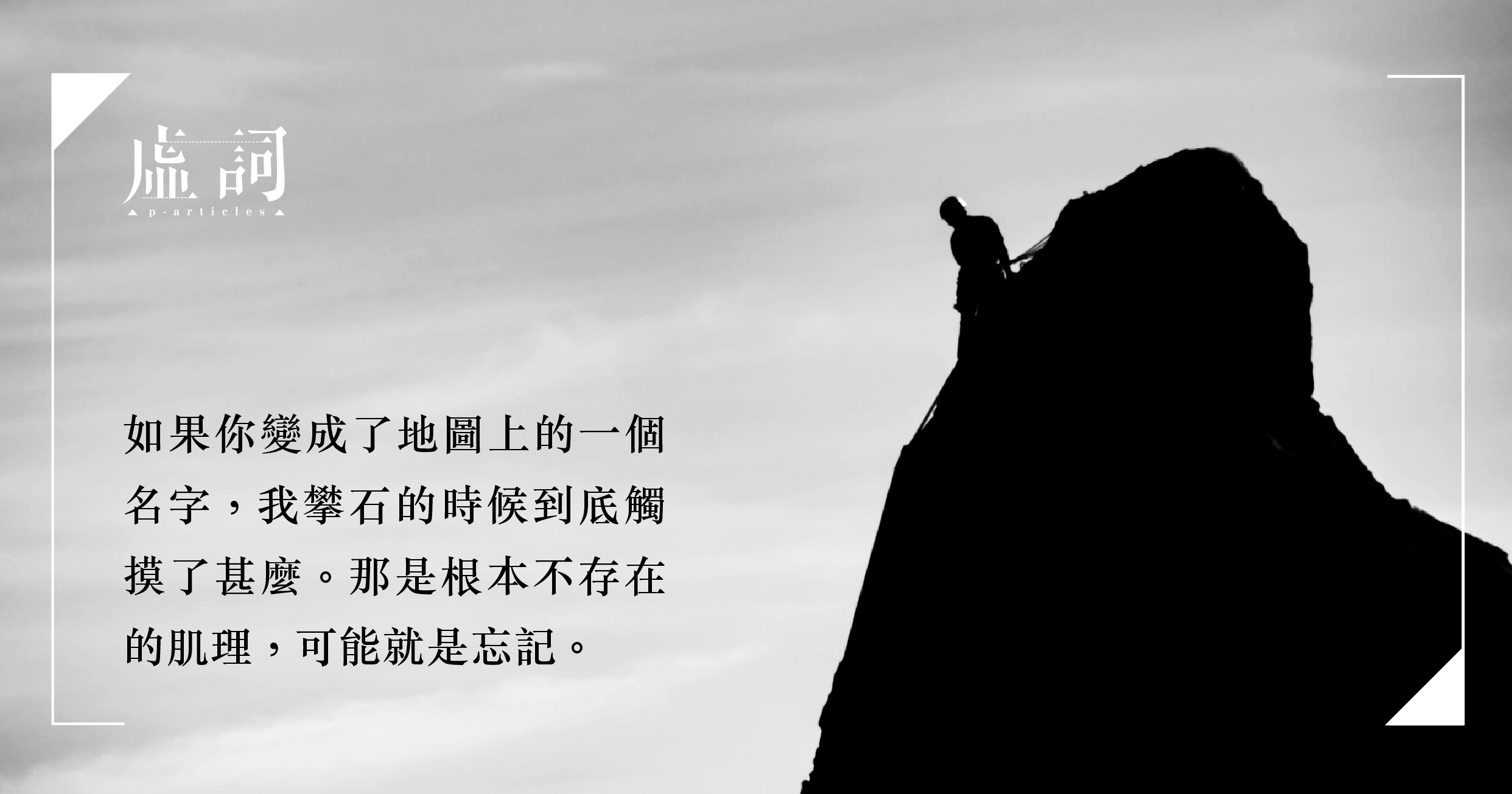自述(其四)——答L.T.
消除背景和時間,只剩下關係。這關係變得十分詭異。剩下的是一種沒有原因的關係,這關係就只有動與被動,在沒有地平的狀態下旋轉。
因此我才能遇見他們。在平常這充滿了背景的界,這些背景規範了關係,我是不可能遇見他們的。這個世界只要有軸,我們的距離就必然的被框定,在一些參照之中,關係可被理解,亦完全被誤解。這非是你把兩軸對倒就能夠顯出的真相。
在此徹底沒有經驗的界,我看見了他。他的動作似乎是在攀登一座已忘記了他的人沒有創造出來的山。這座山應該是存在的,只是沒有被創造出來。畢竟這不是一座被創造過的山。在一個忘記了他的人的記憶中,這座山從未出現過在其經歷裡。此山有路,但去不到我想去的地方。我想去的是去不到的地方,於是我需要抱石,從岩壁徒手上引。我知道我必須要這樣做,才能抽離於被創造而存在。我想觸摸一些創造無法顧及的細節,那些柔軟的石縫,只要你的手指比它堅硬。
此刻就只有我和石的關係。我赤身成為了壁面的反面,摸索那些無從施力的位置。他們都說這是一座無可攀登的壁,因為它並未被創造,因此攀爬中的他必然是真的。
移動是必要的,只有真正的隨機不能被壓縮,成為預測和經驗。雖然我是多想停留下來,維持著這種攀爬的形狀。
被創造的我有時會疑惑是否只是我想像被一個已忘記了我的人創造。我的確是被一個記起我的人創造,還是我創造了他們二者。天色你道甚麼的歉,灰不透的灰在揮舞的輪廓。沒有人知道我來了攀山。他們都說一個人不安全,我並不需要安全。那種岩石非常光滑,毫無施力點,可讓我結而為蛹。那本應存在的立足地沒有被創造出來,我也沒有被創造回去。
手汗如雨。
如果你變成了地圖上的一個名字,我攀石的時候到底觸摸了甚麼。那是根本不存在的肌理,可能就是忘記。
我用了一個夢的時間反省。那個夢很長,我一直把自己懸掛。的確我不知道自己能夠反省甚麼,我只能等待後果,或者更正確,是後果等待我的離開。這樣的我無從被曾經記得我的人創造,我只存在於自己的掌心中,一直冒汗,直至我握不緊自己的過去。
正在下一場不會停止的雨,說正在是比較多餘的,正如說比較一樣。我所攀爬的氣味的確已經消失了,我唯有停止,或者不停止。那時的我,正在思考為何我日後會變成這樣,而現在的我將會是那麼無知,對於舊日的我會否在某刻被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