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之聲︰「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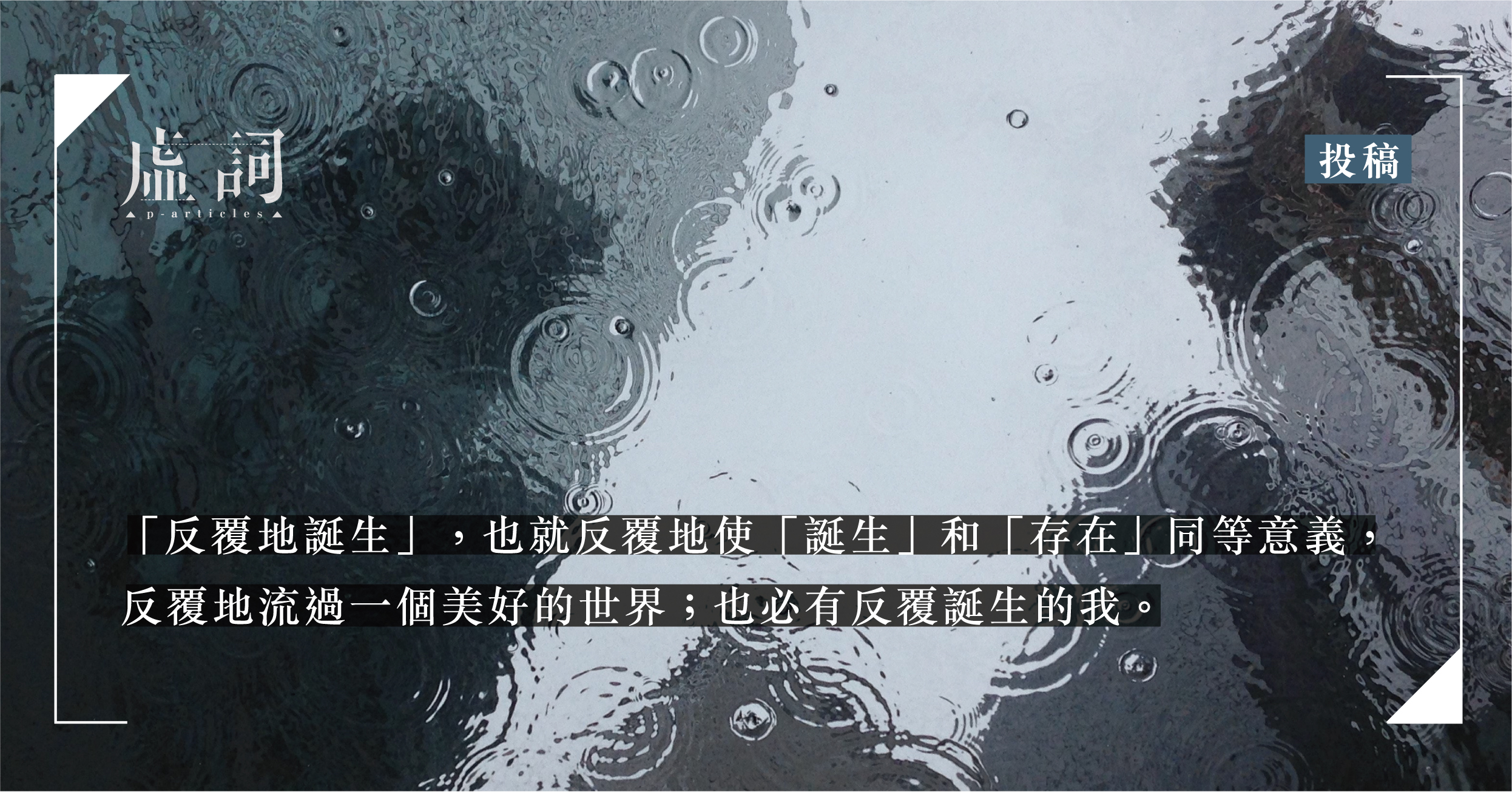
謝旭昇-04.jpg
「一個美好的世界,是可能的嗎?」這樣的句子,在真若有那美好的世界裡,是不會存在的。然而,在無垠的時間當中,必有一條無限長的河流,反覆地誕生;是的,「反覆地誕生」,也就反覆地使「誕生」和「存在」同等意義,反覆地流過一個美好的世界;也必有反覆誕生的我,即使在一個美好的世界裡,腦海中還是浮現出那樣的詰問。也就是說,在一個「不論有無一個美好的世界」的世界裡,它都可能在我的腦海中浮現。是的,「可能」、「或許」、「如若」,這些細長的詞,都像是水流扭成的安慰的繩索,會從那且真若有那美好的世界裡垂降下來,順著被它愈流愈長的本質的河床,無限延伸,直到超越那緊握著詰問之人一生順勢而下的長度。
理解到「誕生」和「存在」同等意義,就能不斷蛻變,但同時也就不斷丟棄自我;所謂像是不曾活過,正是這個意思。不斷蛻變、不曾活過,從裡頭可向外洞察一件事,我們的心靈還是遷循著肉體:心理上緻密的波盪,同於當細分至普朗克時間仍不放棄變化的身體一樣,圓滑而連續,但總是被那無法完全掌握「自我」的自我,解讀成一種斷層錯動。這樣的錯讀並沒有甚麼好奇怪的。經過設計、擺放的一具詞語的葛藤,可以攀爬上任何「能指」的鷹架,但卻無法和自身有任何瓜葛(一旦有,它就超出了自身),所以當它指向(甚至無法指向)自身,不過是一具冰冷的屍體;腦袋可以思考任何物事,除了腦袋本身。
這就回到了我在那輛搖搖晃晃的火車上的問題,當車廂門在故鄉的車站打開時,無論我有沒有走下車,映在心裡的是那道門永恆地正要打開——且不是開著亦不是闔著——的樣子。像是一扇薛諤的門,門縫裡不是隻貓,而是薄如影子的自己,隨時要消逝地存在著。一句半世紀的悲觀和樂觀互揭瘡疤的老話:存在先於本質。但換詞話說,誕生先於本質。
也就是因為這樣,我似乎不斷地走上誕生的劇台,誕生的是角色,本質的是演員,且不斷地走上但未曾抵達劇台,因為一旦抵達,幕就降下——角色就取代演員——幕就升起,不停息地上演一齣從未開始的劇。當意識到這點,便令我完全無法動彈,想要一鼓作氣跳下台階,像一鼓作氣看著永恆打開的車廂門並打破那道永恆。但慢慢地,我理解,或說,我從未理解只是身體帶著我看見:身體會先於很多東西,身體一旦習慣,心理也會跟進。
耶茨也曾經碰上類似的問題:在戲劇的排練中無法找到信念感,也就是無法相信他所要扮演的角色、無法和該角色完好重疊。這其實和身體脫不了關係,那是身體在抗拒角色。如何避免抗拒呢?我們都可以創造出一個中介角色,那中介角色的設定是一位對自己的排練或演出都十分有信念感的演員,然後我們去演那中介角色而非劇台上的角色。一開始會覺得很假,覺得心靈和肉體都是在假裝。但比起「誕生」、比起那位遙遠的自己、比起劇台上的角色,我們更願意試著揣摩中立於身體的中介角色:那樣的中介角色會流露甚麼情感、隱顯甚麼態勢呢?身體會引導假裝之人,身體會先於很多東西。我想起張曼玉演著阮玲玉,在一幕戲裡,她演著溫婉的阮玲玉在情夫旁練習演著一個角色,那個角色和她所有日常身體傾勢皆相反,她拿起煙開始抽,她壓低下頷,眼神往上飄高,緩擺過頭;她不是張曼玉,也不是阮玲玉,也不是阮玲玉演著的角色,而是她們三個。
我們幾乎是以身體的姿態在引導著下一個姿態,這些連續起來,我們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那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