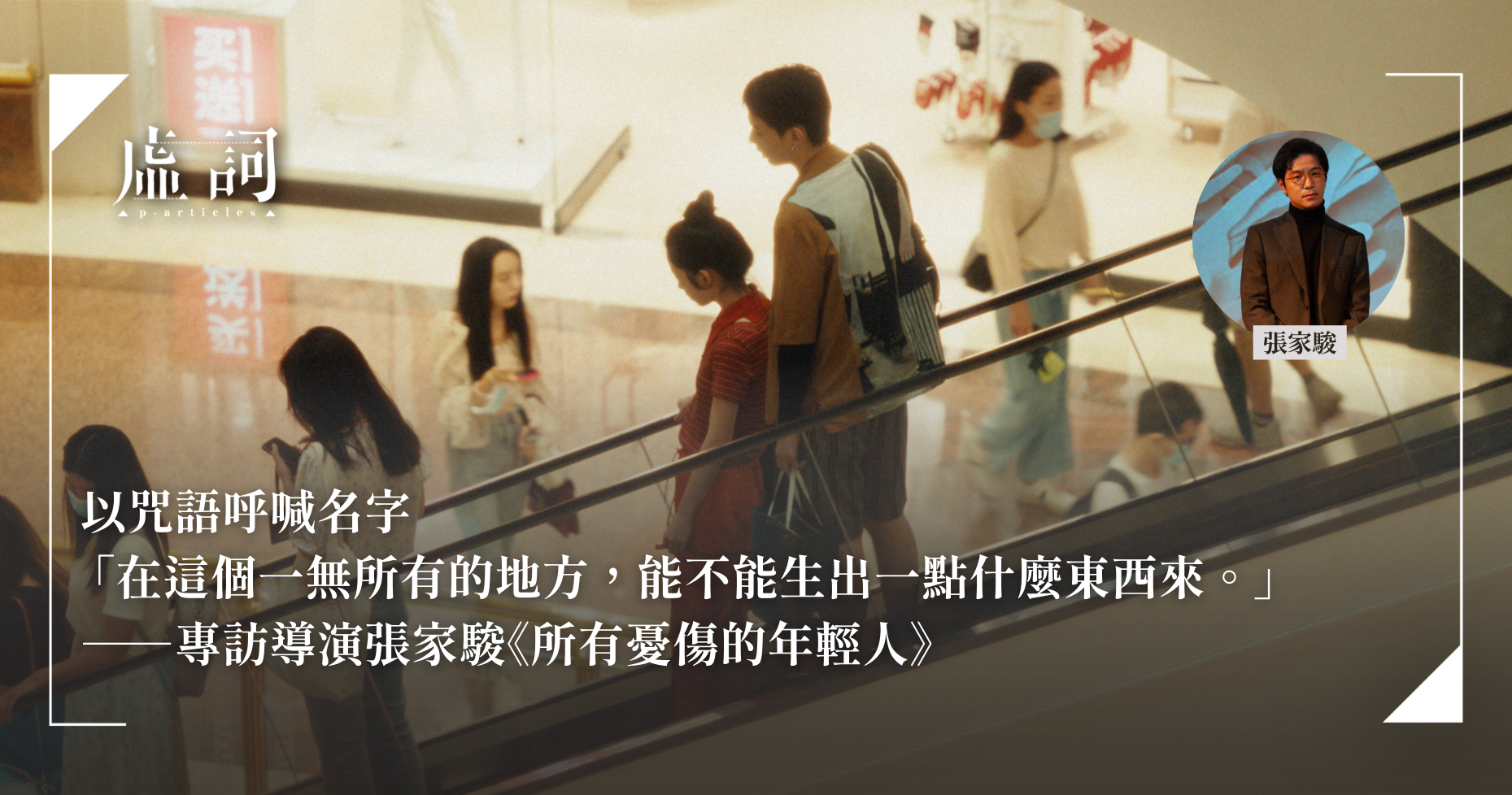以咒語呼喊名字 「在這個一無所有的地方,能不能生出一點什麼東西來。」 ——專訪導演張家駿《所有憂傷的年輕人》
《所有憂傷的年輕人》是導演張家駿和聯合編劇兼美術指導边禧暎(Hee Young Pyun)共同創作的首部長篇。電影由兩個部分「一無所有」(Nothing at All)和「所有」(All)共同組成。兩個故事以上海商場「環球港」為核心場景,由同一組演員出演,男女主角皆為藍天(安雨飾)和悠悠(陳曉依飾)。兩個故事中,演員的職業、裝扮、性格、彼此關係以及各自內在的情感核心皆不同,彼此既互不干涉、又遙遙呼應。而按照張家駿提出的概念,兩個版本可以按任意的先後順序放映。
「你不必兩個版本都看過,你只需要知道另一個版本存在就好了。」他如此說道。
「環球港」作為一種私密記憶
許多人或許不會與「環球港」這類大型商場建立深厚的情感聯繫,但對張家駿而言,這裡卻藏著許多他私人的記憶。他小時候在附近長大,那裡曾經有許多國有工廠和工人社區,後來為了向大規模商業化的地產開發方向讓步,工廠不是倒閉就是搬遷,在他唸高中的時候,附近大部分工人社區的住宅被拆除,數年後,在他出國讀書的期間,「環球港」拔地而起,這不僅象徵了中國其時所經歷的社會階級重組的時代,對張家駿而言,更是記憶的重置。
「離開上海幾年之後,回來忽然發現家裡多了兩棟摩天大廈。進去『環球港』裡面時,覺得完全像一個異世界,裝飾非常誇張,像羅馬公共浴場一樣。」儘管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但張家駿卻發現每個人在商場這個空間場域裡,只會依循他自身的身份標簽來行動。「人在裡面被劃分成三個群組:工作的人、買東西的人、進來晃蕩的人。這三種人相互接觸交流的模式是固定的,也沒有太多情感滋生的可能性。」
他認為,商場對他而言,就是一個情感無菌室的空間。「能不能在這個一無所有的地方生出一點什麼東西來。」源自於這樣的想法,他開始觀察商場這個地方。
以「外星人」的身份遊蕩在情感無菌室中
「有時候我感覺自己像一個外星人——我不太明白自己為何在這裡、別人的行為模式、這個空間的意義等等。我就沿著這個外星人的視角,繼續觀察這個商場的空間,和裡面的人對話,一切都變得非常新奇。」因為自己沒有一個明確的身份,張家駿以閒逛者的角度來觀察,一切日常的重複中都藏著光——他說那是從裂縫中透出來的光。「如果我們坐在商場,我們不會去注意這些日常細節,像是我很記得那時遇見一個年輕的媽媽,嬰兒車在邊上,她坐在娃娃機面前,一雙眼睛出了神,好像看進宇宙黑洞裡面去。」
張家駿說,電影裡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在電梯下面打鬧的孩子們、穿鮮黃色衣服的外賣員、一直試圖給予贈品的化妝品推銷員,而其中,他發現裡面有許多年輕人。「年輕人不僅從事不同的工作,他們更以各樣的身份出現在商場裡面。比如說藍天的原型是一個教街舞的老師,每天門外都有很多年輕的家長在等小朋友下課,有許多看起來跟老師們的年紀相仿。那麼這兩種人:作為顧客和在這裡打工的人,他們有沒有可能在某一個瞬間產生一些情感的連結呢?」
在「所有」或者「一無所有」的部分,其敘事核心都圍繞年輕世代在情感上的匱乏與虛無。「所有」中悠悠試圖一再偶遇藍天背後的迷戀、「一無所有」中藍天對用手機記錄悠悠的狂熱,過程都一樣地疏離、無法靠近,無論身份或關係如何對置,最後都必然落入無法接近的遙遙相望中,只可輕聲呼喊對方的名字。
但對於張家駿而言,年輕世代在情感上的虛無或只是一種表徵。「就我自己來說,我覺得這一代一直都在做一場持久的抗爭。無論是實體上的空間也好、網絡上的虛擬社交空間也好,稍不注意,就會墜入歧見、墜入很無望的感受。要怎麼對這些東西背後的系統有自覺,找到方式給自己可以持續地感覺到東西,這個是我個人最近在思考的。」
上海是個大商場,也是我的故鄉
「對我來說,想到故鄉的時候,我會想到商場。」在張家駿的成長經驗裡,上海並沒有大型的公園,許多時候如果想要散步、發呆,可選的便利的空間就是商場。「這個商場裡面有各式各樣的人,它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一個買賣東西的地方,對我而言它承載了很多私人的記憶,包括我第一次談戀愛啊、更小的時候的捉迷藏啊。這些回憶建構了我對於故鄉的想法或概念。」
張家駿說他最近在聽My Little Airpods《香港是個大商場》的專輯。「我覺得上海也是個大商場,但香港的商場和上海的商場它們之間的差異很小,這種同質化的感受隨著我年齡的變化越來越強烈,不止香港,我去到的世界各地都是一樣,它們都有這樣子的場所,從一個商場到另一個商場都是一個複製品的感覺。在這樣子同質化的空間裡,常常覺得信裡面有一點空空的,有一點一無所有的感覺。」
但張家駿並不相信那樣的感覺就是全部。「可能因為系統的關係、因為環境的關係,有時候我們會感覺世界就是這樣的,沒有情緒就是對的,好像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或許是我比較樂觀,我還是會相信,人會有一個瞬間,他會感覺到,還是有什麼東西在裡面。就算是很微茫、很日常的細節中,一個對視、一杯咖啡上的拉花,有一些真實的情緒會湧現出來。也是我們想要捕捉到的那個瞬間。」
在「所有」中,悠悠想要讓藍天也記得她記憶中的,夏天上海下的那場雪。在最後藍天的表演裡,她站在高處,一邊噴人工的雪霧、一邊輕聲呼喊藍天的名字。「我們在設計那個場景的時候,跟飾演悠悠的陳曉依說,你要像唸咒語一樣,來唸藍天的名字。」對張家駿而言,那是在一種壓抑到一定程度以後,內部爆發了,不得已流露出來的呼喊。
「在現代商場裡,好像完全沒有這種,所謂擁有靈性、spiritual感覺的一個地方。在那個瞬間,這個情感無菌室裡,她流露出她的情緒、在意、不捨與執念,這樣的狀態很打動我。」
那樣子的靈性、乃至更個體化的情緒,有多少是可以被商場這個場域所承接的呢?從各人在兩個故事中可以無縫切換角色的處境中、從影片放映順序可以隨意顛倒的設計中,人的情感在其中可以說是不著跡的——一切漫無目的,也不會被記得。但這亦與商場這樣的場域相合,它本來就不是為了體驗人性、經歷情感而存在的空間,世界各地商場的龐大規模、同質化,充分彰顯了它只是為了維持資本體係運作、去人格化的場域語言。一群人的出現與存在,理由並不重要,商場仰賴的不過是是人的在場,人在其中是面容模糊的。
《所有憂傷的年輕人》中,真正的靈性之處,以致於能讓人宛如留戀故鄉一樣留戀商場的,或不在某時某地的面貌,而在於記憶中,那聲如同咒語般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