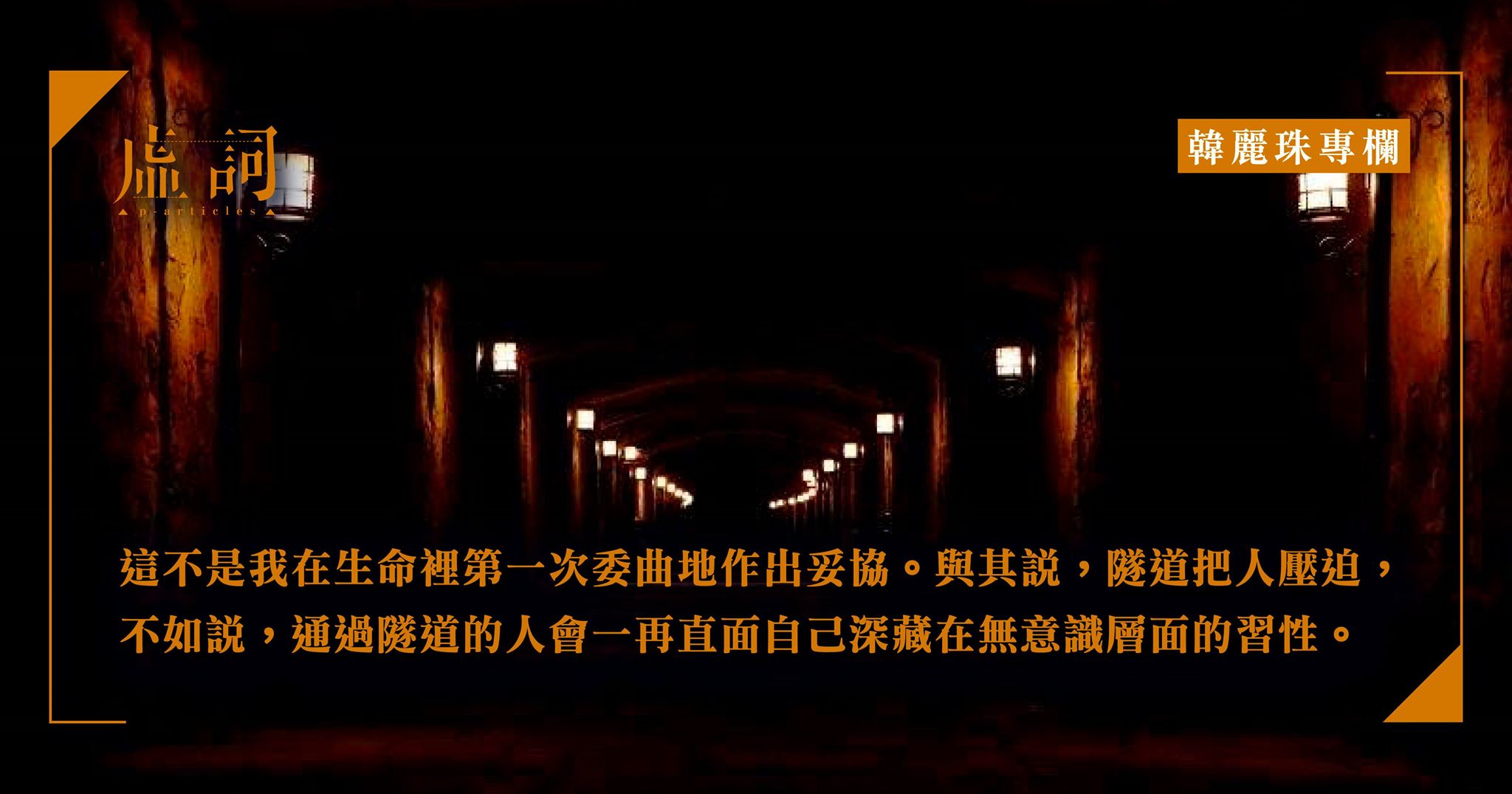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審查隧道
那是一條幽暗而具有吸吮能力的隧道,像一個漩渦,能把人拉到不知名的地方,只是,它是固態的,有路可循。
我知道隧道就在前方,原以為會先經過一番顛簸才會進入其中,可是,在毫無先兆的情況下,我已在那裡。人們往往並非主動走進去,而是被抛擲在那樣的境地。
「文中寫著『想起被強暴的身體』,但迄今,並沒有任何人在法庭被判決為受害者,所以,為了穩妥,要不要改作侵犯或其他字眼?」審查稿子的人對我說。
我湧起了一種跟他辯駁的衝動。我不能寫我想起什麼嗎,難道,在描述一種思考狀態時,也需要面面俱圓的現實嗎,就像在闇黑的隧道裡,撞上了一個人,我知道,那是個熟悉的人,在許多溫暖的午後,我都會在送交稿子時跟他閒聊或問候,可是,隧道會把人扭曲,直至擠出平日難以瞥見的本性。或許,這才是隧道令人憤怒又難過的原因。
可是,我並沒有在回覆電郵時打下任何據理力爭的句子,只是順從地,選擇了一個含糊的,不帶任何指向,同時避免紛爭和投訴的形容詞。
息事寧人。
這不是我在生命裡第一次委曲地作出妥協。與其說,隧道把人壓迫,不如說,通過隧道的人會一再直面自己深藏在無意識層面的習性。早在被扔進隧道之前,我就會因為害怕而迴避和任何人之間的衝突。要是在餐廳裡,侍應送來的食物有一根頭髮,我會不吭一聲地放棄食物;要是在巴士站輪候車輛,有人插隊而且站在我身前,我會盯著他卻不說什麼;曾經在一段被踐踏的關係裡,我把自己摺疊成窒息的形狀,想呼救的時候卻說出:「我很快樂。」那時候,我總是對自己說,因為這些事情於我,並不是最重要的,然而,在那伸手不見五指的隧道裡,我才發現,原來是我覺得自己不夠重要。
審查稿子的人,只要離開了隧道,就是我的其中一個朋友。但,任何人一旦被吸進隧道,就會不由自主地擔演某個角色。正如,人們走在街上,只要看到有一個穿著制服的人走過來,把某個區域圍封起來,人們就會不問因由地繞路而過。他們在瞬間信服權威和規則,不是因為穿著制服的人,而是,在他們的成長過程裡,制服和秩序在他們心裡所建起來的窂不可破的高牆,一堵難以攀越的夢魘高牆。高牆的根基在於人們在社會化的過程裡,慢慢堆積的罪疚感。進入社會之前,人們必須學會,自己就是個帶罪之身,因此,必定會犯錯,又必須在犯錯時得到懲罰。學會對和錯的最主要原因,或許甚至不是辨別是非黑白(因為在隧道裡的漆黑,其實是無窮無盡的灰色),而是接受懲罰,以及在犯罪前自我禁絕。
最初,我覺得在隧道裡,被審查的人撞傷,但後來我發現,那很可能其實是我自己, 一個內化了的,在以往一直在沉睡的審判者面向,直至教育局的人說要抽出不好的人,執法部門投訴電台新聞部用字偏頗,內在審判者才完全醒來。
我想起奧修說:「外面沒有別人。」我想起劉曉波在獄中說:「我沒有敵人。」
世界異常廣袤,同時影影綽綽非常擠擁。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