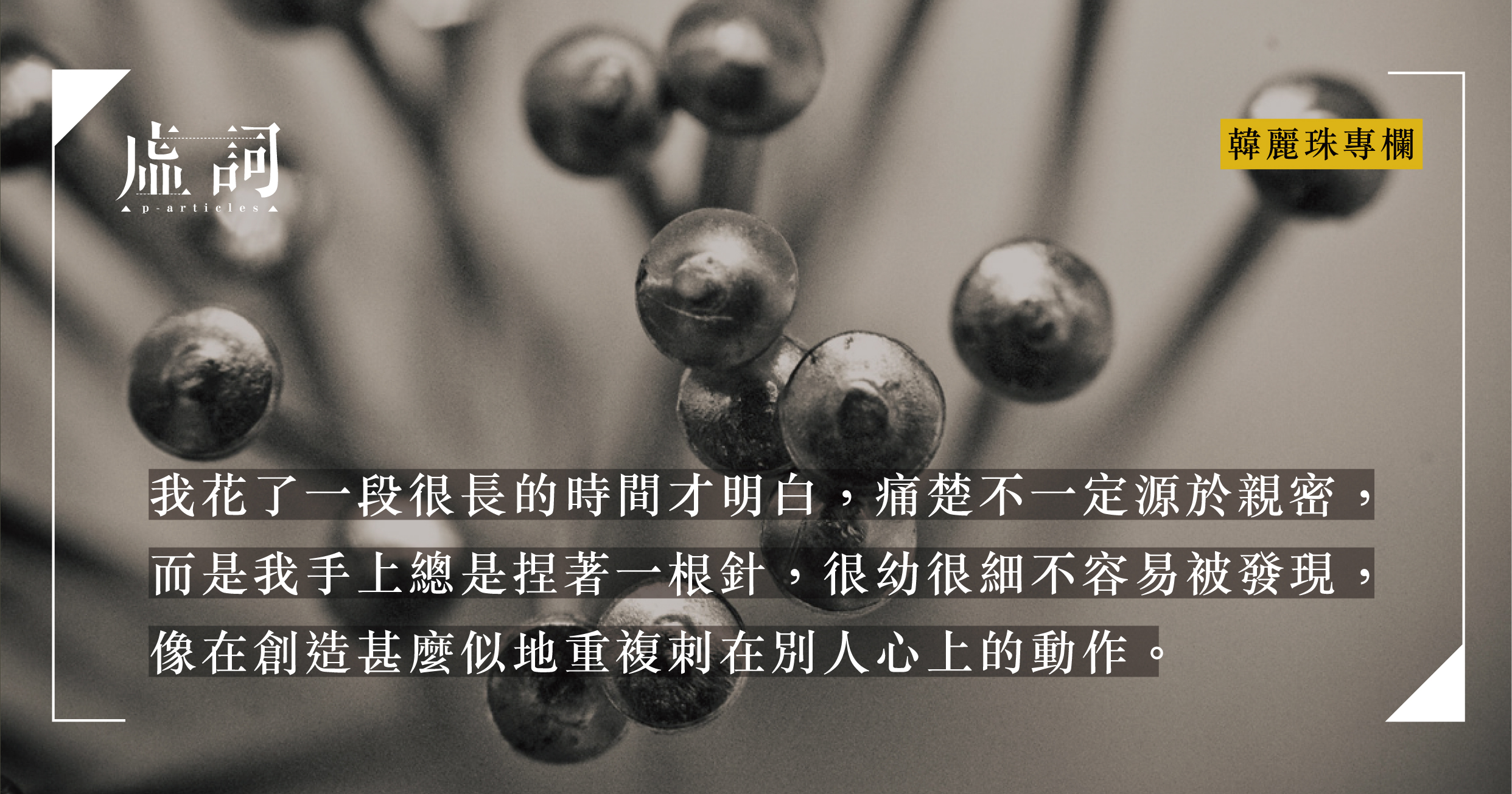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刺在心上的繡
戒除對一個已然離開的人,心生思念,是K在我生命最初的幾年,要我嚴格地遵從的第一道守則,遠比保持誠實良善,不要和陌生人交談以及多吃蔬菜來得重要。我猜,我曾經是個順從的孩子,而且善於計算,以為可以通過順從,順利地交換到認同和愛。那時候我還未知道,所有的禁絕,都會同時刺激沉溺的慾望,因此,戒除毒癮的人,往往會嗜美沙銅,打算戒掉愛情的人便會轉而沉迷工作,而剛剛戒除婚姻的人,很可能會沉醉於飼養動物。因為人只是人,在許多情況下,只能用一種癮頭抵消另一種癮頭,用一種新的痛苦,掩蓋舊的痛苦,以一種孤獨接駁另一種孤獨。
那時候,K(我並不說她是母親,因為K雖以母親為原型,卻已內化成為了另一種不真實卻具有權威的存在,即使在回憶或寫作之中,人最好還是保持最低度的自覺)像任何一個既要工作也要照顧家庭的女人,總是忙碌地買菜做飯常常加班工作至深夜回到家裡便埋怨孩子,但她並不知道(好像只有我才知道)在這些瑣碎紊亂的生活之間她持續不斷地做著的其實只有一件事──拿著一根看不見的針(她從不放開的眉頭過早絕望的手勢斬釘截鐵地吐出的每一個字),專注地縫線,那全是色彩斑爛的明亮的繡花線,縫在她自己和另一個人的皮膚上,縫在她自己和另一個親近之人的心上。或許是她的工作給她的鍛練,也有可能她是個天生的縫紉能手,她縫出了栩栩如真,不,應該說她縫出的事物,超越了真實,而且避開了時間,多年以後,它愈來愈清晰,甚至時間過去了愈久,它愈清晰。
那時候,當我對著一面鏡子,在自己的反照中看見他的影子,便告訴K。K便拿起了最幼細也最具刺傷力的那根針,臉很快地冷掉,是一個刺繡者的臉色,她說:「不要再想他,他曾經住在這裡,你應該記得那有多可怕。」但她那根看不見的針在我的記憶裡激活了魚尾紋。眼角的魚尾紋是他快樂地笑的時候一個特徵。(很久以前,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常常在街上的人群裡,留神一個又一個頭皮稀疏的男人,希望會發現他們的魚尾紋,但街上的陌生者從來不笑,所以這願望從沒有得到滿足。)
這是一種會經過遺傳而代代相傳的刺繡術。我不知道我已承襲,直至密不可分的人告訴我,他很痛,痛不欲生。我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才明白,痛楚不一定源於親密,而是我手上總是捏著一根針,很幼很細不容易被發現,像在創造甚麼似地重複刺在別人心上的動作。直至曾經密不可分的人永遠地離開了,我才清楚地看見,我刺在自己心上的屬於他的形狀。令人傷感的並不是一切已經太遲,而是這是在對的時間所發生的對的事情。我感到疑惑的是,這些事情的發生,究竟是因為我沒有對他說「不」還是因為我說了「不」?
另一個人前來,想要佔據密不可分的位置,他是勇敢的,因為在還沒有很痛之前,他就叫了「痛」。我不置可否。不是因為我已經瞭解,人們常常在感到痛苦而又看見美麗的幻影時,過於輕率地判斷那是愛,而是,我慢慢明白,在靈魂在宇宙流徙的過程裡,此生也只是眾多幻影之其中一種。所以我沒有言明,那只是我的刺繡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