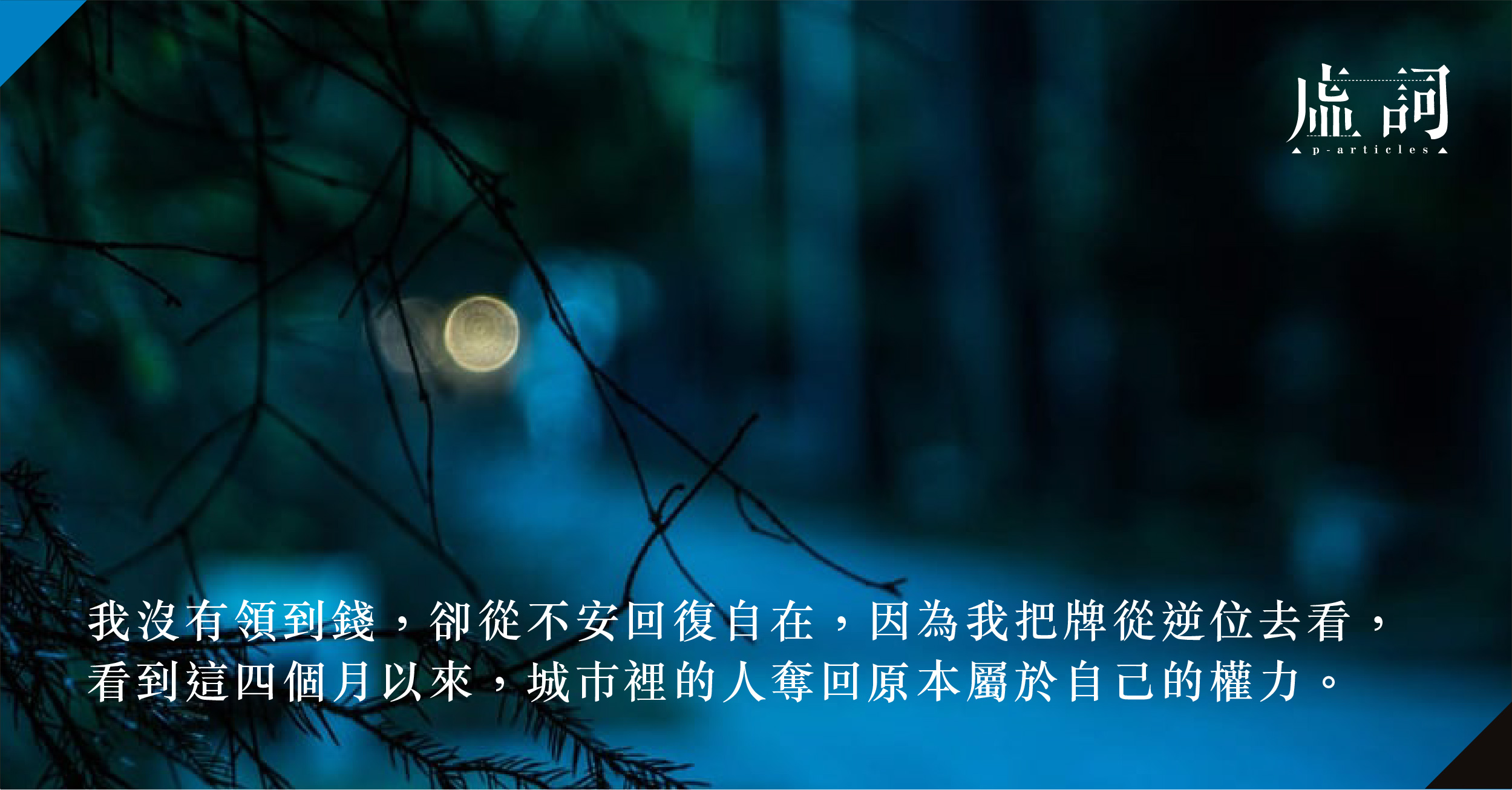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惡魔牌
《禁蒙面法》次天,大部份的提款機顯示提款功能暫停,我並沒有太大的訝異,只是問自己,我現在就需要使用這筆錢嗎?答案是:不﹗我只是為了讓自己的心安住而提款。當地鐵停駛,在車站等候的巴士久久不至,身旁的乘客說已經沒有車子時,我咬了咬牙,知道要徒步走路回家,心裡戰戰兢兢卻異常充實。可是,當超級巿場裡的新鮮蔬菜幾乎被搶購一空,同時無法提取現金,我益發感到眼前的一切虛幻的雲霧終於散去,祼露出陌生而逼人的真實:金錢是什麼?當人失去了安穩生活的配件,鈔票無法取代可以果腹的食物,或變成令人安心的幸福感。正如,當城巿已被管治者的惡意逐步催毀,即使擁有一個價值昂貴的房子,也無法獨善其身。
多年前,我辭去全職的工作,躲在別人的房子裡寫小說時,手頭拮据的恐懼曾經讓我感到腳下彷彿沒有立足之處。我曾經對當時最親近的人說:「身旁的人全都收入豐厚,只有我,如果把口袋裡的錢用作寄出稿件參加文學獎比賽的航空郵費,就沒法買午餐。」
「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說:「時間也是金錢。你可自由地分配自己的時間,使用這些時間創造不同的事物,這也是一種富足。」
當我因為感覺匱乏而渴望囤積金錢時,總會想到太宰治的小說裡,那些無賴的男主角,因為酗酒或放任,欠下巨大的債項,任由女伴為他善後。當我讀到《維榮之妻》裡的大谷,如何掠奪居酒屋老闆在新年前打算用作辦年貨的巨額鈔票後逃之夭夭,使妻子佐知為老闆打工以抵債,我便感到胸口的憤怒之浪在洶湧,而憤怒是恐慌的面具。其實佐知對大谷的不負責任,只有認命似的包容,包容丈夫對自己的任意剥奪。她的包容,固然因為在戰後糧食短缺,人們如螻蟻般掙扎求存,也是愛的責任。有些人以剥奪為愛人的方式,有些人則以忍受剥奪作為被愛的方法。我的憤怒則是因為,小說裡的大谷反映了,愛可能是讓人自願放棄安穩生存環境的陷阱。
太宰治的小說,總是讓我想到塔羅牌裡的「惡魔」,從正位去看,墮落、惡意、頽廢,被物質、權力和色慾駕馭了精神和理性,但把牌倒過來,則是透徹地看清並容納所有的黑暗面後,重新選擇一條自由的出路。
那天,城巿裡多個無法提款的提款機、收銀處排著長長的人龍的超級巿場、路人寥寥可數的街道,還有被催淚彈污染過的空氣,被血跡一次又一次染過的道路,都令我想起「惡魔」牌。我沒有領到錢,卻從不安回復自在,因為我把牌從逆位去看,看到這四個月以來,城巿裡的人從多年來被薪金和樓價操控著的狀況,過渡至以提取現金、取消戶口和把積蓄轉成外匯等經濟手段,奪回原本屬於自己的權力。這裡大部份的人已看破了價格,再略過價格,重新看到人和事物的價值。
空蕩蕩的櫃員機說不定暗藏祝福。於是,我重新點算一遍家裡的食物,屬於貓的罐頭和乾糧,屬於我的擠滿了冰箱的蔬果,怎樣看也足夠一天的份量,而明天的煩惱就留給明天去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