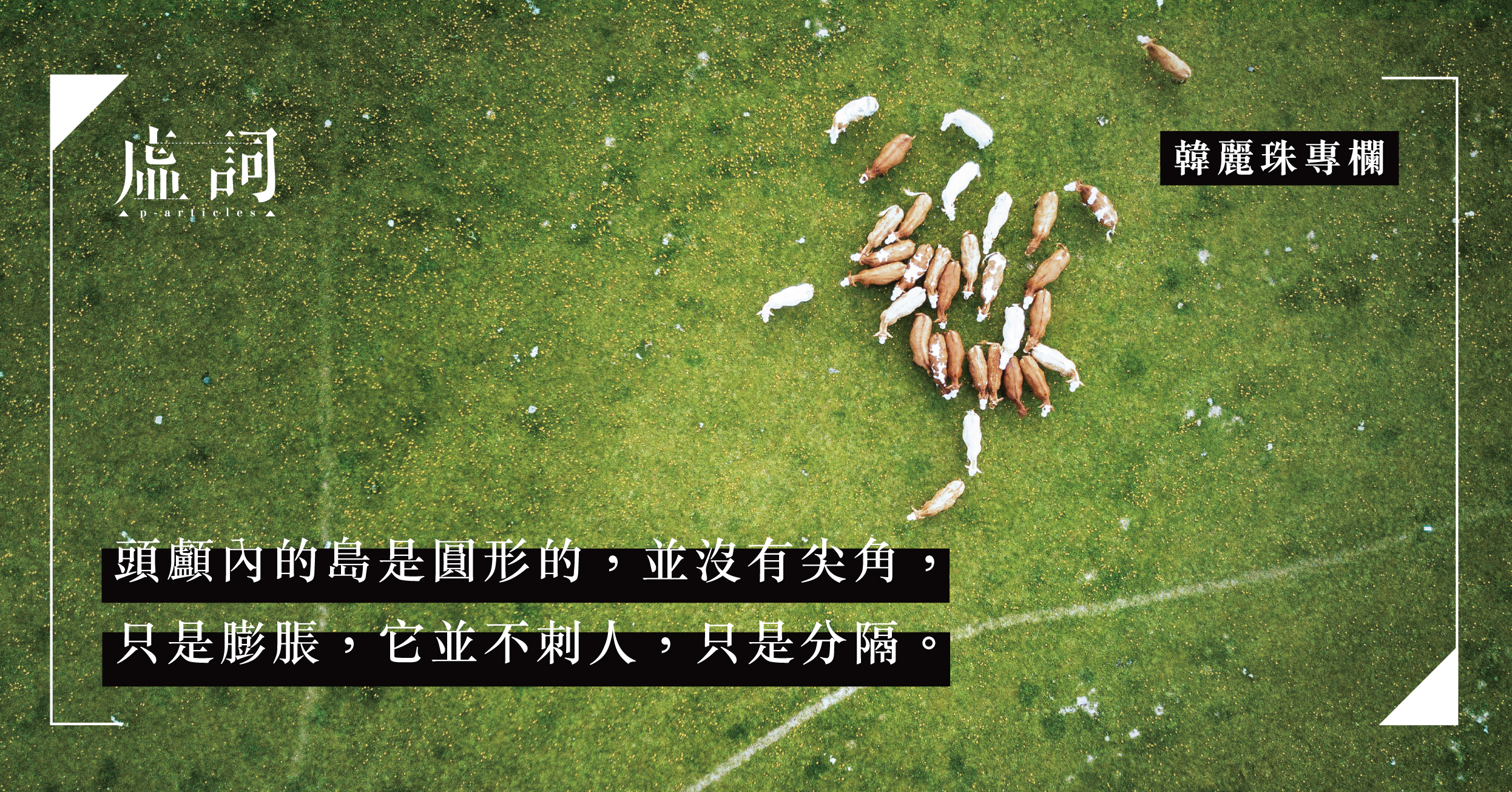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戒肉
成為素食者,並不是我的決定,而是身體給我的訊息,或,設定的界限,但,也有可能,那只是遵從另類療法,給長了腫瘤的人的建議——腫瘤擅於汲取蛋白質,戒掉肉類是遏抑腫瘤生長的必然方法。
「情況比想像中嚴重。」醫生指著電腦掃描的結果說,那是一個懸在腦海之旁的島,圓形的。人的身體有百分之七十是水分,要是島的面積愈來愈大,吸乾了腦海的水,就會帶來各種麻煩——我這樣詮釋他的話。
如果,飲食習慣是對體質的詮釋,疾病是對生活習慣的詮釋,治療方法是對病因的詮釋,我懷疑,在這種種詮釋之間,我只是個無意識地跟隨別人詮釋的順從者。一天三餐,飲和食,人能擁有絕對的自主意志嗎?畢竟,吃飯從來不是一個人的事。
聽到醫生的裁決,我在某方面鬆了一口氣,終於可以拒絕肉類,就像拒絕一個我早已厭倦卻為了種種原因無法割捨的習慣。
頭顱內的島是圓形的,並沒有尖角,只是膨脹,它並不刺人,只是分隔。
人一旦發現了自己和別人之間沒法輕易掩藏的的差異,就無可避免地經歷一場由親密而來的可能導致決裂的考驗。
曝露自己和別人的差異,是一種令人尷尬的誠實,如果可以的話,我寧願戴上「我跟你們一樣」的面具,尤其是置身在我喜歡的朋友之中,可是,身體並不允許我撒這個謊。
於是,每次跟朋友吃飯,心裡都在進行一次恍如被蛻去全身表皮的試鍊。「可以去有肉食也有素食的餐廳。」我會主動對他們建議。(他們心裡會不會有一種「這個人真麻煩」的想法)「去素食餐廳吧,我們也想吃得清淡健康。」有些朋友會若無其事地這樣說。(我會感到被體貼的舒適,但同時也想到這可能是一種禮貌。)「那麼,可以吃海鮮嗎?雞蛋?如果點一客肉類炒菜,你能只吃那些菜嗎?」曾經有朋友在點菜時這樣問。(我想省事地答應,但身體嚴厲地說「不﹗」於是我懷疑朋友是否想說服我吃肉?於是我渴望回到只有我自己的餐桌上。)「這裡有你可以點的食物嗎?」曾經有朋友在某間茶餐廳坐下來點了菜後才如夢初醒地問我,而我能點的只有飲料。(於是穿過了被忽略的感覺,同時找到一個我一直想要的答案:面前這個人,一點也不愛我。)當然,有更多的時候,我被朋友帶到許多裝潢雅緻,菜式美味的素食餐廳,共渡了美好的時光,不過,即使在被珍視的時候,我知道在心底某個隱蔽的角落,仍然在等待他們終於不耐煩,要回到他們肉食的世界去,而我會對自己說:我早已習慣獨自吃飯。
那時候,我會清晰地感到,橫亙在我和他們以及所有人之間,一個巨大的圓形。那個圓形並不是因為頭顱中的圓形島嶼而來。巨大的圓一直都在,我只是通過顱內的島而突然發現了它。我繞著圓形嘗試靠近他人多一點點,然而,圓的直徑無論哪一點都完全相同,同樣的遙遠,同樣的不可接近,那是孤獨,孤獨的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