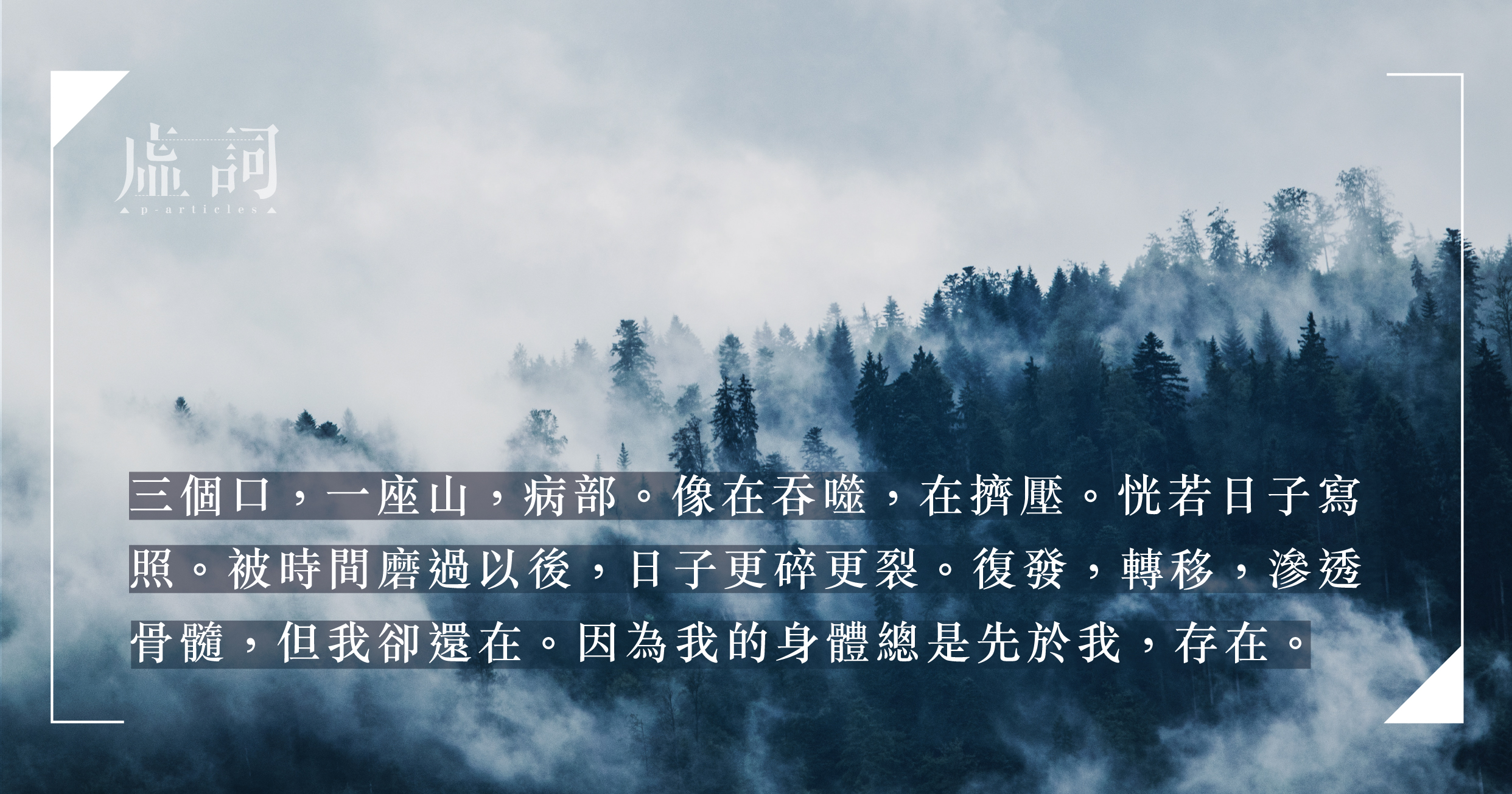極地慢慢之景
把望遠鏡反過來,看直線便覺得彎曲。
三十年,回過神,才發現,一切是真的。
裡面大半日子,由最初的直線,跟著細胞突變,漫長地糾成一團。我沒法改變它的形狀,只能試著解開它。期間,我似乎做了許多事,但其實並沒有。然後學習以一個過來人,一個旁觀者的角色,跟你說話。
三個口,一座山,病部。像在吞噬,在擠壓。恍若日子寫照。
被時間磨過以後,日子更碎更裂。復發,轉移,滲透骨髓,但我卻還在。因為我的身體總是先於我,存在。每當我吞下五角形的藥,便對苦味更加敏感,但它們只是在口裡,再溶進身體裡——已經發生了,已經吞下了,如此而已。
還能如何呢。
霧濛濛,生命也好像潮濕濕的。你關上一扇門,再關上一扇窗,並以這個世界的邏輯給我開出兩個出口(逃出來,或躍下;破門,或破窗)——由頸開一刀,從右側胸口進入,對落兩吋伸出[1],一紅,一白。進入血管,藏在底層,通向心臟中央靜脈。紅的輸血落藥,白的抽血吊鹽水打針。紅色白色紅色白色,底層之下一堆細胞狂熱分裂,不斷繁殖。喧囂會有靜下來的時候,四包大,一滴一滴慢慢滴下來,我躺著,一動也不動。
上帝說光,就有了光。天花板的白光管猛地照著,要求堅強,要求不哭。我頭向左側(有時向右),躺下,面向牆,屈膝,將外褲內褲往下拉,拉到屁股。針,應該說,鑽,插入腰椎,從推的力度可以感到它似乎很粗,而且不短。骨髓在骨頭中央,是生產血球的海綿體,抽的時候有時較實,有時會白白乾抽。針,應該說,鑽,呈T形,在髓腔裡面不斷旋扭不斷旋扭,有時用刮,像把劇烈的酸、脹、麻、痺緊緊鎖進骨髓裡面。忽然一下抽拉,再一下抽拉,發出類似引擎的尖銳吱呀。聲音沒有彈性,在腦後抽空一下。緊盯牆上的鐘,拇指食指指甲捏實被角,咬唇,咬齒,一陣消毒藥水味——粉色的布簾拉開,同時拉開隔著現實的一層血肉,一切流動總是虛幻的,時鐘走向十二點半。
幾乎所有兒童及青年癌症都是因為DNA隨機錯誤造成的。
結論:運氣不好。
方法:摧毀骨髓摧毀細胞,空出來,再讓新的骨髓重生。即移植。
移植,重生,概念一下變成具象。身體實實在在變成一個難以居住的地方。
K8N,獨立隔離,白色無菌。保護衣、手套、口罩;發燒、紅疹、生蛇、微絲血管破裂、口腔潰爛。含冰粒、小心刷牙。數字是僅存的一切,0.4,7.4,等待白血球生長。輸血輸血再輸血,把空白密密填滿,藍藍瘀瘀,像極地慢慢之景。
一百天。打開門,拆喉,時間終於與空氣對流。在紅白二色的暗室裡,拮一針,種豆,年月便半真半假地如蕨敞開。一天一月一年,於是以為,越過五年存活期,鹽水架也會生出一種濕漉的綠色喜悅,像快長成一棵樹蕨。因此,我常常抬頭看樹,想看看樹到底在想甚麼。
有時覺得,微物世界的一切原來非常頑強地排斥著人。人,並不似我本來以為的樹,而更似入秋就掉落的,那些葉。
五年存活期其實僅是一個數據,那些連續劇的情節,醫生的話,陰影與壓痛,愧疚與負擔,才是虛幻而實在的,生(宿)命。去亦無路,退亦無路,為甚麼走一會鞋帶便自己鬆開。也許有些人懂得,但我不懂,不懂得路是否也會自行終止。生命的運氣問題必然大於公平問題嗎。我不知道,我不能把它們分開來想。因而你說,或許宿命,就是生命之中最正常,最健康的部分。
身體駕馭意識,意識駕馭身體。一隻手按著疼痛,一隻手拿著聲音。在一堆回憶與現實之上,追記是徒勞的,記憶的本質便是破壞,便是逐漸惡化。這麼多年的是日早餐,雞蓉粟米粥,那個托盤依舊散發著一陣塑膠味。生活會被絞碎,但我還未被肢解。生存,本來不就是向心的嗎?
人一下子出現,就消失。往往這樣一會,便沒有了。我在這人生至大之因果,之疼痛之中,僅能從一種語言結構,重建自己,像結繩記事,用象徵把握現實。那是因為,我體內有個人,掙扎著,想穿透一切,走出來,完成生命的最後動作——呼出最後一口氣——便重獲新生。
[1]叫希克文導管,又叫喉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