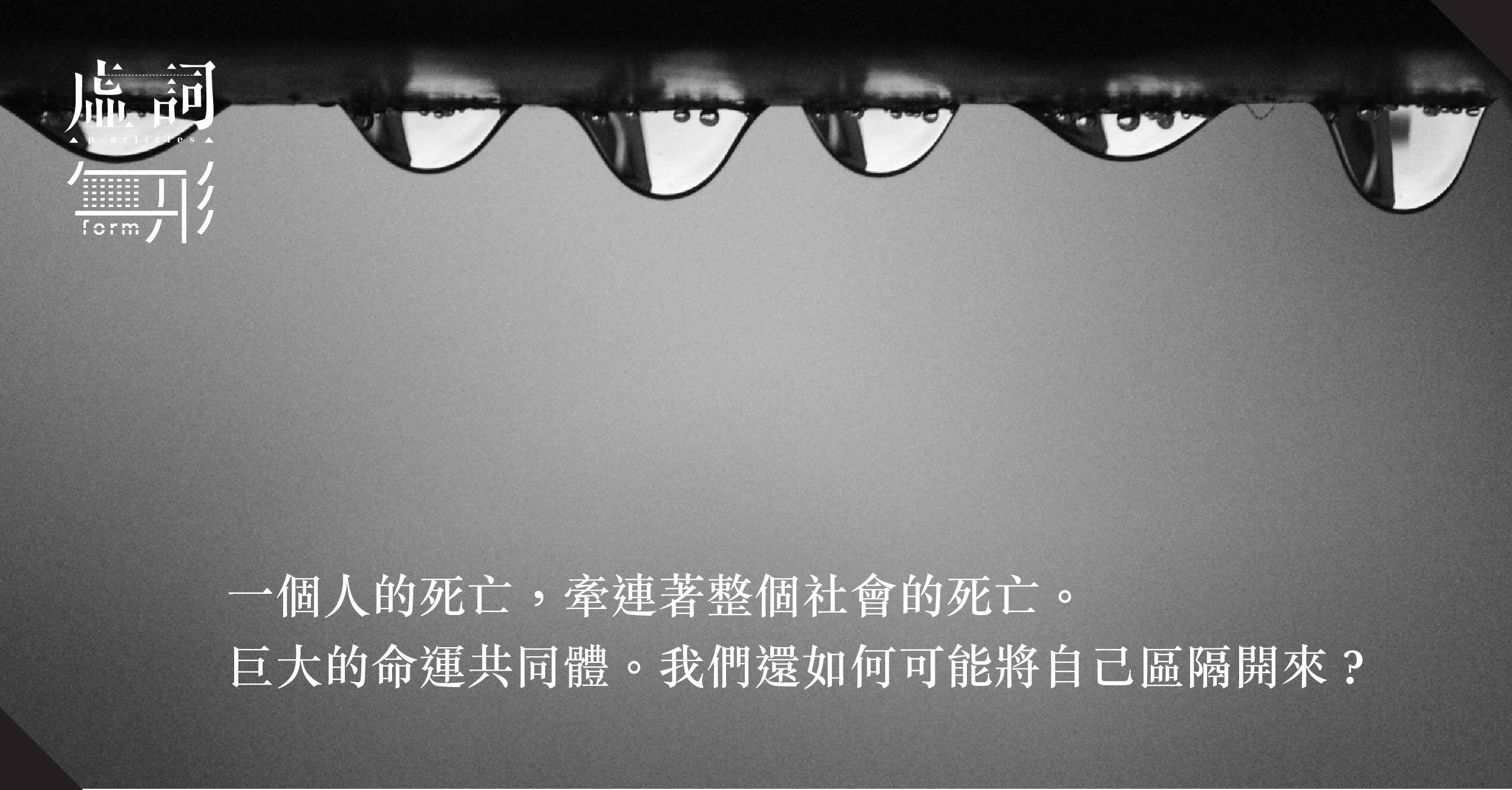【無形.黑】那不存在的光
把房門關上,把窗關上,窗簾拉上,把燈全熄滅。在這個時刻,窗外仍有很多不能熄滅的,不知意味著甚麼的零星燈火,以及各種黑與灰的事物,但凌晨依然是凌晨,太陽將從東方升起的事實亦沒有改變。
是怎麼樣的事實呢?我總是說不上。以我的表達能力,可以理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這並不緊要,因為我知道,的而且確知道,那不是一件要去感受的事,而是,我們直接就在其中,在千萬的無言者之中。
黑或者白,光或者暗,我多希望它像許許多多其他的事一樣,可以選擇。
不是痛楚,猶勝痛楚。
一瞬之間,你覺得整個世界都變了,變得如此的醜惡。
閉上眼,一個畫面,一件件不合理的事實橫卡進眼前。無數愛過與痛過的生命曾在此游移、掙扎,九死一生的掙扎。
一個人的死亡,牽連著整個社會的死亡。巨大的命運共同體。我們還如何可能將自己區隔開來?
沒事。我說的不過是一件,又一件,被刻意隱匿的,發生了不可挽回的,種種(個別)事件,(是事件,沒有脈絡)而已。(如同旁觀一場生死表演,斑斕都市中的一道瘡疤)然而當它的枝椏往內伸,長葉,變樹,就會橫溢而出,戳穿一個巨大謊言,那不存在的光。
*
見樹,見林。這個場景於是不停在我的夢中出現,延伸,變動,有時是一座黑暗森林,有時是被四堵牆包圍。就好像毫無選擇地走進病化的內牆,一個明明熟悉,卻不敢指認出來的空間。當目光繞過,發現原來一直有個龐大的黑影在推著,像異形一樣隱藏著,並黏附在人的暗面,生長在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惡上。只一剎那,黑流盲動,重量壓下來,拉向意義崩潰之地,到最深,最底——
不是選擇,不是放棄,不是這樣的東西。
是被一個更大的世界威脅,那是我們的世界。
那是絕望。
甚麼也看不見,甚麼也不被看見,把苦難丟進荒蕪。但社會總是沒錯的,錯的總是我們自己,總是那些最平凡最普通的人。弱勢,權力,罪惡,正義,被拉,被鎖,要你有罪,你就有罪。被制度默認,縱容,乃至鼓勵,撐到最後一刻,為甚麼會連憂患亦無處容身,終被迫向自戕一途。問題困在腦袋裡,四周的物件會繞著打轉,如同浮木失去平衡。不停問,不停問。又如同一個懸空的人,一直懸在不敢看向的窗邊。
從高處。我的眼睛好像慢慢與真實連結。
每個人都可能被逼上絕路,我嘗試感受思維如何在你腦中跑過一遍。
是跳。還是墜。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總是在這樣的夜的邊緣,在很多個一模一樣的夜裡,一個人也沒有的時候,事實擺在眼前,滴在纖細的幽暗裡。那質地與曲線對接,緩緩沉入無光。
*
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開了。暗為夜。
黑暗就感覺空間。幻想著,把四面牆變成一道門,穿過它,穿過它才可以安然出入生死人間。我要想的,是以何種方式穿過它。彷若一切還有形狀,一層緩衝轉化,彷若創世。
或許我還年輕,年輕到對一切事物都要尋求意義,微細至一首歌一個數字一隻飛過的烏鴉,但世上就是有太多毫無意義的純粹發生,只是剛巧,命運的鐘聲響起。
又或許不過是,人的限制。
就這樣眼睜睜看著,那失眠者的月亮,那一片黑色的光,像生大於死,也像死大於生。完全不知起點在哪裡,也無從揣測終點該在哪裡。在這大起大落的兩重境界,無限大之中,世上每事每物以它所能的姿態來到眼前,考驗我們,我不自覺地提出反駁,如同一場生存角力,一場虛弱的抗辯。
問題沒法想明白,又同時知道,答案是無意義的,僅夠平衡那虛空,那沉重。想著拆解的可能,也許亦是我的一種自私。
*
點亮刺眼的燈泡,如點亮那個承受它的人。像一顆溫熱的心臟,某種強韌力量。當被光包圍,靠近熾熱,便沒有任何東西不再存在。而我,也不再去否定邪惡,不去否定自己身上也有的惡。想起馬格列特的畫,光的帝國,白日與黑夜並無衝突,可以矛盾共存。
光暗交匯,在暗處企望,就有影子。問起公道,我們能討回的,只能是意圖埋葬的真相,不是已經埋葬了的生命,而明暗不是此刻隱喻,是生命真實。從不是愈辯愈明的,消失在人群,在語言。彷彿不同的,是姿態而已。那麼把墜下設想成跳躍可以嗎。恍惚,疼痛會推遠成遙遙的一顆白白光點,一顆白白星塵。白白死去。
由生到死的路到底有多遠,有多近?「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甄士隱剎那頓悟,恍恍惚惚不知不覺,我們又走進了兔子洞。如夢方醒,來到這裡。好了。
*
生命延續,夜已極深,那小時候的手影小狗似乎還留在牆上,我曾牢牢緊抓的生命,現在竟在想著,要讓它加速溜走。又有一點痛,輕微的,正一吋一吋蔓延全身。
在窗外,太陽照常升起,一節一節地濛亮起來,像免於恐懼,像從未感受過不幸。而後面,有一朵雲埋伏,像個暗影,像世界本來的樣子。光明與暗影越來越近,時鐘向前撥了一格,今天、明天、後天,還有很多很多往下升起的,昨天。
(這篇文章是每晚二三百字寫成的,寫了一星期,幾乎無法寫出,覺得怎也無法成篇。大概這段日子,維持日常已耗盡了生活裡僅剩的力氣。或者,無法勉強拼合的文字正如無法勉強的生命。抱歉我總是寫不好,可是已經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