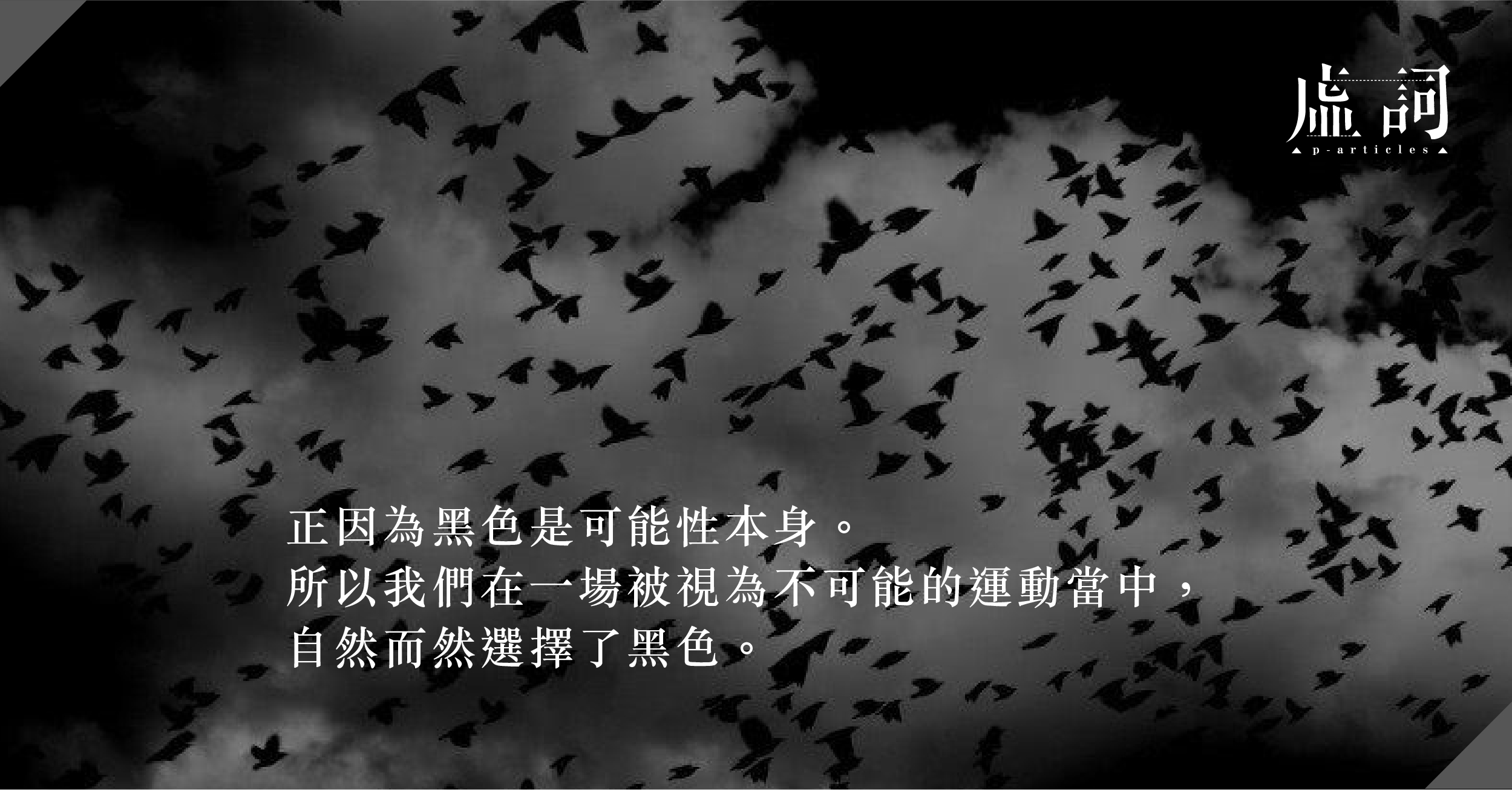【無形.黑】黑色,我多麽愛你黑色
相對於巴丟草設計的那面七彩繽紛得有點像百衲衣的連儂旗,我更喜歡運動初期常見的黑色半枯洋紫荊旗。除了對原本香港特區區旗的反諷,我曾一廂情願地認為它是從屬於國際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的譜系的,是在香港已經息微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捲土重來,哪怕只是美學上的。
然而在香港這個保守的城市,一下子就有很多人「提醒」運動者,「黑旗危險啊!」黑旗意味著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意味著政治光譜的極左部份」,「意味著全面推翻政府」,「意味著恐怖主義!」——這真的非常可笑,簡直就像魯迅先生《小雜感》裡諷刺的道學家:「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這樣的城市,就沒有無政府主義根基了嗎?這場運動真的跟無政府主義沒有關係嗎?在運動初期,我寫過一篇文章向台灣讀者闡釋我所見的這場運動,文中提及:
「打不死的,是香港人的義與愛。平時也許不苟言笑、冷面待人的香港人,一起並肩走上街頭的時候,天然地擁有了安那其主義的互助精神。6月12日撤退下來的人的回憶書寫中,記載的很多都是身邊陌生人伸出的援手、遞過來分享的物資,其中有把僅有的雨傘送給兩手空空的女生的男孩,和新聞鏡頭所見那位守住地鐵站入口一再從警察群中接回落單示威者的孤身黑衣人一樣令我感動。既然選擇了放棄大台指揮的游擊戰,作為靈活個體遊走的抗爭者自然懂得結聚力量的必要。」
這裡面強調的兩點:「互助」與「個體」,恰恰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核心價值所在。且看維基百科裡這一段多麼清晰:「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立場是反對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統治和權威,提倡個體之間的自助關係,關注個體的自由和平等⋯⋯」
有很多人誤以為無政府主義等於自私的個人主義,但看看無政府主義祖師爺之一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他是這樣說的:「國家吞沒了一切社會職能,這就必然促使為所欲為的狹隘的個人主義得到發展。對國家所負義務越多,公民間相互的義務顯然將越來越少。」我想倒過來說,對政府所負義務越少,公民間的互助則越多。安那其之間的互助,克魯泡特金告訴我們:「那是比愛或個體間的同情不知要廣泛多少的一種情感——在極其長久的進化過程中,在動物和人類中慢慢發展起來的一種本能,教導動物和人在互助和互援的實踐中就可獲得力量」,這就是安那其主義的積極性,它為抗爭賦權、賦予最本源的能量。
「個體」的重要性,在這次運動中更加突出,我記得早在《美德》,董啟章就預言過這種未來的抗爭型態:「孩子們看似同行,實則孤立,心不在焉地以散漫的隊形進發」——董啟章有意無意地寫出了新世代抗爭者的特點,他們是新的安那其主義者,是不需要發牌者(大台)的塔羅牌們。
香港本來就存在踐行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環境和政治基礎。我們可以、也曾經發起、參與一種獨立於政黨之外的社會運動,直接跟社區、跟無政黨背景的民眾發生關系。這種運動是游擊戰式的,不是為了爭取某個議席、某張選票而去采取某種行動,而僅僅是基於一個個體對某事件的反應——你不用去捆綁別人,也不用去號召別人跟你一起做,你完全可以一個人去遊行抗議,這是立足於個人主義、而非集體主義的政治行為。雨傘運動前後,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無政府主義實驗。
回想2000年,我寫過一組詩叫《安那其先生的黑色歌謠》,時維1999年西雅圖反世貿「暴動」一週年,自命無政府主義者的我無緣於暴動,只是在華西街夜市買到一件寫著「無政府」的上衣天天穿著,未免有點悲涼。於是寫了一首自嘲之詩,且錄其中兩段:
1,安那其先生的誕生
黑色啊黑色,我多麽愛你黑色
當我被人視爲烏鴉的時候
我樂於往自己身上披上黑夜。
在世界的一個角落,承受了夏天
它歪著翅膀的突襲。
光頭閃耀,光環落在我身上,
我束緊然後脫離,我明亮然後神秘
我誕生像一枝箭,在風中破開。
從辦公大樓摔下我的憤怒彷彿決堤,
革命太火熱了,我決心親近勞工
鑽進廉價衣物堆,
從華西街買回我墮落的標誌:
一件黑色長衣,印著無政府三個大字。
黑色啊黑色,我多麽愛你黑色
當我被獵槍擊中的時候
我讓自己的傷口叫喊出一聲毒血。
3,安那其先生的日常生活
革命過後我假裝熱心家事
把對混亂的渴求訴諸洗衣機的旋轉,
我的熱情眩暈也如洗衣機!
於是我冷酷,指責,我不相信:
電冰箱焉能禁錮巴枯寧?
黑色啊黑色,我多麽愛你黑色
我趁著黑夜席捲安那其先生的帽子和斗篷
我連滾帶爬力圖從瘋人院飛越。
沒有辦法了,晚上接小弟放學
我才找到了生活的無政府意義,
敲打著欄杆和燈柱高興地唱: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直到監獄裡傳來回聲:
黑色啊黑色,我多麽愛你黑色
我只好過馬路時拼命違反交通規則
我只好上網吹牛冒充黑客。
我欣然見到今日的抗爭者不必如此自嘲,他們沒有無政府主義之名,卻有無政府主義行動之實。
而且我始終相信快樂抗爭(這個概念跟無政府主義是緊密結合的)的必要性,即使現在已經到了革命前夕生死存亡的關頭,但我們仍然可以向意圖製造恐怖的權力展示:政治抗爭不只意味著你們所信奉的殘酷、暴力、血腥,快樂抗爭的方式本身就昭示了我們的選擇、我們與恐怖權力是兩個世界的人。我們這樣也是告訴那些不去抗爭的人,讓他們明白,喔,做一個反對派原來可以這麼快樂。反對派不一定就是被迫害、生活在黑暗與痛恨裡,他可以捍衛自由的同義詞:幸福。
說回黑色吧,為什麼安那其選擇黑色?除了這是有利於游擊戰的夜行衣的顏色。我還有一重理解是:這是對想像力的捍衛——憑什麼黑色就意味著恐怖主義?意味著絕望、地獄、負面⋯⋯?無政府主義秉有一種最基本的挑釁態度,那何不從對顏色的主觀定義開始?黑色為什麼不可能是彩虹?
正因為黑色是可能性本身。所以我們在一場被視為不可能的運動當中,自然而然選擇了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