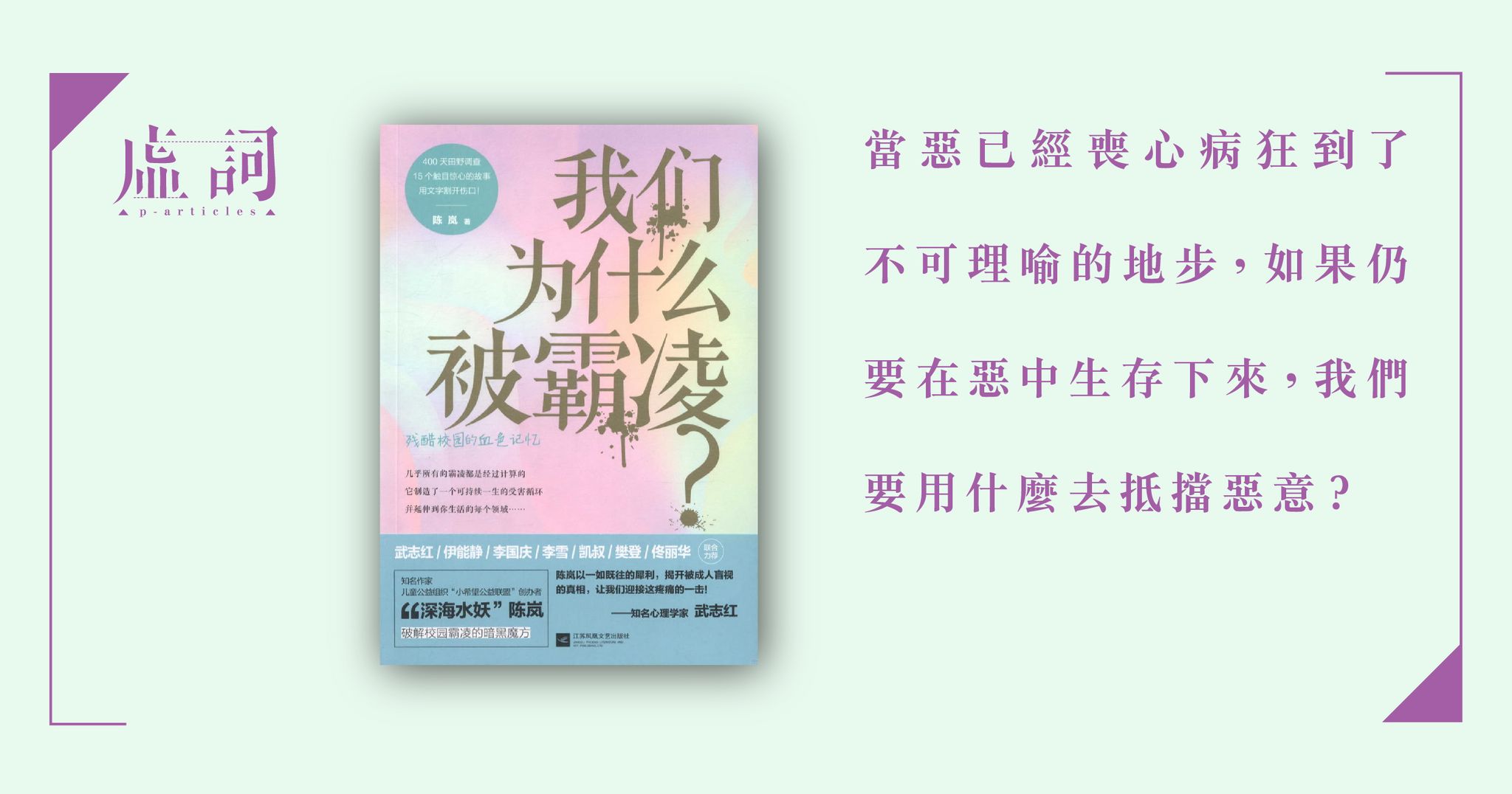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與愛的距離——評《我們為什麼被霸淩?》
2018年新年的時候,我再一次走進了我的初中。
我穿過操場,那些似曾相識的花仍然在花壇裏開放著。我沿著花壇慢慢走向教學樓。我看到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兒,背著龐大的書包,肥胖的她低著頭走在路上,畏畏縮縮地把脖子不停地縮進臃腫的大衣裏,不敢與他人直視。她爬了個坡,走到了諾大的操場上。突然,一群又一群的人湧過來,對著她指指點點,她的耳朵裡充斥著四面八方的恥笑,她的帽子裡有四面八方丟過來的垃圾,她的眼睛裡是極力掩藏著被鄙視被侮辱後強裝鎮定的驚恐。她想向站在遠方的老師求助,老師抱著雙手若無其事地冷笑著看著她。她想向父母求助,寒風中的父母看著已是差生的她,眼神更是淩厲。她就這麼一個人站在人群中,不知所措。
我走過去,向她打了聲招呼,對她說:十年了,我來接你了。
操場上的我,抱著十年前的自己,蹲下來,泣不成聲。
那時候的我,並不知道有一個名詞,叫做霸淩——「由少數人帶領的群落,對個別人圍攻、羞辱、孤立、譭謗,並對對方的身心進行持久的傷害」。
即使是上了大學才知道這個名詞的我,忍然不齒於將被霸凌的經歷「廣而告之」。因為那每一個只會吃了睡睡了吃的日日夜夜都刻畫著一個成績越來越差的我,刻畫著一個活得行屍走肉的我;刻畫著中考失敗後在全家人冷暴力生活下的我;刻畫著小心翼翼的我,以及恐懼自己的我。
我恐懼我自己。因為我有錯。
那時候的我堅信:應該沒有人會有我一樣的經歷。那時候的我不會想到在多年後的一本書中,我會遇到15個人,他/她們用他/她們真實的霸淩/被霸淩的故事,將他/她們傷痕累累與鮮血淋漓的痛又或是不可理喻的惡告訴世界——《我們為什麼被霸淩?》,以及「我們為什麼去霸淩?」
十六歲的林歡站在初中食堂裡拿著餐盤打飯,快到窗口的她,忽然被後面走上來的一個不認識的同學插到前面,然後越來越多的同學走到每一次都要到窗口的她的面前,理直氣壯地打菜,並明目張膽地用厭惡的眼神對著她耀武揚威:「你不有本事嗎?找你爸爸媽媽給你去開後門呀,你去上哈佛耶魯的人,跟我們在這兒擠啥?」「就是,讓你爸爸媽媽給你開個食堂唄!」窗口裏的打飯師傅看著林歡不斷地被人擠開,幸災樂禍地看著,笑著。
食堂裡的林歡犯下了什麼滔天大錯呢?
林歡放下盤子,走回教室——全班沒有一個人和她說話,她的試卷被人扔到泥水裏,書包裏被人塞癩蛤蟆,做對了的題被打叉——她是賤民。
教室裡的林歡犯下了什麼滔天大錯呢?
當林歡被教師李清要求在黑板上前畫出超出了課程大綱阿米巴蟲的時候,已經超綱學習過的林歡竟事無巨細地將其畫了出來,然而換來的卻是咆哮的李老師:「你跩什麼跩?......看把你能的!耗子吃了二兩油,癲狂得不知道自己姓甚了!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看看你是個什麼鬼樣?......你看看自己的那張臉,披頭散髮,頭髮一摔,擱在人家明星身上那是風采,擱在你這樣的胖子身上那是瘋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你看看你這張臉,不用化裝你就能去演《聊齋》,對,就演那個前面是頭髮,轉過來還是頭髮的女鬼!哈哈!」李老師甚至在所有授課的班級散播著「一個叫林歡的女生,利用她爸爸媽媽在官場的身份,欺壓她這樣一個清高正直的女教師......準備行賄,被高貴廉潔、剛正不阿的她嚴詞拒絕了,她隨時等待著打擊報復,並且準備為自己的人格戰鬥,甚至犧牲。」
這些未成年人與旁觀者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所做出的惡,居然是來自於一位「人民教師」的語言與行為的殺戮。
林歡做錯了什麼?只因為她會畫阿米巴蟲嗎?
一個「教師」,為何如此喪心病狂?又為什麼沒有人站出來,站出來拉深淵中的林歡一把?為什麼每一個人都成為了旁觀者?甚至是幸災樂禍的觀看者?
十六歲的劉小榮加入了一個叫「伐木累」的小群體——其中包含了六個女孩子:小寒姐、平姐、小於姐、小連姐、小奇姐、蘭蘭姐。晚歸宿舍的劉小榮在被來開門的室友小婷憤憤問:你咋不帶鑰匙啊?怎麼沒忘記腦殼後,向「伐木累」的姐姐們裏撒嬌抱怨。於是「伐木累」組合氣勢洶洶地衝到宿舍,將小婷又踢又踹地拖到了學校門口的賓館——「小寒姐把皮帶解了下來,沒頭沒臉地就朝著小婷抽了過去。啪的第一下,小婷慘叫起來——小婷的胳膊上頓時起了一條一指厚、三指寬的紅痕。小寒姐突如其來的暴戾馬上激起了平姐的回應,她上去就朝小婷的小腹踢了一腳,小婷整個身體都飛了出去,撞在牆角。平姐走過去把窩在牆角的她揪住頭髮拖起來,轉頭示意我往死裏抽她。十六歲了,我從來沒有打過人,連狗都沒踢過。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平姐說的話就像有魔力一樣,我不僅走過去,像模像樣地舉手就抽了小婷一嘴巴,而且熟練得就像我已經這麼幹過幾百次一樣。小於姐虎身上去又是一腳。小婷被踹得連連後退,站在另外一邊的小奇姐、小連姐連著兩腳又把她踹回來」。隨後「伐木累」將小婷的衣服扒了,把全身赤裸的小婷扔在洗手間的地上,打開水龍頭,平姐抓住小婷的頭髮,把她拖拽起來,讓她跪在水裏。回到宿舍後的小婷,一口一口的黑血往外嘔。
為什麼這些女孩子們如此喪心病狂?為什麼被小群體「伐木累」欺負後的劉小榮居然加入了「伐木累」?為什麼十六歲從來沒有打過人,連狗都沒踢過的劉小榮在群體的慫恿下從被霸凌者變成了霸凌者?
因為家,「伐木累」的含義是:家。
被「姑姑用木盆裏摔在身上」,被不願讓她唸書並克扣學費的父親叫嚷著「這些都是老子的血汗錢,你日後掙錢還給老子」的劉小榮來說她從未受過愛。所以當她有了以「家」為名的群體庇護的時候,她「在同學們眼裏看到了羡慕」。單獨的她,缺愛又孤獨;群裡的她,「溫暖又安全」。她在群體裡終於被「關愛」被「保護」被「擁抱」了。為了一直被「擁抱」,為了獲取「家」的認可,她和「家人們」一起走上了作惡之路。
我們與惡的距離,不過是與愛的距離。
當惡已經喪心病狂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如果仍要在惡中生存下來,我們要用什麼去抵擋惡意?
十六歲的林小榮沒有被判刑,她被勸退,離開了學校,「伐木累」的其他成員被判數罪,進去了一個可以讓她們束縛行為的地方。而不愛她的家人更是覺得羞恥,父親積極策劃著讓她嫁給一個老光棍。
十六歲的林歡沒有去哈佛,也沒有去耶魯,她去了斯坦福,念心理學碩士。父母無條件的愛鍛煉了她自我的堅毅,也成為了她穿越黑暗激流的力量。
愛讓人受傷,也讓人療癒。
十年後,唸書回來的我,回家整理初中時代的東西。我拿出畢業後就再也沒有開啟過的一個鐵盒子。我打開它,盒子底部有一個白色信封。我拿出來。白色信封上畫著一個粉紅色的足球,帶著一雙金色翅膀。我隱約地回憶起那是中考後的盛夏——終於擺脫了那個學校的日子,我在800米的跑道上揮汗如雨。一個清瘦的男孩子走過來遞給我這封信。他是我已經不曾說話許久的同班男生。不想與這些霸淩者有關係的我,回到家直接把信鎖進了盒子。
我慢慢打開信,一張空空如也的白紙呈現在我眼前。我奇怪:哪有人送一張白紙的?突然我想起那幾年我們流行一種「隱形筆」,那是一種只能在紫外線照射下才能看到字跡的一種筆,於是我把白紙放在光下。密密麻麻的I LOVE YOU鋪滿了一頁紙。
隱形的字跡,終於在光下顯現。
那些沉默的愛,終於在十年後讓我知道我不是一個人。那些沉默的愛,雖然沒有站出來幫助我橫掃千軍萬馬,但仍然有人用沉默的行動告訴我,在那個黑暗世界中,「千夫所指」的自己依然被隱秘的愛著。
在黑暗處,我看到了那些沉默的愛在群體中不能發聲的無奈。時隔多年,它們終於見到了光亮。
如今,在教育和生活的現場,我也仍然在日常地被霸淩著,被言語與行為隱性或顯性地攻擊著——我的耳邊不斷被充斥著「你不要臉」「你拽什麼拽,你二十年都不要妄想著超過我」「沒有我的幫助,你一事無成」「她這麼垃圾,不要和她玩兒」的這些來自權威的霸淩。目光所及之處,霸淩——教師霸淩孩子,教師霸淩教師;客人霸淩服務者,服務者霸淩客人;父母霸淩孩子,父母霸淩父母,孩子霸淩孩子;熟人霸淩熟人/陌生人;陌生人霸淩陌生人;甚至國家霸淩國家——也無處不在。
我仍然會發抖和恐懼。而我可能終究也是懦弱的,像那一份沉默的愛一樣,我也沒有學會立馬站出來去為自己為他/她人聲張正義;但我又似乎比過去的我更勇敢了一些——逐漸學會採取隱性的方式抵抗霸淩者,學會了用紙張與電腦來承載被霸淩後的戰慄、憤怒與恐懼;學會了讓被霸淩與霸淩見到光;學會擁抱被霸凌者,以及自己。
無奈,這份單槍匹馬的勇敢,過於沉默,過於懦弱,過於杯水車薪。如果這份勇敢能夠強大起來,那會是一幅怎樣的畫卷?
〈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