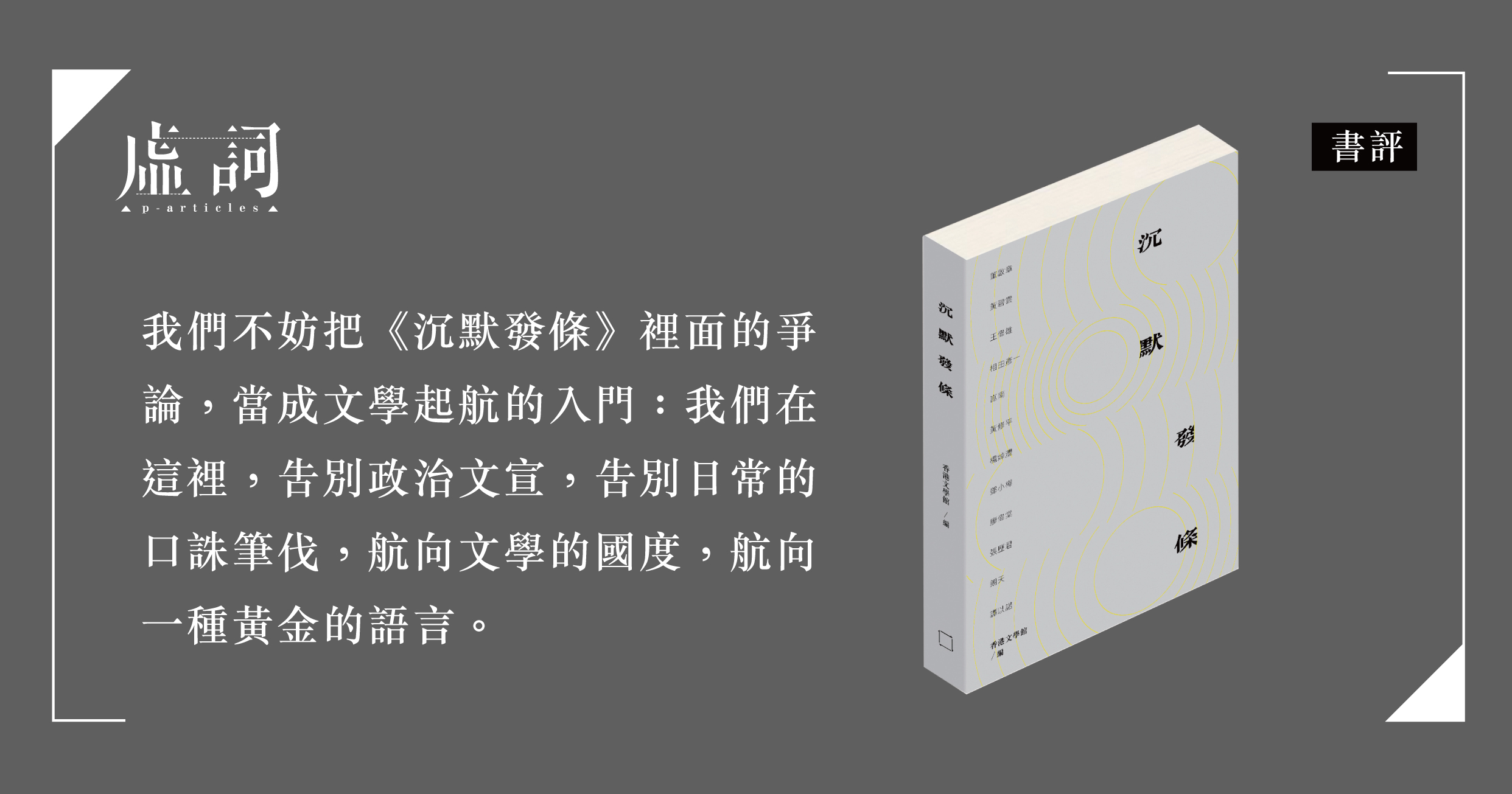自我對抗,文學起航——讀《沉默發條》
2014年,董啟章被選為香港書展年度作家,該年香港社會對於佔中抗爭的討論正白熱化,及後發生了雙學佔領金鐘的行動,此時此刻年度作家成為敏感的名稱。議者認為作家既然支持社會抗爭,就應拒絕與建制有關的一切,而董啟章的回應是在書展作家感言裡,大談「沉默」的意義如何被扭曲。根據董的說法,近幾年來社會有個錯覺,認為「沉默」就是負面的,而「發聲」就是正面的。董氏認為這就是語言被濫用的現象,一如在關於社會運動的報告和描述中,「暴力」也被濫用來描繪抗爭者的行動。
沉默,一種內心流亡
讀著《沉默發條》的時候,我也在思考究竟甚麼是「沉默」,我想到在德語中,「沉默」並不是名詞,而是動詞。當然schweigen這個動詞也可被寫成一個中性的名詞schweigen。大概「沉默」不單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行動。恰巧英、法語言中的silence都源於一個拉丁文動詞:silere,後者的意思是靜下來、無聲。原來「靜下來」也是一種動作,是主動的而不是被動的動作,一種經抉擇而作出的行動。在今日高舉鄂蘭的vita activa的社會中,把沉默說成行動彷彿是對沉默的「肯定」。另外,沉默也是一種語言,因為沉默也不止一種形式,不同的形式就有不同的跡象,可以從中讀出不同的意圖。
雖說沉默是個人決擇下的行為,但人們只能從那個人沉默背後的事件背景,才能對他的「沉默」進行定義或判斷。西方對「沉默」的論述由來久遠,始於晚期羅馬帝國的神祕神學,這種神學觀認為,由於最高的智慧是某種不能被言說的奧義,故必須對其保持沉默,這種傳統延續到現代語言哲學家維根斯坦的那句名言:「在不可言說之處,我們應該保持沉默。」另一位是現代極權體制下作家所謂的「內心流亡」,因危及生命而被迫對政權保持沉默,但沉默既是不反抗,也是不默從的跡象,不默從發聲表現出作家的獨立人格。有時候,沉默還意味着因抗議而刻意放棄發聲的權利。
在董啟章於2014年書展講座的講稿〈默想生活:文學與精神世界〉中,作家從語言和發聲去討論沉默。這種沉默的跡象背後,是作者面對香港日漸崩壞的政治環境,以及對於有人選擇附和,有人選擇怒哮的反應。作為著名作家,選擇在任何一個陣營下搖旗吶喊,或發出同意或反對的聲音,自然少不免將文學語言與政治語言混同,因而有損文學創作的尊嚴的,但對於政治事件沉默,即同樣會被看為無視社會現實,亦違背了文學的人文關懷。董認為不得不重提、思考甚至選擇沉默的背後,表現出作家面對這種兩難的困局。
基本上,董啟章那篇講稿切中了作家所面對的問題,在某些定義方面,例如將文學定義為一種默想生活、認定文學介乎於行動與沉默之間,我們還是可以商榷一下,留有細微的討論空間。首先,文學並非不屬於行動的範疇,而沉默也並非不是一種行動,正如並非不發聲便等於沒有作出行動。當我們討論沉默時,必然是沉默者為其沉默行動賦予了意義,我們才覺得有討論之必要。還有的是,在文學作品對某一事件或政治問題保持沉默,這本身就是對於該事件或政治問題表達了態度。
默想,對抗語言的誤用和過量
「從默想生活,生成文學⋯⋯」黃碧雲在為書展講座而作的講稿〈必須與世界隔絕,才能靜想〉裡面,大篇幅地討論這個課題。文學需要讀者,猶如演員期待觀眾的「觀賞」,而「默想」的對象是神。如果像黃碧雲說的,默想生活的封閉、孤獨,是為了打開世界所有,那麼這種封閉和孤獨只有在神在場的情況下,才可能將世界打開。另一個問題是如何避免令孤獨淪為寂寞的危境。這是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最後一章念之在茲的問題,鄂蘭引用尼采的詩〈席爾斯.瑪麗亞〉(Sils Maria),說明自我的「一變成二」是為了防止自我陷入「寂寞」的境地。我們默想,不也是一種「一變成二」的內在對話嗎?
董黃兩人堅持以沉默和默想對抗語言的誤用和過量,然而沉默歸沉默,沉默也只是語言中間的一種停頓,文學還需面向世界,向世界表述自身,扣問世界,或嘗試與它對話。曼德爾施塔姆說詩歌應該像一個漂流瓶,詩人只能期待漂流瓶最終在他方岸邊為一個讀者拾起,但總會有人拾起,不然文學何為?
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曾以梅爾維爾小說《錄事巴托比》討論「潛能」這個哲學概念,除了阿里士多德對於「潛能」的解釋外,巴托比慣用的口頭禪「我選擇不⋯⋯」(I prefer not to ……)還為「潛能」提供另一種定義。放進作家那裡,這種「我選擇不」的態度就好像比拉—馬塔斯(Enrique Vila-Matas)小說《巴托比症候群》裡面選擇封筆或不把腦中作品寫出來的「作家」一樣,我們就想像世上有那麼一個從不發表作品甚至從不訴諸筆墨的作家⋯⋯
如何航向文學的國度
然後每當我們提筆創作時,我們總無法忘掉那幾個問題:
文學既是處於自由探索的狀態,它本身有沒有必然/必要的目的?
文學本身有沒有必然/必要的義務?
如果文學有一種義務,一種以其正義為目的之義務,它的義務對象有多少?
如果有許多對象,會有最高至最底之分還是所有對象都有等同的地方?(譬如:社會公義、發現人性、挑戰理解力的極限,發明一種嶄新的美,等等。)
普遍認為偉大的、真正的文學,是應該服膺於上述哪一種對象?
應該從這些方面,討論董啟章就文學沉默所闡述的論點,及其他人讚同或批評的意見。論者或會質疑董啟章討論「沉默」的動機,但這並非我們從事文學創作時最核心的問題。
想像一下我們的社會,沒有人從事文學創作(研究論文或職場報告不算在內),連最通俗的文學作品也沒有,對於語言的濫用只存在於文宣之中(正如政府曾立例規管地產發展商的新樓盤宣傳品),一切文學創作只停留在腦海的想像文字裡,那麼文學只是甚麼?
然而文學已經展開了行動,以文學的語言,對抗官方或非官方意識形態宣傳,也對抗自身,就像巨噬細胞。由是之故,我們不妨把《沉默發條》裡面的爭論,當成文學起航的入門:我們在這裡,告別政治文宣,告別日常的口誅筆伐,航向文學的國度,航向一種黃金的語言。
* 文章題目及小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沉默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