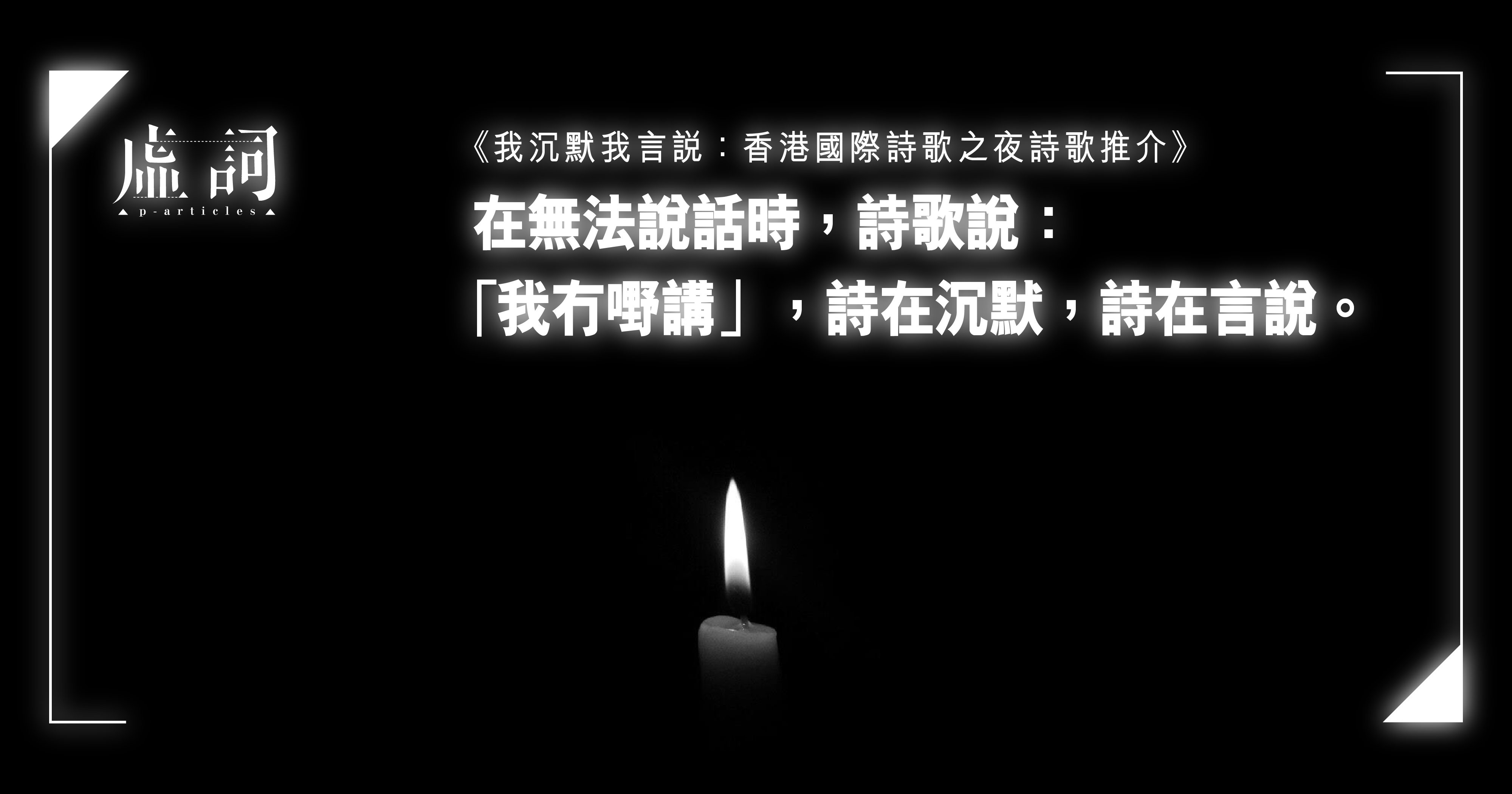我沉默我言說: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詩歌推介
「我冇嘢講」:我沉默,我抗議。在壓迫之地,說話與性命攸關,每一句辯解都有可能成為指控;在懸而未決之處,哲學止步,把握不了無可界定的未知事物,沒有描述真理的說話。最終只能保守最後的權利:我有權保持緘默,緘默成了最沉重的言說,然而在沉默中,在難以言說的痛楚裡,我們需要詩歌。只有在詩意的空間,才能聽見沉默的言說,詩意的語言在曖昧不明之處分明,在延異凝滯之境另辟新徑,在沉寂無聲之中錚錚有聲。在無法說話時,詩歌說:「我冇嘢講」,詩在沉默,詩在言說。
由香港詩歌節基金會主辦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踏入十週年,今年以「言說與沉默」作為主題,於11月19至24日一連6日舉行,參與的國際詩人高達三十位,當中有受政治迫害的、有為女性發聲的、也有以語言作為反抗的詩人。所有的詩歌朗誦會與討論會免費入場,開放予公眾報名參加。在此精選來自六位詩人的六首詩歌,詩歌由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提供,並由香港詩歌節基金會總監宋子江先生推薦,讓我們看看詩歌如何以言說對抗沉默,讓難以言說的生命,併發出一種可能。
一個詞語的失去就意味著一座墳墓——以詩對抗語言的死亡
Abbas Beydhoun 阿巴斯.貝多恩(黎巴嫩)
沉默與血
譯 韓譽
梳過的頭
與無花的花瓶
在從昨天就被打開、棄置的
小玻璃瓶的水裏
只剩下些許生命
黑布
脫不開她的雙肩
在這條脖頸裏
沉默比血更多
我沒有說什麼
別再在我這裏剪指甲了
我忘了耳後的一點肥皂沫
但你,一定
沒有忘記你衣服下的
一根線頭
年輕時曾身陷囹圄,阿巴斯.貝多恩曾經歷多次中東戰爭,因從事黎巴嫩的左翼政治運動而多次坐牢的他,曾多次放棄寫作。逃去法國後,他因為思鄉、被迫流亡等原因而患上抑鬱症,那時的他重拾寫作,以詩歌療傷。現在的他是詩人,也是記者與小說家。
閱讀<沉默與血>,讀者被迫進入一個靜止的空間。「無花的花瓶」早在昨日被打開、棄置,生命無聲死去,死因無人知曉。「在這條脖頸裏 / 沉默比血更多」,是因為死去所以沉默,還是沉默的人如同死去?你、我、她又是誰?阿巴斯曾說自己的詩歌比較沉靜、隱密,詩裡沒有被命名的人,也是為了減少語言裡的噪音——在阿拉伯語中,每一個字都可在可蘭經裡追溯到相對應的意思,所以阿巴斯偏好使用中性的語言和語氣,力求使語言變得純粹。結果是,這種克制營造出一種沉默的氛圍,令詩歌更壓抑與緊繃。
曾有幾次,當戰爭爆發時,阿巴斯停止寫作。他認為戰爭使人的生命變得狹窄渺小,當社會、歷史、文化通通幻滅,人還能抓住甚麼來書寫?完整性的全然瓦解,使語言亦落得同樣下場,阿巴斯認為,除了通過細小、直接的事物以外,我們沒有其他方法形容這個世界。把「指甲、肥皂沫、線頭」等細微之物賦予重量,很大程度是受兩位詩人啟發:法國詩人Pierre Jean Jouve和希臘詩人Yannis Ritsos。當阿巴斯在法國留學的時候,受到很多外國詩人的啟發,前者善於透過物件營造緊張感,如能以瀝青上的一口痰比喻為母親的血;後者則善於把日常瑣碎之物賦予重量,如能把一個鈕扣變成一種內在的、抽象的事物。戰爭三番四次使阿巴斯失去言說的力量,但同時,在絕望中他探索了新的言說方式:即使最細微的物件也能發聲,也有意義,從碎片化的日常中,他以詩歌肯定了生命的重量。
活著就是抵抗——愈禁止愈強大的逆權詩人
Ana Blandiana 安娜.布蘭迪亞娜(羅馬尼亞)
哀歌
譯 高興
獨自艱難,
同他人一起,苦澀,
更新的色彩
在葉子上皸裂,
而從變質的石灰層下
傳來陣陣獰笑,在戰爭爆發之前。
更惡嘴啃著沙子,
更善醞釀著酸楚的詩句,
獨自一人很難,
但同眾人一起更難,
難以沉默,
更難以喊出
一個粉身碎骨的真理。
最要命的是,我害怕並難以
將上帝拽回
天空。
半生以詩逆權,安娜.布蘭迪亞娜是羅馬尼亞文化界傳奇人物,既是詩人,也是人權鬥士,活在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壽西斯古的時代,她的詩作近乎全是禁詩,但她以詩作出抵抗(resist)與反對(oppose),更曾開宗明義地發表「示威詩歌」的類別,愈禁偏偏愈廣傳。
<哀歌>道出逆權詩人的掙扎,詩裡充滿二元對立,惡與善、獨自與他人、沉默與言說。詩人無法沉默,但抓住已然粉碎的真理,結果便是與真理一樣——粉身碎骨,公開批評獨裁者的人,往往要付出代價。安娜的處女作,剛準備發表便被抽起,全國出版社更不得出版她的任何作品,只因當局發現其父正在服勞改刑。一個剛發聲,還未成名的詩人就這樣硬生生被打壓,安娜其後的詩歌之路,也是不斷被禁止、查封,甚至乎一家被國安部人員日夜監視,截查書信和截斷電話綫。一個失去所有溝通、表達渠道的詩人,卻一直「醞釀著酸楚的詩句」,從未放棄寫作。<哀歌>裡並沒有言說任何事件,只是側寫善與惡的抉擇、説與不說的掙扎,這樣更說明了獨裁政權的可怕。
「最要命的是,我害怕並難以 / 將上帝拽回 / 天空。」或許詩人一方面害怕審判,一方面更害怕失去審判、失去唯一的正義,安娜不只寫詩,也身體力行爭取人權。她不但成立羅馬尼亞筆會,也創辦羅馬尼亞無黨派組織公民聯盟,她從沒忘記從此沉默的犧牲者,先後創製了「共產主義受害人紀念碑」與「共產主義和抵抗運動受難者紀念館」。安娜曾說,當她的詩歌被抄寫及傳閱後:「這些詩歌不再只是我個人的示威,而是大家的示威,令我不再孤單。」「獨自艱難 / 同他人一起 / 苦澀」,縱然苦澀,但相信無數羅馬尼亞人,或是在極權下抗爭的人,也通過安娜.布蘭迪亞娜的詩歌,一起承受更難的言說,獲得了與眾人在一起的勇氣。
是地球物理學工程師,也是波蘭地下刊物詩人
Miłosz Biedrzycki 米若什.別德日茨基(波蘭)
你是空間,你是壁虎
譯 茅銀輝
你是空間,你是壁虎
你是一切,除了簡單與平靜
在陽傘下,你遮蔽天空
在半秘密的數字背後,你畫出陰影
用這樣的發明能做什麼?
從一個小球到乒乓球,從高跟鞋呢?
蓋子下面的淙淙聲和沸騰聲
九月的汩汩聲,晨間的爆裂聲,同樣如此
髒了或傷心的時候
我會鑽進外連接地層
在消聲室裏
我會如枯葉般飄落。
與201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朵卡萩一樣,米若什.別德日茨基出生在1960年代,那是波蘭工人飽受壓迫的年代,工人組織工會群起反抗,1980年,地下組織團結工聯組織一系列示威與罷工,而當時只有二十多歲的米若什,則加入了1987年創立的地下刊物bruLion,成為了波蘭bruLion一代最著名的詩人,並常以筆名MLB出版。
比較有趣的是,米若什除了是詩人和翻譯家,更是一位地球物理學工程師。<你是空間,你是壁虎>的背景儼然是一個靜默的實驗室,孤獨的科學家研究著「半秘密的數字」,「蓋子下面的淙淙聲和沸騰聲」讓他更嚮往外面的世界與生命的流動,這個詩人科學家筆下的感官世界,有一種冷靜的憂傷。所謂bruLion一代,其實是比較「寬鬆」的世代,那時波蘭正值政權交替、歷史轉型,在轉向民主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亦同時更新的波蘭下,新的文學聲音油然而生。波蘭語bruLion意解草稿本,象徵著一種未完成、匆匆寫下的狀態,亦即代表詩作走向真實、個人與自由。米若什的詩便經常抒發個人情緒,「這樣的發明能做什麼?」彷彿是對「進步」的疑惑,隱晦地反映社會變革中個人的不安與孤獨。
波蘭bruLion的詩人當中,很多是受到美國詩人弗蘭克.奧哈拉(Frank O'Hara)等美國詩體影響,而喜用即興、口語的寫作手法。米若什也是以口語化的詩歌寫出感受的普遍性,讓人閱讀時更容易代入,「髒了或傷心的時候 / 我會鑽進外連接地層」,略帶玩味的意象下卻是哀傷。這個要躲進地層的詩人,或因專業是探究地球,所以更要書寫微小的個體,如果地球是巨大的「消聲室」,而我們是「枯葉」,那麼「飄落」的時候,米若什選擇的,便是以詩代脆弱生命發出微弱之聲。
像我這樣一個來自非洲的女詩人,是沒有不為女性發聲的權利的
Ijeoma Umebinyuo 苡若瑪.恩梅彬憂(尼日利亞)
委曲求全之道
譯 吳詠彤
你一定要帶你的女兒到教堂去
是魔鬼利用了她來誘惑她的叔叔
是魔鬼附上了她十四歲的身軀。
當她對你說覺得受傷害,
你要因為她曾誘惑男人而責備她,
讓她為自己的身體感到羞恥。
你一定要把她帶到教堂裏讓她得救贖。
到她十七歲的時候
那些男孩進了她的房間而她並沒有在第二天
把這事告訴你,
你的女兒卻把她的傷痛和淚水浸泡成頌詞歌頌他們的惡行。
那天在倫敦某處她坐在沙發上
向著她的治療師尖叫著乞求幫助
而她從來沒有向你提起此事。
到她二十三歲的時候她站著
手上拿著大學畢業文憑
卻沒有笑
在你和叔叔中間,
當他移近她就不安地閃避
你的女兒們坐著把一個又一個回憶道出,
揭開了一連串藏在時光裏的秘密。
她們並不沉默
不像她們的母親
她們捧著自己的心,以愛治療著她們的痛楚。
到你的女兒二十五歲的時候
她致電我
求我把抑鬱帶走。帶走。帶走。
帶走。帶走。帶走。
當你的女兒三十歲你懇求她讓你能做一個
驕傲的母親。
她嫁給了他。
心碎了,肋骨碎了,在兩次小產之後
那天她說「不」
他對她的身體宣示主權,而她由得他。
而她由得他
她由得他﹖
但,請你記得
當你的女兒十四歲的時候你曾求她
你曾求她
要學懂沉默。
‘I know who I am and where I am from. Shrinking myself is not an option.’ 帶著「有色人種」和「女人」的雙重標籤,苡若瑪.恩梅彬自覺必須成為女權主義者,她是當代非洲頂尖新晉詩人之一,一直以詩作為女性發聲。
「當你的女兒十四歲的時候你曾求她 / 你曾求她 / 要學懂沉默」。在非洲,女性被教育成一個沉默的人,<委曲求全之道>裡的女人,由十四歲一直沉默到三十歲。「求我把抑鬱帶走 / 帶走 / 帶走 / 帶走 / 帶走 / 帶走」,反反覆覆的懇求,彷彿是受苦女性獨自一人的痛苦低語。
苡若瑪曾多次在訪問和TEDx演講中,試圖理解與拆解沉默的傳統,苡若瑪認為,沉默的最終得益者只是社會,而沉默是相當危險的事情。事實上,性暴力、抑鬱等在任何性別身上都會發生,她主力寫的是女童與年輕女性,但也寫其他性別,苡若瑪曾說,她的觀眾是任何覺得需要被療癒的人:非洲男女、黑人女人、移民、精神病患者、寂寞的人,她希望在文學裡為他們找回一個位置。「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聲音不重要,那麼我們會漸漸失去為自己敘事的權利。」苡若瑪希望女人能參與政治,能爭取選擇的權利,在國際社交媒體上具極高人氣的她,也一直以自己的聲音,代表更多被迫沉默的人發聲。
苡若瑪.恩梅彬TEDx演講: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yZsPUnPGj0
魔幻怪誕又大情大性——最「貼地」的日本詩人
Yotsumoto Yasuhiro 四元康祐(日本)
影中邂逅
譯 田原、劉沐暘
是在夜晚睡覺前
還是在早晨醒來時
妻子說
「我去見了你母親」
那時我只是簡單應了聲「嗯」
我清楚,二十五年前死去的母親
不可能從那裏趕來見她
一定是妻子去了那裏
橫穿過夢的原野,再走下死亡的山谷
明明膽小卻又莽撞
跟二十五年前第一次見她時一樣
被關門的聲音嚇得跳起來
輕易被太陽的邀請耍弄
獨自一人也能跳舞的她
可是,風停後是死一般的寂靜
閉上眼,從山丘對面
妻子向我走來
她渾身泥濘,臉頰滲血
懷抱著珍奇野獸的沉默
曾出版多本詩集如《大笑的臭蟲》、《午後禁語》,以至近期的作品《前列腺詩歌日記》,從光怪陸離的書名中,不難發現四元康祐是個古靈精怪的詩人。出生於大阪的他,4歲移居廣島,隨即體驗到何謂失語。原來大阪人以喜愛搞笑和健談著稱,但廣島人卻因為原爆的議題,自小被灌輸和平觀念,有著合群的日本傳統個性。初時格格不入的他漸漸學會廣島方言,以致後期移居美國及德國,在不同語言之間穿梭的四元康祐,在某天用英文寫了幾首輕詩後突然覺悟,「語言之間夾雜著詩歌最鮮活原真的一面。」
「對我來說,詩歌本質上是翻譯的行為。從無法說的東西翻譯為可以說的東西。」四元康祐試圖用戲劇化的獨白來寫詩、用別人的聲音來言說,也透過探索一種新形式的抒情詩,以擺脫、公開自己。四元康祐的詩,便常常源於日常生活,<影中邂逅>以和妻子的日常對話引入,從而開始魔幻的、超現實的夢。四元康祐是詩人,同時是個商人,或許如此,他的作品既貼近生活,也帶著詩人獨有的超然氣質。但是,四元康祐卻說:「我討厭詩人被認為是超然物外,孤絕地像享有特權談論美好事物和高尚思想。」如此貼地的他,也有關注最近香港的局勢,並為香港寫下幾首詩,跨越的不只是語言的界限,更是心靈的界限。
戀上香港的敗壞與璀璨,以台灣的眼睛看香港
楊佳嫻 Yang Chia-Hsien(台灣)
守候一張香港來的明信片
一個回歸與出走
均無法被立即決定的年代
熱帶草木依舊蓬勃
耳語如蚊蚋飛翔於大氣
你說,曾在驀然迸開的
煙花中看見:天使墜毀
而歡愉的喊聲剛好蓋過一切
星座是否依舊
沿太古的軌道繞行
意識微涼,當暴雨毫無預警
擊打著書店的窗玻璃
霓虹管是胭脂慢慢溶解
節慶之後,你也許更蕭索了
像半截吸過的煙頭
擱在夢境邊緣,閃爍
時光持續發酵,從鏡中
辨認髮上微微湧出的星霜
夏天街道浮道著酸意
玻璃的稜線起伏
我們各據海角,僅僅能夠得知
新聞標題上彼此城市的輪廓
風向如此猶疑……
你曾許諾的那張明信片
仍未到達。彷彿傍晚的碼頭
一隻鷗鳥凝視水色
你的字跡將對我說些什麼呢
濃霧掩蓋航線,如抵抗一般地
隱約有船引擎隆隆犁開寂靜
喜歡張愛玲,也喜歡也斯,這位與香港一岸之隔的台灣學者、詩人楊佳嫻,喜歡前者在描寫家庭時,在「恐怖中還有溫情與依戀」;喜歡後者筆調裡「悠然的感喟,滄桑的顧視」,或許楊佳嫻喜歡香港,就是喜歡那種敗壞中的璀璨。「煙花」與「墜毀」、「霓虹管」與「溶解」,楊佳嫻在等候明信片到達的時候,竟從想像和記憶裡掌握了香港街道與建築的全貌。在楊佳嫻的散文集《海風野火花》中的「島與半島」,楊佳嫻自述了和一位香港文學學者的戀情,他們在書信之中交換過不少文學話題,想必也交換過「彼此城市的輪廓」。等待,自有一種落寞與浪漫,讓風中既有「猶豫」,街道既有「酸意」。
和也斯的詩歌相反,台灣現代詩的主流,是以高密度為追求,楊佳嫻近年也開始寫一些鬆弛的詩歌,在意象與意象之間給予更寬廣的空間,「疏鬆的詩句,更依賴意義與情懷的灌注」。楊佳嫻在詩作裡提到的「濃霧」、「稜線」、「輪廓」甚至「字跡」,也彷彿是要從朦朧中,試圖拼揍出香港的面貌,讓香港在朦朧之中,能夠被言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