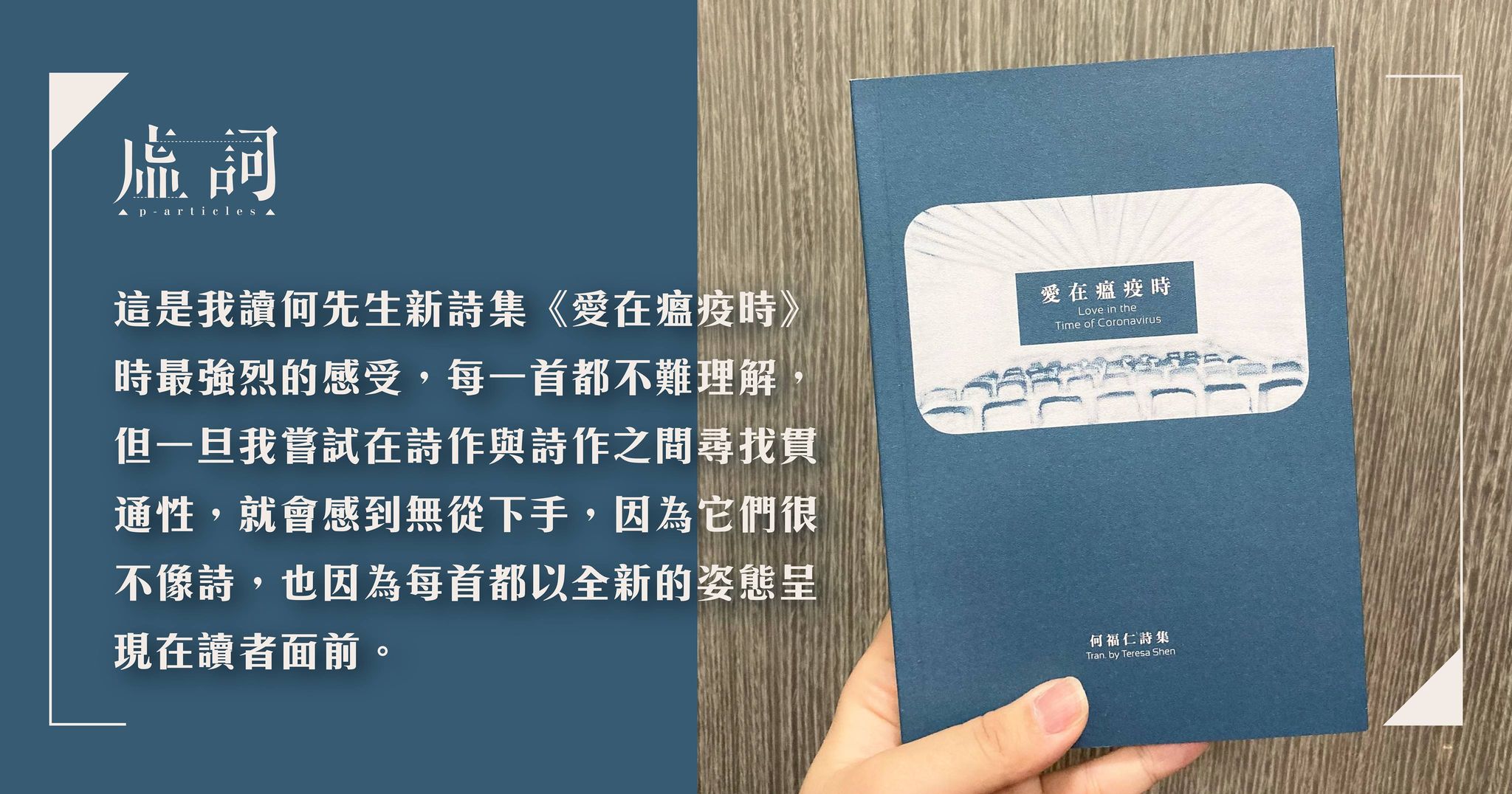瘟疫時代詩歌的逃逸線路——讀何福仁先生《愛在瘟疫時》
「我們一旦扎根在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消失了。」
——G.K.Cheston
(一)
上述引文為英國評論家切斯特頓(G.K.Cheston)的名言,原句是“The moment we are rooted in a place, the place vanishes.”,何福仁先生曾在其散文〈寫詩是一種獨特的自由行〉(註1)徵引此句。該篇散文中,何先生說詩是一處寧靜、可靠之地,寫詩能帶給他歸家的感覺;但同時他也引用切斯特頓的這句話,認為這是一個沒有固定方向、無法確切找到的地方。易言之,詩這個「家」於何先生而言,是一個不斷切換地點、隨處生根,甚至會隨時間而改變形態的地方。
這是我讀何先生新詩集《愛在瘟疫時》時最強烈的感受,每一首都不難理解,但一旦我嘗試在詩作與詩作之間尋找貫通性,就會感到無從下手,因為它們很不像詩,也因為每首都以全新的姿態呈現在讀者面前。起初感覺困惑不已,直到翻開詩集的後記,何先生開篇明義:「大家就當這些詩是一篇長而又長的散文,又或者是綴段式短而又短的小說,只不過都分了行。這些分行的東西,講的是2020一年瘟疫蔓延的故事。所以也不妨當是紀錄」(註2),我才恍然大悟,何先生這是在泯除讀者對詩歌的刻板印象。但他明顯是自謙了,除了文體的泯除之外,詩集中這50首詩還嘗試了各種書寫方法,包括代入病毒的視角(〈搓手戀〉、〈我不見得完全被討厭〉)、代入動物和他人的視角(〈瘟疫與狗〉、〈告訴你,我是因為瘟疫才活過來的〉)、重寫中外文學經典(〈紅樓夢裡的瘟疫〉、〈悠悠我心〉、〈問天〉),甚至是寓言式的書寫(〈王子的故事〉、〈瘟疫與煙民〉)......
在疫情的大背景之下,當許多創作者深感無力,對文學(尤其是詩)的力量產生質疑時,何先生竟在這一年內嘗試各種寫法去表現「瘟疫」這一主題,不限於固定的寫法,對詩歌進行徹底解轄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解轄域化是對轄域化的顛覆,意指對某種等級制中心主義和靜止時空的解放。就像他在後記所言,在這個時代若要以詩的形式表現時代現狀,不但要摒棄春風秋月的詩意、摒棄法國人的「純詩」觀念,還要藉助散文、小說、戲劇,以至一切有效的形式(註3),顛覆讀者對詩的固有印象。另外,何先生這本詩集沒有分輯,詩末亦沒有註明寫作日期,他解釋「是隨著疫情的發展而寫,也照這樣編排次序」(註4),在我看來,他似乎想以「瘟疫」為大主題,讓文字在筆下任意生成(becoming)各種形態的果實。承何先生所用的比喻,若將寫詩喻為歸家,那麼寫詩方法的豐富多樣,無疑為他開拓出更多歸家的路徑。
(二)
上文所述,無論是「解轄域化」、「生成」、隨處生根的狀態,還是將寫作比作思想層面和語言層面的「逃離路徑」,都讓筆者想到了德勒茲塊莖(Rhizome)理論。「塊莖」是德勒茲著作《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的最重要美學概念,意指「一切事物變動不居的複雜性」(註5)。學者麥永雄則在《德勒茲哲性詩學:跨語境理論意義》一書中解釋:「『塊莖』(如藤和草之莖)的生態學特徵是無中心、無規則、多元化的形態,它們斜逸橫出,變化莫測。」(註6),這與柏拉圖以降主導的西方傳統的、具中心論、規範化和等級制特徵的「樹狀」思維截然不同。因此,「塊莖」的特徵之一是「多元性原則」(principle of multiplicity)。塊莖圖式的多元性與傳統樹狀模式、簇根模式的偽多元性不同,是一種對二元對立模式的徹底消解。
何先生的詩觀明顯不存在僵化的二元對立模式,「詩」與「非詩」之間沒有明確的分界,他甚至鼓勵詩人要主動打破固有的隔閡,在疆域之外尋求養分,正如他在後記寫道:「詩的國度,不容其他作家入境,詩人卻可以也必須出境周遊,打開視野。簡言之,必須打破文類的界限。面對疫情,要不斷洗手,但文類的潔癖則不可有,一無束縛,要怎樣寫就怎樣寫。(註7)」在李浩榮的〈訪何福仁談《孔林裡的駐校青蛙》〉中,何先生還舉中國古代各朝詩體的更迭,說明詩體的掙扎和革新是「正確而必須」(註8),再次暗示了「詩」與「非詩」之間不應有明確的界限,「(詩)可以伸向小說、戲劇,扮演角色……」(註9)。在這種創作觀之下所生成的文學作品,無疑更適合表現當下的社會局面。
在德勒茲的理論中,「塊莖」會不停歇地「在符號鏈、權力的組構,與關涉藝術、科學、社會鬥爭的環境建立聯繫」(註10),在碰撞的過程中把語言拽出慣常的路徑,開始新的「發狂」(delirious)。而我們當下所處的社會正是一個多元雜燴,充滿複雜權力關係的處境,單一的寫作手法顯然難以全面表現社會原貌。時下亦十分像是德勒茲在與加塔利合著的《卡夫卡:為少數文學而作》中所提到卡夫卡的寫作與其時代的關係:卡夫卡作品對已轄域化的主流語言的顛覆是革命性的,而這正因為卡夫卡的時代處於奧匈帝國和哈布斯堡王朝崩潰,「是有一個解轄域的歷史、語言、文化過程」(註11),近年來香港無論是政治局勢、官民關係,還是大眾的生存狀態,都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因此用更多元的方式進行創作,更適合表現當下的社會局面。
(三)
《愛在瘟疫時》十分重要的一點在於對人與物的解轄域化。在人們固有的思維模式中,人與物之間存在著明確的邊界,哲學家不斷地定義「人」以便將人與物更清楚地進行劃分。康德(Immanuel Kant)則是一例,他從認識、情感和意識三個方面來區分人與動物,以此確立人的特殊位置。在這種思維模式下,「我們傾向於假設某種關於體驗的正典或標準的體驗模式,例如人類生命的模式,而不得不忽略非人類的體驗(如動植物、非有機體的體驗,甚或那些我們至今尚無法形象描繪的未來體驗)」(註12)。但德勒茲主張以多元視角對人類中心主義進行解轄域化,這也正是德勒茲欣賞卡夫卡的原因,「卡夫卡創作的故事中把生命想象為甲蟲、洞穴動物或機器。由此,我們可以從一種非人類的視角想象生活。(註13)」《愛在瘟疫時》裡人與物的界限亦被徹底消解,二者不再是二元對立的模式,彼此的可能性因此得到解放。
為達到這個效果,何先生所用的方法,便是視角的混雜,以物的視角寫人類的事情,從人類與非人類雜交而成的「生成物種」的視角想象生活。例如〈搓手戀〉一詩,全詩以酒精搓手液作為敘事視角,詩中的「免於毒素」、「奇貨可居」、「清洗歹毒」、「化為青煙」都是酒精搓手液的特徵,但「出身良好」、「騙賣」、「轉借奸商圖利」、「上京」、「一朝高中」、「贖身」等又是風塵女子的視角,因此交融生成了一種雜燴了酒精搓手液和風塵女子的特徵的獨特視角,儼然一則風流佳話,這種浪漫且略帶俏皮的想象無疑消解了疫難的沉重感,讀者讀到此處不禁莞爾。另一首〈生命就是這樣〉(註14)亦是用同樣的手法,將人與植物的視角相融合,「探出頭來」、「掙開泥土」、「沾一些雨露」等雖是植物的特徵,但整首詩卻將植物人格化為「你」,結尾還以對白作結,似是敘事者與植物之間的一場對話,人與植物交融生成了一種即使身處逆境也要樂觀生活的獨特視角,並藉植物之口說出「只需要耐心/堅持;陽光會撒下金黃/再沾一些雨露/總可以活下來/活著就有希望」,鼓勵疫難之中惶惶不安的人類耐心抗疫,莫失希望。
(四)
《愛在瘟疫時》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何先生在這本詩集中似乎將瘟疫當作可以隨意和其他事物進行裝配的機器(Machine)。在德勒茲的理論中,「機器的概念否定了基要主義的超驗上帝和主體觀念或評判標準,意味著事件的不斷連接與生成的不斷更新……以自行車為例,它本身顯然沒有一成不變的目的或意圖。只有當它與其他機器(例如人類的身體)聯繫起來時,才能得到定位和發揮功用。(註15)」簡而言之,事物的意圖不在其自身,而在於該事物與其他事物產生聯繫時所得到的定位和發揮的功用。事物即符號,充滿偶然性,符號本身並沒有永恆不變的價值。因此,羅貴祥在《德勒茲》一書中亦借用索緒爾語言學的觀點說明在探討語言(或其他事物)的意義時,固然不應完全忽視其「歷時性」(diachronic)的意義,但更應以結構主義的視角探究其「共時性」(synchronic)的意義。
雖然這本詩集以「愛在瘟疫時」為名,詩集中有七首「瘟疫與XX」顯得十分亮眼,這七首詩的主角都不是瘟疫,反而是XX(XX有時是貓、有時是狗、有時是老闆、有時是南北國)。何先生將「瘟疫」安置於不同的語境之下,讓瘟疫與其他的事物產生聯繫,似乎在暗示,瘟疫本身並沒有封閉性的身份,沒有一成不變的目的和意圖,只有當它和其他事物產生聯繫的時候,才會有所謂的褒貶。因此他嘲諷和揶揄的對象並非瘟疫,反而是XX。例如〈瘟疫與將軍〉(註16)以寓言式的故事諷刺了一名為了樹功而用飛彈攻打病毒,全然不理民眾安危的將軍,諷刺在位者不以民為本的作風;〈瘟疫與煙民〉(註17)諷刺了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詩中以「世衛那個埃塞俄比亞的頭頭」代稱)對疫情和研究成果的刻意隱瞞;〈瘟疫與偵探〉(註18)以勸誡的口吻阻止偵探找出事件的真相,以免惹禍上身,諷刺追尋真相者往往會遭到報復。諸如此類。這同時也在暗示,瘟疫本身並無分好壞,只因跟不同的他者產生鏈接才有不同的定位。因此通讀全集,不難發現何先生在描寫瘟疫的時候往往用俏皮可愛的口吻,反而將諷刺的重心聚焦於複雜的人間世相,正如詩集後記所說,破壞人與自然之間的諧協的,往往是人類自己(註19)。
(五)
德勒茲在《差異與重複》中創造了「差異」這一概念,顛覆尼采「永劫回歸」的論調,認為即使世事在不停地重複,也不會有兩個完全一樣的事物。那些被稱為複製物的,也是新的事物。羅貴祥指出,「歷史的運動不是受超越性的定律(transcendental principle)所支配的,而是交織成一塊『內在性的平面』(plane of immmanence)……在歷史這個內在性平面上,只有事件的個體性,沒有統一或整體性;只有『這裡』(haecceities)的此時此刻的絕對性。(註20)」
因此重複的存有過程(becoming)和差異便可視為歷史事件的兩個組成成分。這兩個成分在何先生的詩集中得到同等的重視。他在後記中說新冠肺炎的故事至今尚未煞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放眼歷史,人類卻一直和病毒結緣,此乃「重複」。但看似不斷重複的瘟疫,又有其絕對的獨特性,「人類在不同的時間空間替它起過不同的名字:黑死病、天花、瘧疾、梅毒、黃疸、肺結核……,目前肆虐全球的則叫新冠肺炎。(註21)」此乃「差異」。因此,何先生希望能夠做到「既寫實,又寫意」,既記錄事件的細節,又準確把握背後生成事件的動因,更全面地還原歷史。
詩集中不少作品都會直接使用具體事件的真實涉事者、事件發生的時間,以及相關的意象;但何先生又不止步於對具體事件差異的強調,他嘗試在具體的事件中抽出它在歷史長河中重複的部分,亦即作者所言的「寫意」。例如〈加拿大來郵〉(註22)一詩,詩的內容是敘事者的哥哥寄來的一封信,信中哥哥讓弟弟不必再寄口罩過去,因為在加拿大,戴口罩的人會被視為不健康。這首詩的表層意思不難理解,講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外不少地區的人都自恃身強體壯無懼病毒,不但自己不戴口罩,反而視戴口罩著為異類,這是此次疫情較獨特的現象,是為對事件之「差異」的把握。但何先生並非止步於對現實的記錄,他隨後的「詭異的東西,往往不露徵象」極為精煉地概括了世間之事,大大升華了整首詩的意義,結尾的「我一直想一如其他人那樣生活/我最害怕敵意的眼光」更是道出了所有異鄉客的心聲,正是因為人們對異鄉人的敵意和不友善,才會導致這種歧視的出現。此即對事件之「重複」的總結。
(六)
至今尚未消停的新冠肺炎對世界造成極大的影響,同時也為文藝界的寫作帶來了新的書寫困局——疫難當頭,寫作的力量似乎微乎其微,甚至不知應如何找到適切的入口去書寫這一主題。何福仁先生的這本《愛在瘟疫時》幾乎可以作為「現代詩教學的參考書」(註23),詩集中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書寫方法,並且有意識地打破文體與文體之間的界限、泯除讀者對詩歌的固有印象、主動為人與物解轄域化、讓所書寫的主要對象(瘟疫)與更多他者產生聯繫、更好地掌握當下發生的事件的「差異」和「重複」,在詩歌寫作的路上探索更多的逃逸路線。但何福仁先生這本新詩集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本文限於篇幅,不得不在此停筆,權當拋磚引玉,望能引出更多方家的討論。
註:
1. 何福仁:〈寫詩是一種獨特的自由行〉,《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5),頁232。
2. 何福仁:〈寫在瘟疫蔓延時〉,《愛在瘟疫時》(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15
3. 同註2。
4. 同註2。
5. Neil Spiller ed.,Cyber-Reader : Critical Writings for the Digital Era, London : Phaidon, 2002, p.97.
6. 麥永雄:《德勒茲哲性詩學:跨語境理論意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頁46。
7. 同註2,頁154。
8. 原文:「從四言、五言,到七言,唐詩宋詞元曲,一直在發展、改變形式,你可以說這是審美內容的推動,其實也是詩體的掙扎求存。到了五四,新詩徹底打破形式的束縛,是正確而必須。」節錄自李浩榮:〈訪何福仁談《孔林裡的駐校青蛙》〉,《愛在瘟疫時》(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166。
9. 李浩榮:〈訪何福仁談《孔林裡的駐校青蛙》〉,《愛在瘟疫時》(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167。
10. Deleuze and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492.
11. 同註5。
12. 同註5,頁76。
13. Cf. Claire Colebrook, Gilles Deleuze, New York: Routledge, London, 2002, pp.125-128.
14. 何福仁:《愛在瘟疫時》(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21),頁151,頁99-101。
15. 同註5,頁74。
16. 同註14,38-40。
17. 同註14,頁41-42。
18. 同註14,頁54-56。
19. 同註14,頁152。
20. 羅貴祥:《德勒茲》(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頁143-144。
21. 同註14,頁152。
22. 同註14,頁33-35。
23. 阮文略:〈疫下三千世間相的見證之詩——讀何福仁《愛在瘟疫時》〉,第四十一期《別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