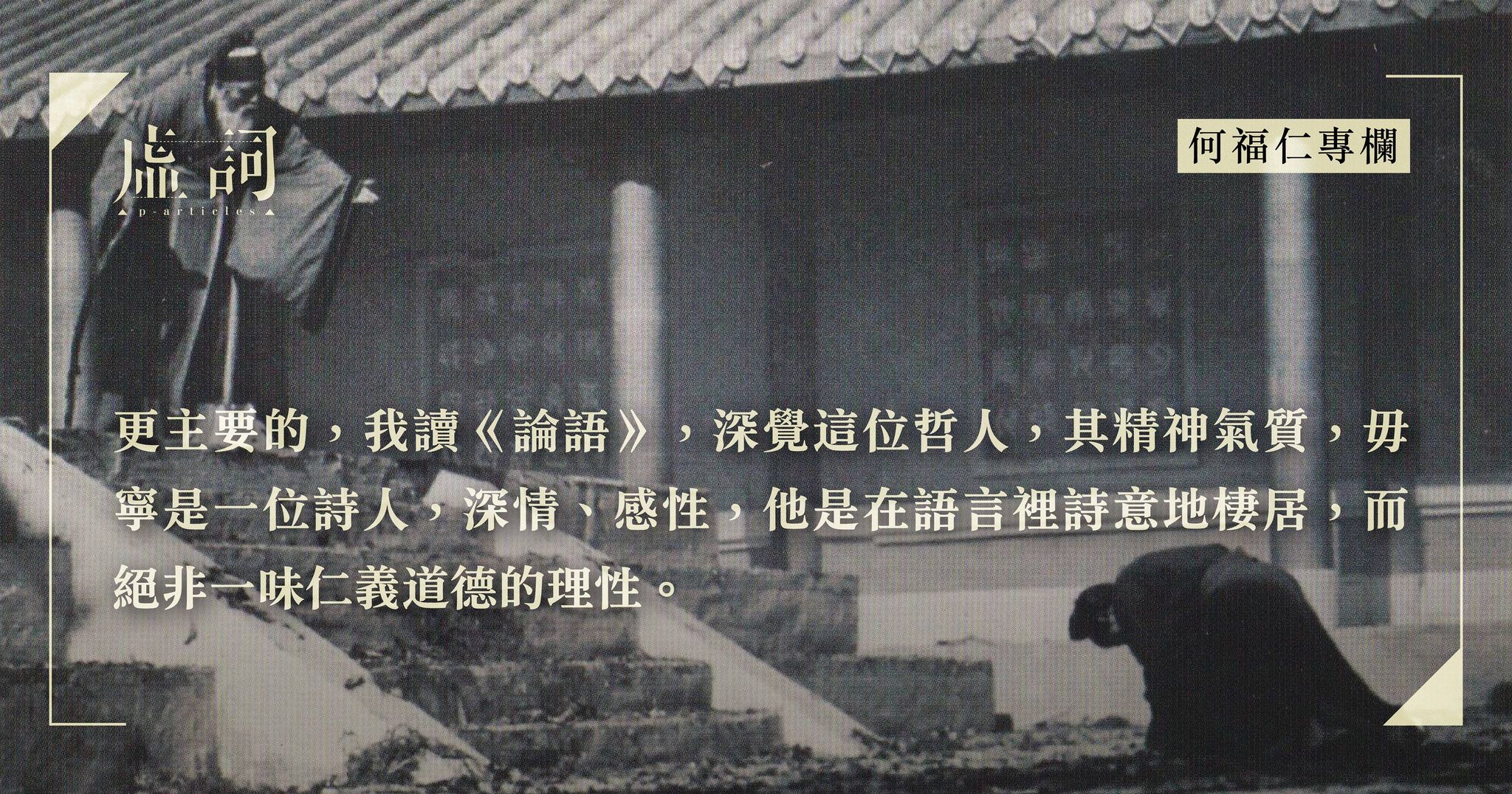【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孔子與詩
1
這題目是「孔子與詩」,不是「孔子與《詩經》」,孔子與《詩經》的討論、研究,歷來多得不得了,到了今世,由於竹簡的發現,例如《孔子詩論》、《民之父母》等,仍然論之不盡,時有歧見、新見。單是上博竹簡《孔子詩論》,因為出土時散亂破損,且是秦統一文字之前的書寫,到底論詩的人是孔子抑孔子學生卜商(子夏),也有過不同的意見,最後大家都接受孔子。至於竹簡的排序,更不得了,整理者馬承源是一個排法,李學勤、李零又是另外兩個排法。不過這種討論很有意思,沒有一個霸權可以說了算。
這方面不是我所能置喙。但孔子與詩,我還沒有讀到,我的問題是:孔子寫詩嗎?多年來我一直想著這問題,不是因為我好歹也是個二千多年後寫詩的後後輩,而是想到他是最早的詩集整理者,不止選了就算,還調正音樂,那時代的詩,都合樂,以樂為主,是名實相副的詩歌。今人動輒也稱新詩或者現代詩為詩歌,其實並不恰當,一來並不以歌為主;二來,除非後來配樂,根本無歌。孔子時代,以至整個漢語詩史,唐詩宋詞元曲,大多合樂,直到胡適的嘗試,才與歌正式離分,過去那許多年的詩有一個很好的名字:「歌詩」。
更主要的,我讀《論語》,深覺這位哲人,其精神氣質,毋寧是一位詩人,深情、感性,他是在語言裡詩意地棲居,而絕非一味仁義道德的理性。這感性的一面,才可見他不是可厭而至可怕的老頭。這麼一個人,一生與詩為伍,在二次創作《春秋》之前,我想,不可能不寫詩。
但談孔子與詩之前,還不得不先釐清他與《詩經》的關係。孔子時代的《詩》,還沒成「經」,到了西漢,《詩》才尊奉為《詩經》。同為戰國中後期的郭店竹簡《六德》,講六德(聖、智、仁、義、忠、信) ,與六位(父、夫、子、君、臣、婦)對應,六者需各行其職,再而指出要觀諸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物雖無經之名,卻已成型,並有權威之實。其中提到「為父絕君,不為君絕父。」誠為思孟學派一脈。當然,《詩》的經典化,仍需經過儒家多年的經營,不斷徵引、解釋、傳承,而推動最力,影響也最大的,當然是祖師孔子。
孔子以《詩》作為教科書,教後生小子,認為整個完人教育,由《詩》開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8.8) 在《論語》中,他談到詩的地方很多,最著名的是指出詩的各種功能:「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17.9) 這個詩,可以是泛稱,也可以是專指。學詩,既可抒發情志,興觀群怨,更通達政事:「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13.5) 這所以,孔子對兒子孔鯉說:「不學《詩》,無以言。」(〈季氏〉16.13) 無以言,是指大如外交場合,小如社交活動,都不會應對。倘加上《左傳》、《孔子家語》,《國語》等等,那麼他談詩、評詩、引詩,以詩解詩,在先秦人物裡,比其他各家都多。
其後的子思孟子當然同樣談詩引詩。至於其他各派,也說詩,卻未必出於善意。墨子生於春秋末戰國初,引《詩》11次,說《詩》4次(鄭傑文:《墨家的傳〈詩〉版本與〈詩〉學觀念》) ,是較多的了,但大罵孔某「大姦」、「賊天下人」,「弦歌鼓舞以聚徒」(《墨子‧非儒》);又把《詩》三百分拆為誦、弦、歌、舞,質疑孔子主張厚葬之久:
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公孟)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 (《墨子‧公孟》)
他說要是以為孔子可以做天子,那等於點算別人的契刻,就當是可以成為富人:
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為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為富。
法家大家商鞅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 ,以為《詩》是六大害蟲之一,一如柏拉圖那樣,要逐出他的理想國。中西這兩位「英雄」,生於同一時期,所見略同。
不過論批評用詞尖刻,且恰如粵語所云「抵死」(這是粵俗的妙語,不知如何翻譯,字面是deserve to die),還是《莊子‧外物》:「儒以《詩》《禮》發冢。」發冢,即盜墓,儒者是盜墓賊。莊子是戰國時代人,只是〈外物〉多不以為是莊子之作,這麼說不過是為《詩》《書》澆上最後一堆土。
荀子是戰國末的儒學大家,當時《詩》《書》已非時尚。他引《詩》多達80次,旨在佐證自己的論說,到頭來卻為了「隆禮義」而主張「殺《詩》《書》」,下開了法家李斯焚《詩》《書》的做法。
2
孔子出生時,《詩》已出土近一百七十年,從此不死,稍稍恬退,然後一直為祟。何以見得?因為在《左傳》中所見,春秋時代的權貴在典禮、宴飲、交際時,經常用《詩》,即使有不同的理解。至於如何運用,只有儒者堅持仍需合乎禮制,不可亂用。司馬遷說孔子刪詩,從三千刪減為三百,令人難以置信,因逸詩畢竟不多,《左傳》中所記有詩題或只有詩句,只十五例。但他自己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罕〉9.15) 樂不正,則不能去到該去的地方。他指的是《雅》、《頌》,都是權貴士大夫之作,著眼就是政治教化。
孔子沒提《風》。《論語》中他談到的是「鄭聲」: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15.11)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也。」(〈陽貨〉17.18)
孔子厭惡「鄭聲」,要對付佞人那樣,把它「放遠」。但這鄭聲是順韶舞之樂而說的,是指鄭地流行的音樂,與國風中的鄭詩有別。《禮記‧樂記》中子夏說:「鄭音,好濫淫志。……是以祭祀弗用也。」淫是過濫之謂,孔子認為會擾亂中正平和的雅樂。他既然曾整理《詩》,詩三百,包括鄭詩十五首在內。這也證明他說的是激動人心的鄭聲,「淫」與「邪」有別。之前吳國公子季札聽過鄭聲,說「美哉」,但認為是亡國之音。鄭詩多是愛情詩,愛得瘋狂也甚少至於國亡家破吧。
漢人有行人到民間採詩之說,再經樂工加工,以便君主體察民情云云,與其說這是記實,毋寧是讀書人對君主迂迴的記望。不過朱熹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詩集傳‧序》) ,則南宋以後,奉為確論,胡適等人都接受了。顧頡剛接受之餘,另外提出民間歌謠無取乎往復重沓,而〈風〉詩,因奏樂的關係,往往反復重沓好幾遍,於是「可以假定其中的一章是原來的歌謠,其他數章是樂師申述的樂章。」(《從〈詩經〉中整理出歌謠的意見》)
從〈風〉詩的內容看,確合乎朱子所言,但從形式看,則是另一回事。楊牧(王靖獻)早年的博士論文《鐘與鼓》(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 將西方套語理論引入《詩經》研究(其中對「興」的性質尤多創見),認為是口頭向書寫的過渡,以至措辭(雅言)、用韻,語助詞、代詞、稱謂、衣飾等等檢視,顯然不止是樂師擴充庶人的民歌。從黃河流域,到江漢流域,各地的〈風〉詩,竟並無不同。近人朱東潤、屈萬里等人已指出根本就是貴族士大夫之作。
孔子綜論《詩》三百篇,一言蔽之,云:「思無邪」(〈為政〉2.2),楊伯峻譯為「思想純正」。從政教的角度講,那就是「政治正確」。當代詩經學把《詩》還原為文學作品,「還原」云,先秦人自有文學藝術的感性,可是學詩用詩,主要還是當政教的工具。不過孔子還不至於那麼狹隘。反而程頤的解釋穩妥得多:「思無邪者,誠也。」誠,也是《中庸》的關鍵詞。《論語》中,孔子也曾引逸詩: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子罕〉9.31)
詩人說:唐棣開花了哦,翩翩翻舞;我怎能不思念你呢,只是我住得太遠。但孔子一語揭破他邪而不誠:「不是真的思念,真的思念,再遠又有什麽關係!」無論求的是賢人,是情人,都不能作虛弄假,都不能不誠。所謂「修辭立其誠」,這合乎「思無邪」之旨。
3
先秦人用《詩》,用法有三:賦詩、歌詩、引詩。三者有別。
賦詩,賦這動詞有兩義:
一、外交活動、享宴時,諸侯士大夫借《詩》代言,以表達自己的想法。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漢書‧藝文志》) ,選了詩句,可由樂工朗誦,但不需樂伴。有借有還,必須雙方懂《詩》才行。
二、指寫作,例如《左傳‧閔公二年》:「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為之賦《清人》」。《載馳》見《詩經‧鄘風》;《清人》見〈鄭風〉。前者是一位女性。過去李辰冬曾認為這五百年的詩集俱為尹吉甫一人所作,直是宇宙間第一詩人,難怪他在〈六月〉中自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賦另指寫作,見司馬遷云:「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報任少卿書》)、蘇軾形容曹操「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赤壁賦》)然則今人的詩會,寫詩的人朗誦詩作,可稱為「賦詩」。
歌詩,則肯定要樂工奏樂唱出。
至於引詩,陳來引楊向時在《〈左傳〉賦詩引詩考》的分析,有六類:
1. 斷章取義;
2. 摭句證言;
3. 先引以發其下;
4. 後引以承其上;
5. 意解以申其意;
6. 合引以貫其義。
《左傳》賦詩引詩,有學者統計,凡256條。不過陳來在《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的注釋引張素卿云:時人引詩,始自恒公六年。不過翻開《左傳》,啓首隱公元年,即有《詩經》名句「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
這些,都是先秦時代,貴族權貴明玩的遊戲、暗中的過招,不懂政治的庶民確乎「無以言」。賦詩引詩,襄公時期最盛,那是孔丘成長的時期,可見那還是詩禮之世,當他說「無以言」,是有這樣的時代背景。但不可不知,襄公之後,《詩》的狂瀾日退。西周晚期新貴抬頭,肯讀書而懂詩的不多,接著昭公、定公、以及哀公,已絕少引用。這才是真正的禮壞樂崩,到了戰國,名嘴縱橫,更無一再借助《詩》。
賦詩引詩歌詩,背後不可不誠,名嘴自然沒有興趣。還是那位再三讓國的吳國公子季札灑脫,有遠見,深明亂世政治的恐怖。公元前544年,季札應聘訪魯,那是還能保持周初禮樂之地。魯的接待極盛情,樂工為他演奏,他大概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可以在魯地聽了一場歌詩舞的音樂會。那時,根據司馬遷的〈孔子世家〉,我們的孔丘才七歲。他後來在齊,聽了《韶》樂,已經樂極而三月不知肉味(〈述而〉7.14)。季札呢,飽嚐了一席專為他而設的《詩經》。學者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演奏曲目的次序,認為符合通行的《毛詩》,於是看到這時候的詩確已成形云云。我則想到這位掛劍送亡友,隱世躬耕的貴公子,真太有意思,那是一場空前絕後的音樂會,絕對不是偏聽的政客能有的耳福。我把《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全文引出,以目代耳,加一點想像,庶幾或可分享一二: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穆子)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
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其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見舞〈象簫〉、〈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
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見舞〈韶簫〉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樂工不是對牛彈琴,因為明知他是知詩知音的大家,聽了看了,就馬上做文化的樂評。孔穎達疏云:「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為之節也。」(《毛詩正義》) 他的評語可不是一味頌讚,也點出不足、缺憾。他聽過鄭聲,說「美哉…..」。這場音樂會一定很悠長,奏的唱的舞的一定很累,欣賞者凝神觀賞,不停喝彩,何嘗不累?因此說,夠了好了,再有,也不敢不請停止了。
如果孔子寫詩,會是怎麼個樣子?(2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