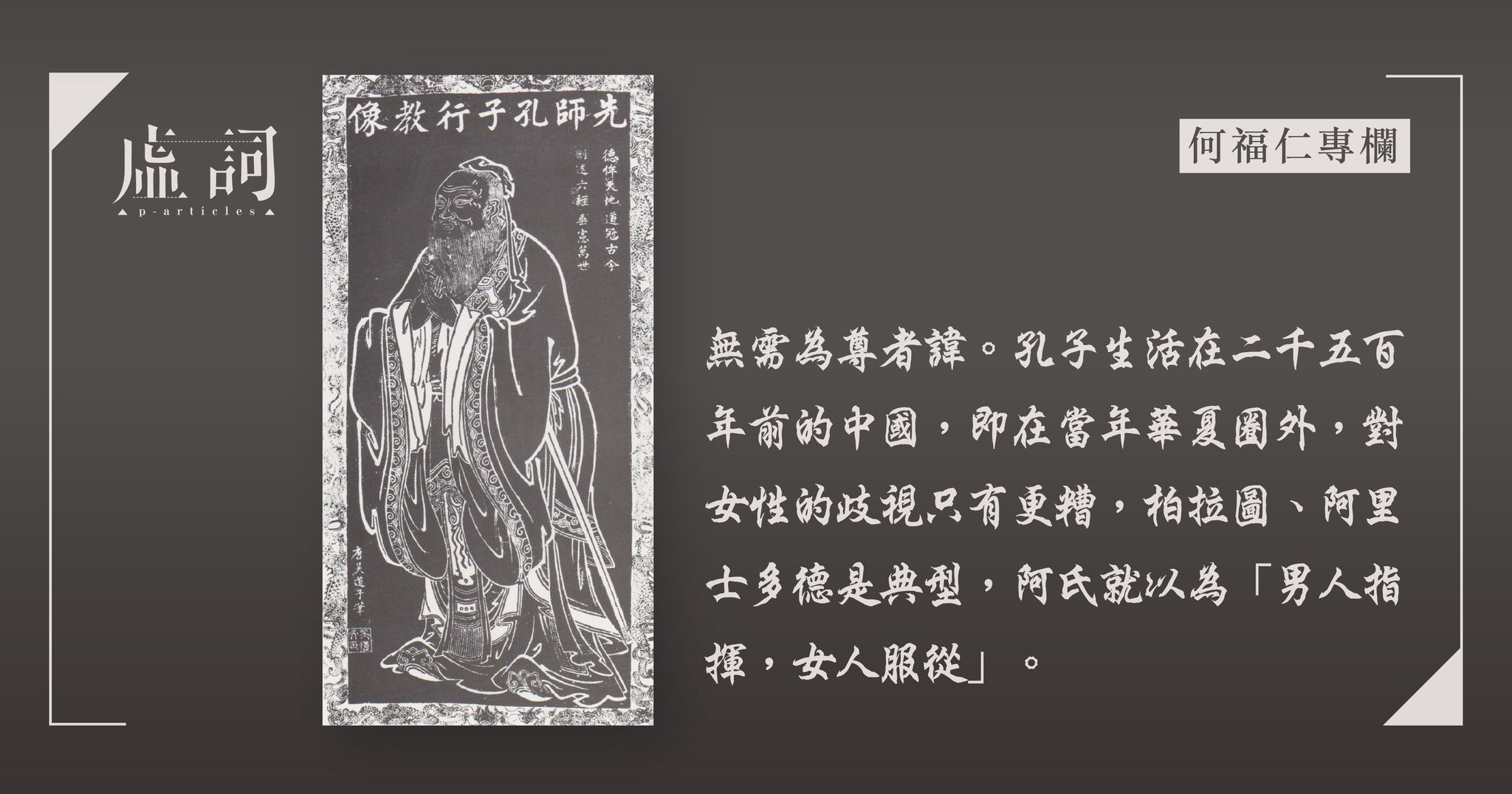【何福仁專欄:時宜篇】孔子與女子
孔子是厭女、仇女,以至是今人所謂「仇女主義者」(misogynist)?《論語》裡有一句:「唯女人與小人為難養也。」〈陽貨〉(17.25)這麼一句,把女人和小人並列,歸於「難養」,倘在當代,真夠令一個有點名望的男士聲名狼藉的。
無需為尊者諱。孔子生活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即在當年華夏圈外,對女性的歧視只有更糟,柏拉圖、阿里士多德是典型,阿氏就以為「男人指揮,女人服從」。古希臘之後,名流盧梭、叔本華、尼采等,都相當「厭女」,尼采粗暴地向男士提示:「到女人那裡去,別忘了帶上鞭子!」「仇女」,是流行疾病,可沒有什麼人認為真的是病。吾國一向有「紅顏禍水」之說,名單甚長,西方最著名的紅顏是特洛伊的海倫,天才詩人馬羅問:
Was this the face that launch'd a thousand ships,
And burnt the topless towers of Ilium?
是這張臉曾使千帆並舉,
把伊利安高聳的城樓燒成灰燼?
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學大師馬基雅維利有一本書:《論李維》(Discourses on Livy),分析羅馬共和政體,在第三冊第二十六章,說到女性對政制的「貢獻」極大,題目很清楚:〈國家如何因女性而敗亡〉(How a State is ruined because of women) 。宗教方面不必多說,更不必提當今的塔利班。
香港算是相當尊重女性,不少女性居於領導地位,但風光的背後,許多工種,仍然男女同工不同酬。據港府統計處最近發表的《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2019 年10月至12月),統計了不同界別的收入,中位數差額竟達5000港幣。
上述這些,是想勿對孔子之說大驚小怪。而且,上述對女性的歧視是一概而論,孔子之言,則肯定並非泛指。下文再解釋。其實《論語》裡還有一句,見於〈泰伯〉(8.20),孔子稱頌舜帝、周武王,這兩君都有賢君輔政,這一節先引武王的話,說自己有賢臣十人,然後孔子這樣回應: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他說人才難得,不是嗎?唐堯和虞舜之際,以及周初武王那個時候,人才興盛。然後忽爾來了這麼一句:「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這話很奇怪,好像是所謂十賢實為九賢而已,因為其中有一婦人。要是這樣理解,那麼孔子是把婦人排出了賢人、才人之列。不過倘把「九人而已」四字刪去,卻是對婦人的稱讚。本意是說人才的難得,九賢還要加上一個婦人,才湊足十位,說是才難,卻予人「女子難得成為人才」之嫌。抄一些語譯如下:
楊伯峻:「然而武王的十位人才之中還有一位婦女,實際上只是九位罷了。」錢穆:「唐虞之際下及周初算是盛了,但其中還有一婦人,則只九人而已。」李澤厚:「十人之中,還有婦女,所以只算九人。」
老實說,也拿不準孔子這話的意思。而且,通篇〈泰伯〉,俱稱「子曰」,單獨這一句,逕稱「孔子曰」。是後人添加的嗎?
武王的九賢如周公旦、召公奭、姜太公等等,另一位遺珠的「婦人」是誰?邑姜。史書會說她是武王的王后、姜太公的女兒、周成王、唐叔虞的母親。這樣的身份,好像她不是她自己。山西太原的晉祠,即供奉邑姜和唐叔虞母子。
周武王是個成功的男人,他有九賢治外,有賢內助治內。男主外女主內,主次之分,是注定的嗎?人類之初的母系社會,是母同主內外。多年前我到過安陽殷墟的婦好墓,走進墓地,渺無其他人,墓地出土不少甲骨文,據專家解讀,發覺她不單主持祭祠大典,是宗教領袖,更是軍隊主帥,曾帶兵一萬三千多人出外打仗,那是殷商的一半軍力,可見深得武丁信任,立下赫赫戰功。舊時典籍記商朝武丁時代的賢臣,總是甘盤和傅說,不知還有婦好一人。
別怪孔子也不知道。
2
但眾所周知,《論語》所載孔子的話語並沒有上文下理的語境,編排並非編年順序。「唯女子與小人」之句,下文是「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孔子是什麼時候說的,何以這樣說,並無確證,只能推敲。朱熹解「小人」為「僕隸下人」,「女子」為「臣妾」;明人林希元謂「女子,婢妾也」。康有為不乏奇怪的創意,把女子改為「豎子」,解釋云:「女子本義作豎子」。「養」,大多指「待」。
這兩種人,親近了,則熟不講禮;疏遠了,就會埋怨。
孔子和女子的瓜葛,《論語》所見,有兩事:一、因齊人送女樂給魯,季氏收了,耽於玩樂,疏於政務,孔子見已無可為,於是離開祖國,開始十四年的流亡。當時是魯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 ,見〈微子〉(18.4) :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之去,是當時在魯做司寇,頗有政績,齊與魯相鄰,恐怕魯真的讓孔子當政,強大起來,一定稱霸,齊就危了。原先想割一些地給魯,搞好關係。但大夫黎鉏提議,先搞破壞,破壞不成才送地吧。於是送了八十個能歌擅舞的美女給魯,還有駿馬三十匹(魯定公也是馬迷) 。當權的季桓子收了,三日不聽政。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史遷不免加鹽加醋,加上見祭天的祭肉沒有按禮分送給大夫。
其二是南子事件。
孔子去國,其中一站是衛國。南子是衛靈公夫人,既把持朝政,又傳與他人有染,名聲很不好。《左傳‧定公十四年》記載,大子蒯聵聽到野外之人傳歌,稱她為「婁豬」(母豬),甚覺受辱,想謀害她,但事敗,只好出奔。衞靈公死後,南子立蒯聵之子,是為衛出公。後來蒯聵發動兵變,自立為衛後莊公(以別於前莊公),殺南子。
《史記》寫孔子與南子會面很仔細:孔子當時寄住蘧伯玉家。南子使人召見孔子,云:四方君子與國君稱兄道弟的,一定來見我們的夫人。孔子辭謝不得,只好去見。南子坐在紗幕後面,孔子入門,向北面叩頭。夫人自帷中再拜,她的各種佩戴環叮噹有聲。再沒有下文。
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滿。孔子表示這是為了禮貌的答謝,發誓表示自己清白。一月後,衛靈公與南子同車,有宦官同車侍候,招搖過市,反而使孔子坐在後面的車子。孔子感到屈辱,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離衛。
相關事件,《論語‧雍也》(6.28) 只有簡約記述: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至於「好色者」一句,在《論語‧子罕》(9.18)、《論語‧衛靈公》(15.13)裡重出,其實並未明確指的是誰;在《史記》裡,指的卻是衛靈公,不是南子。我們看兩子之會,──對不起,我們只能看到《史記》的記載,再無其他了。止此事件,兩子並未逾禮。漢代《鹽鐵論》裡有「德之賊」的御史大夫吱喳大叫,什麼「男女不交,孔子見南子,非禮也。」即使南子有「淫行」(朱熹語) ,問題不是見,而是怎麼見。不見,那反而是抱了成見的非禮,是「厭女」的歧視。
不過孔子之見南子,是通過一個同樣名聲不好的人物,由此君引見。那是彌子瑕,是衛靈公的男寵。「斷袖分桃」的典故,說的就是這兩君。到了年老,不再小白臉,靈公愛弛,罷免了他,於是又有「餘桃之罪」的成語。《呂氏春秋‧貴因》云:「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鹽鐵論‧論儒》也云:「孔子適衛,因嬖臣彌子瑕以見衛夫人,子路不說。」
孔子所謂「女子與小人」,此中或有他所指的人物。或有,是不能確定。只能闕如,但我肯定的是,孔子並不仇厭所有女子。
3
《論語》中孔子把女兒嫁給一個囚犯公冶長,因為非其罪(〈公冶長〉5.1),又為兄長的女兒主婚,嫁給南宮适,因為政治清明,他會做官;黑暗,會避免刑戮(〈公冶長〉5.2)。這是他的眼光、分寸。換過來,就不好了,難以向兄長孟皮解釋。此外,孔子好像跟女性無甚緣份,他不可能有女學生。而世傳他出妻(休妻),兒子以至孫兒子思,都出了。三世出妻,這其實是一筆胡塗帳,事見《禮記‧檀弓上》: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孔子四代,兒子孔鯉(伯魚),孫孔伋(子思),曾孫孔白(子上) 。子上之母,即子思之妻。「先君子」,指孔子。這段指出子上的母親去世後,沒有舉行喪禮。門人問子思,何以不使兒子為「出母」辦喪禮。他說只有先君子才做得合情合理。我怎及得上祖父呢。「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答得婉轉,不為,即不再作為;已休,又已改嫁,孔伋當然不再視之為妻;孔白也不視之為母,換言之,親情斷絕,不需守喪。
問題在,此中「出母」一詞最關鍵,究竟是指已休出之母,還是,像近人楊朝明考訂所云:「出母」不等同「出妻」,也不同於「庶母」,而是指「生母」,楊氏並引錢泳《履園叢話》:「出之為言生也,謂生母也。」又說因誤解出母為出妻,一只錯,從而推溯前代出妻。(《齊魯學刊》2009年第2期)《禮記‧檀弓上》另一段云: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唐代的孔穎達云:「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於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禮記正義》) 我們對古人守喪的規矩無疑覺得繁瑣可厭。總得理解一下。「期」是指喪服一年的時間。又有「祥」和「禫」之別。子女守喪,第一年稱「小祥」;第二年「大祥」。「大祥」之後隔一個月為「禫」。禫指守喪期滿,除去孝服,恢復日常。孔穎達從伯魚為母親只服喪一年,仍然在哭喪,就被孔子斥責,從而推論此母已「出」。孔子出妻之說,即始自孔子這位第三十一世孫孔穎達。不過根據《儀禮‧喪服》,母親過世,父親猶在,守一年期就夠了。
孔門果真三代出妻,也屬見怪不怪,因為出妻之條有七,隨時隨地可以把妻休了,見《大戴禮‧本命》: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
婦有七去,卻不見夫有七出。這是另一種同工不同酬。孔子出妻之說,並沒有說明理由。後來子思的門人孟軻,見妻子在房中伸開兩腿踞坐,坐相不好,也要把她休了,卻被孟母訓止。(見《列女傳》及《韓詩外傳》)。
4
孔子不是仇厭所有女子,雖然他離家十四年,沒有另娶,只誤傳與南子的緋聞。離家時已五十五歲,也許不便帶著老妻,要是的確索性把他休了,並非不可理解。我說「也許」罷了。回家前,老妻已先走了。他肯定並不仇女,首先,佛洛依德之流倒會猜想:他三歲喪父,自小和單親媽媽一起,不可能說母親顏徵在近之遜遠之怨的「難養」。媽媽含苦茹辛,逃避閒言惡語,從陬邑避地到曲阜。他充其量會戀母,又或者戀父。
其次,他在《論語》提及《詩經》的〈周南〉、〈召南〉,對兒子伯魚說:要是不讀〈周南〉、〈召南〉,就好像面壁而立。(見〈陽貨〉17.0) 面壁,即寸步難行。兩南不乏稱讚女子勞苦工作,申訴她們被不公平對待之作。有興趣的男士,自己翻看。《詩經》三百,豈有仇女詩?
他也有稱讚女子的時候。在《國語‧魯語》,以及《禮記‧檀弓下》,他盛讚一位女子,她的名字是敬姜。《孔子家語‧曲禮子夏問》記得最詳細:
公父文伯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人之欲供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揮涕,無拊膺,無哀容,無加服,有降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孔子聞之,曰:「女智無若婦,男智莫若夫。公文氏之婦,智矣。剖情損禮,欲以明其子為令德也。」
敬姜的兒子死了,兒子的大小老婆一路啼哭失聲。母親的敬姜對她們告誡一番,在外邊喜歡結交朋友的,士人願意為他死;貪圖女色的,婦女願意為他死。我可不喜歡他以好色而傳播醜聞。你們願意留下來供奉祖先的話,那麼就請遵行五個「不要」:不要憂傷得憔悴,不要痛哭,不要拍胸,不要哀傷著苦臉,不要延長服喪期,按禮制降一等服喪,依從禮訓安靜,那就是彰顯我的兒子了。
孔子讚她,也讚得特別,讚的可不是未婚或失婚的人:女子的才能沒有比得上已婚的婦女,男子的才能也沒有及得上已做丈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