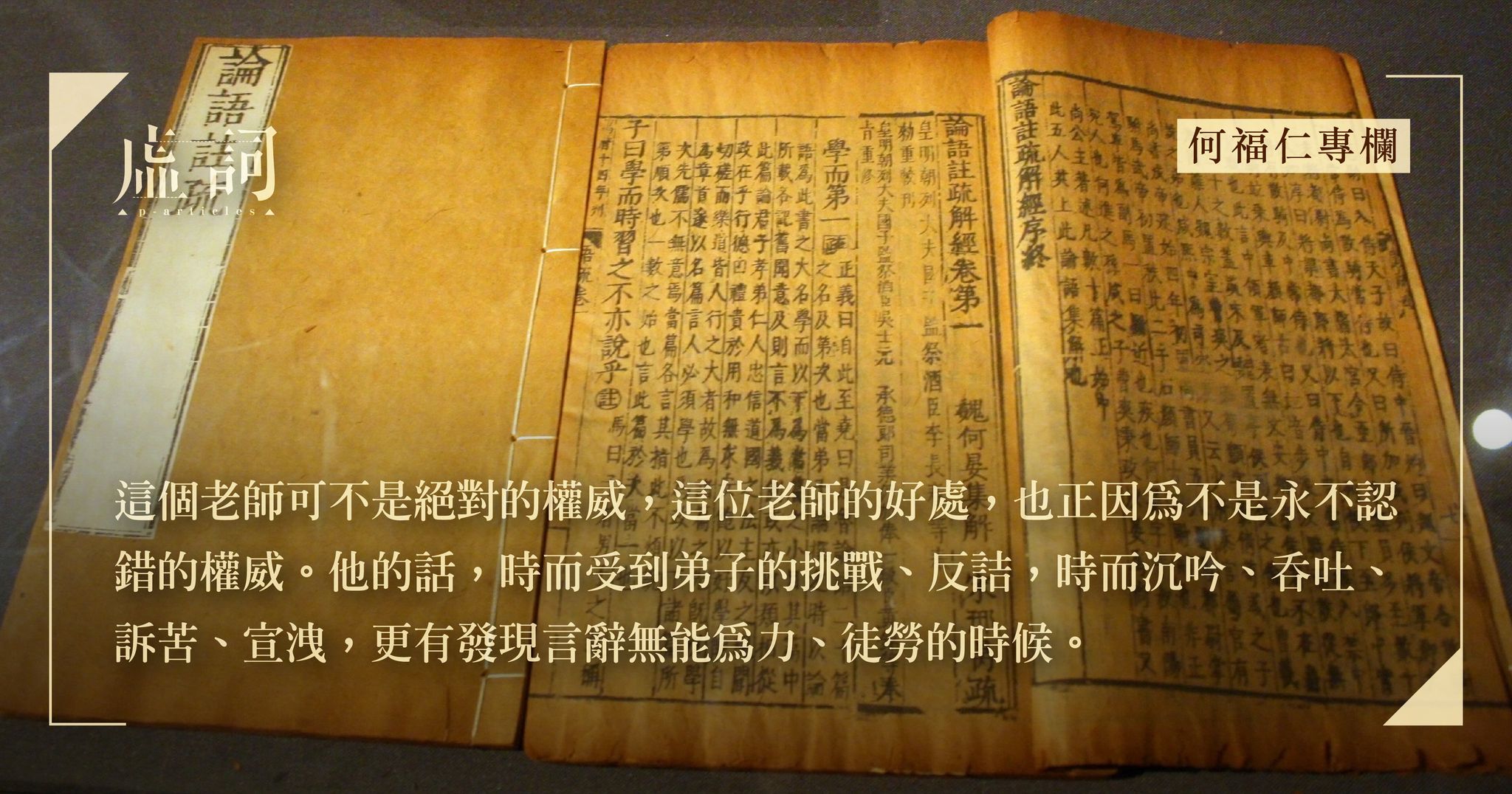【何福仁專欄:時宜篇】眾聲複調的《論語》
(按:這是「時宜篇」的收結篇,雖然我的《論語》好歹還沒有寫完;文章不易寫,沒有看到的書,我不敢寫,所以需要更多的時間整頓、梳理。感謝編者,尤其是黃思朗兄,一直費神照拂。)
1
《論語》的編撰顯然沒有考慮語境的問題,或者根本不以為語境重要。把孔子的說話從語境割離,當然有問題,《禮記‧檀弓上》有一則著名的案例,有若和曾參討論老師對喪葬的想法,理解不同,需借助另一同學子游提供說話的背景,方得澄清。不過更大的問題是,這種做法背後的思維:把孔子的說話當是單一、權威的獨白。當年的編撰者如此,後世大部份的儒家學者也讀成單一、權威的格言、警語。再而按己意加以闡釋、運用、延伸。
重讀《論語》,我覺得不妨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因為我聽到這位偉人的聲音其實很複雜,喜怒哀樂,什麼情態都有,而不是始終堅定、自信;不是一味高高在上的指令。他有猶疑、徬徨、失望的時候;他是一個不戴面具不用假名的真人。我把二十篇按內容形式表列,分成四類,為了方便,章節照楊伯峻劃分(唯五個重出句不算),容個別有不同的分法,形式分類也可斟酌,但應大體不差:

《論語》中最多的是獨白。不過孔子與弟子或其他人的問答固然是對話,就是只見「子曰」的獨白章節,其實也是對話,因為總有弟子在場,有人聆聽,有人記得,甚或根本有人在發問。不然從何得知?何以有此記錄?
換言之,「獨白」也有隱含說話的對象。然則《論語》中,對話加上獨白,約共佔八成。其他如他人或弟子的說話,也不乏對話;不含說話的敘事,只佔一成;兩者合共也不過兩成。此見對話正是《論語》的精粹。今人讀《論語》,意義之一,我以為即是其中的「對話意識」,這也是儒學文化對這紛爭、仁智互見的世界的貢獻。孔子當時,幸或不幸,不像孟子,並沒有論敵可言。有趣的是,當面逗引以至挑剔他的,只有他自己的學生。《孔子家語》載孔子指出忠臣的諫言有五種:譎諫、態諫、降諫、直諫、諷諫。他自己則採取婉言規勸的諷諫云云,好像很會說話似的。但《孔子家語》種種長篇大論,顯然經過潤色。在《論語》裡,當孔子向君主提出規勸,多的是直諫。有時,對他不同意的政策,當君主向他詢問,他會沉默不答,又或者說自己不懂,沒有學過(〈衞靈公〉15.1)。我甚至覺得他不是一個喜歡論辯的人,像孟子。孟子在《孟子•公孫丑》說孔子自稱不擅言辭(「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容或是自謙,但對說話,他一再主張慎言、少言,他說過「君子欲訥於言」(〈里仁〉4.24 )、「惡夫佞者」(〈先進〉11.24)等等。所謂孔門四科,包括「言語」,應是指外交辭令。而這四科,並非孔子親授,前人(程子)已指出這是世俗之論。
在《論語》的對話裡,孔子這個人,顯然是一個爽直、真誠,往往喜怒形於色的讀書人。一如許多寫作人執筆爲文的狀態,他通過對話來表達自己的思考,通過對話來整理、深化自己的思考。
照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的對話理論,對話是「同意或反對關係、肯定和補充關係、問和答關係。」(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這是《論語》裡孔子和其他人的基本關係。對話的前提條件是互相尊重、平等交流;還不止此,用巴赫金的說法是: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此即巴氏所強調的「對話性」。他認爲小說最能呈現這種「對話性」,其中又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爲典型,他的小說人物,都是思辨型。這是陀氏最大的發現。孔子當然是思辨型人物,卻並非虛構,《論語》更不是小說,不可能盡合巴赫金的理論,但閱讀以對話爲主的《論語》,是否可以從巴赫金的理論得到助益?《論語》是否也有這種對話性呢?在現今多元化,追求平等對話的社會,如果再從單一、封閉、獨白式的角度去讀《論語》,意義不大。這是我重新思考的問題。翻開《論語》,我想追問:今人是否還需要讀經?經者,不易之理。我的答案是:不需要。但如果不當是經,《論語》從來就不是經,即使在朱熹時代也不是五經之外的第六經,那麼倒不妨讀讀,並且細讀。
孔子的說話,主要的對象是弟子,其次是向他請益的貴族、諸侯的君主,說話的姿態,注定是訓誨式、點撥式的;他的身份是人師。別忘了,這是二千五百年前,他是第一個打破貴族的壟斷,開始私人傳授知識的老師。他並不懂得現代的教育理論,但至少在二十世紀之前,世上沒有人比他更懂得並且實踐教育。更難得的是,這個老師可不是絕對的權威,這位老師的好處,也正因爲不是永不認錯的權威。他的話,時而受到弟子的挑戰、反詰,時而沉吟、吞吐、訴苦、宣洩,更有發現言辭無能爲力、徒勞的時候。時而,其實也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小說人物,他自我裡有一個他者,亦此亦彼,跟自己討論、爭辯,以至自我審判,用他的說話是「內自訟」(〈公冶長〉5.27) ,好像跟自己打官司,輸的是自己。又例如:
觚不觚?觚哉!觚哉!(〈雍也〉6.25)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17.11)
這些,難道是明斷而故問?巴赫金指出有一種「格言式思維」,那是以格言、箴語形態發表的話語,雖脫離了語境和人聲,仍能以無人稱形式保持原意,成為普遍的意義。《論語》有不少這類由弟子紀錄的格言,無庸置疑,我們總可以從傑出的哲學家、成功人士找到這類話語;從特殊事件尋找普遍的意義,哲學家最優爲之。成為格言,則斷章可以取義,好處和壞處是一事的兩面。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孩童要取他的茴豆,他氣急敗壞,說:「多乎哉?不多也。」他說自己茴豆的數量已經不多了。重要關頭還引經據典,食古不化,然而這與講「多能鄙事」的孔子根本無關(〈子罕〉9.6),而且意思相反。
2
孔子有些說話,的確不能放諸四海,例如: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先進〉11.8)
其情可感,但絕對不是什麼警語,可以為天下法。芸芸弟子,只有最好學、最能安貧樂道的顏淵才足以令孔子感同身受,死的不啻是他自己,這是特殊的對象,特殊的境遇。朱熹注云:「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變成孔子哀悼的不是一個曾經活生生的人,而是他自己的道;顏淵成為傳道的客體。孔子說過「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4.8),如是則道未傳,還不可死。這句話摒棄人情,就失去感染力。李零認為《論語》寫顏回寫得最差,子路最好(《去聖乃得真孔子》)。子路當然寫得好,但整本《論語》,我最受感動的,正是〈先進〉裡孔子對顏回生前死後的說話、應答,有幽默感,有難言,有反覆,厚葬而引起的問題尤其珍貴,說明弟子並不一定以老師的話說了算。《論語》無一語認定顏回接班傳道,只強調他好學,而視之如親子。《論語》中,顏回出現二十次;子路多了一倍,是四十次。然而孔子跟子路的對答,因為人物性格單一,有沖口而出的反詰,但沒有幽默感,到最後仍回到老師的訓誨去。
孔子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另一弟子司馬牛病重,孔子重複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6.9) 那是另一種難過的表達。因為具體、深刻、溫情,顯然無意成為抽象的哲理。終年以至一生都是一副人之患的臉孔,了無人氣,其實不僅可厭,甚且可怕。下面我略舉孔子的一些說話,表現出各種複雜、不同的情態,以見《論語》裡他的聲音,豈止劉向《別錄》簡化成所謂「善言」,或者朱熹所引楊時所云的「微言」,又或者孔子自己所提及嚴肅正氣的「法語之言」 (〈子罕〉9.24),我槪括區別的用辭,未必最恰當,但無損話語內容的多元異質:
1 表白解釋之言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雍也〉6.28)
2 有苦無路訴之言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11.10)
3 虛與委蛇之言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途。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陽貨〉17.1)
4 矛盾之言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執,其何以行之哉?」(〈爲政〉2.22)
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子路〉13.20)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衛靈公〉15.37)
5 戲言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陽貨〉17.4)
6 失言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述而〉7.31)
7 反復調停之言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先進〉11.14)
8 叩鐘識音之言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路〉13.3)
9 否定語言之言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17.19)
10 教學相長之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八佾〉3.8)
11 正言若反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先進〉11. 4)
12 自我修正之言
宰予畫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公冶長〉5.10)
13 相譏而實相親之言
子畏於匡,顏淵後。
子曰:「吾以汝為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先進〉11.22)
14 肢體代言
或問褅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八佾〉3.11)
15 推搪否定之言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15.1)
16 各是其是之言
一、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 13.18)
二、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
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
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烏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微子〉18.6)
三、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18.7)
四、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微子〉18.8)
上述「叩鐘識音」取《世說新語‧言語》龐士元訪司馬德操事例。其中各是其是之言,最符合巴赫金的所謂「對話性」,又以第三組最可注意,因為那明顯是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他對學生宰我提出的三年之喪,說「汝安則為之」,事後還會對其他學生批評宰我「不仁」,表達自己的想法。對葉地的行政長官,則只說我那裡的所謂「直」跟你的不同。「異於是」云云,顯然是孔子的慣用語。對象一為弟子,一為長官,別有分寸。
對長沮、桀溺、丈人三位緣慳的隱士則表現對不同道之人的尊重,三位對孔子都冷嘲熱諷,其中桀溺還游說子路改轅易轍:洪水滔滔,你可以同什麼人去改革它?不如追隨避世之人。孔子只表達自己有所堅持,做法不同:鳥獸不可以同群,如果天下安寧,我就不會參與改革了。對那位招待子路的丈人,要子路重訪致謝,並解釋自己的行徑,道的不行,早知道了。
他自己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子路〉13.23),再提到好些被冷落而能守節的前輩(「逸民」),或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或言中(符合)倫、行中慮,或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同樣滿懷敬意,不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如此而已。他同時說過:「賢者避世。」(〈憲問〉14.37)拿戰國後諸子的爭鳴,孔子是否太客氣呢?
但孔子真的完全沒有因為挫折而想過避世麼?那念頭那怕是一蹤即逝?而且,他馬上轉移了話題: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5.7)
我讀《論語》感到最大的可惜,不是孔子不能做官,做大官,而是他跟三位「道不同」的隱士並沒有相遇,要透過勇而無文的子路為中介,沒有展開更深入的對話。三位隱士之外,另有一位楚狂接輿,走過孔子時唱歌:算了吧!算了吧!如今的執政者都危乎其危!孔子要跟他說話,他已跑了。(〈微子〉18.5)就是長沮、桀溺、丈人、楚狂,以至晨門的人、荷簣的人,那些並無一官半職的小百姓、異見者,對他都是一種衝擊,而且擊中他的要害,點出他的不好處,也正是他的好處,《論語》裡要是沒有這些人,從對面、不同的角度說話,──你說得夠多了,也讓我們說說,那麼這個孔子是不完整的。
3
《史記》載孔子適鄭,與弟子走散了,獨自站立在城東門。鄭人見了,對子貢說他這個人腦額像堯,項脖像皋陶,肩膀像子產,腰以下可是比禹短了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轉告孔子,孔子也欣然笑說:樣子,小事,說「像喪家之狗,對了!對了!」神與聖是不會自嘲的,孔子會;況且誰又真見過堯、禹、皐陶等人?當孔子借子路之口對丈人的兒子說:我跟你的不同,這可不是黑格爾式對立統一的辯證法,而是巴赫金式「彼此共存」的對話論;不是一分為二,再合二為一,也不是互換與同化,而是彼此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共時共存。這方面最符合巴赫金的所謂「眾聲複調」(heteroglossia)。
巴赫金認為眾聲複調是文化轉型的現象,他認為從古希臘史詩發展到小說, 是從半父權,孤立、單一的文化,演進到多聲道、平等、互動的多元文化。他從蘇格拉底的對話、羅馬的梅尼普諷刺裡找到對話的源頭。質言之,西方文化是從獨白的大一統,走向分裂、多元、相爭而共存。孔子則置身於不同的文化困境:周王苟延殘喘,他很清楚知道,君權已旁落諸侯,諸侯則旁落家臣,再而由家臣的家臣(陪臣) 手執國家的命運。整個春秋,大小戰事395次,孟子所謂「無義戰」,真是「禮壞樂崩」。文化大轉型、大裂變,這是《論語》的背景。孔子要重建周的文物典章,要挽既倒的狂瀾。
孔子從小吏到司寇,在政治上可以發揮的日子很短,嘗試拆毀貴族權力象徵的「三都」一事碰壁,結果受冷遇,不得已去國。他名滿天下,當時的天下,大家表面上都尊重他,要聽他的意見,到頭來沒有人把意見付諸實踐。而且,盛名之下,謗亦隨之;猜忌同行,文學藝術的圈子從來如此,筆下最多「寬容」的人,背後每每中傷同行,更遑論政治上的對手。當他在齊國,齊景公對他說不能待之以魯君對待季氏的禮數,只能用低於季氏而高於孟氏之禮,然而,「吾老矣,不能用也。」(〈微子〉18.3)這算是比較坦率的交代。連周公似乎也放棄了他,久矣不入夢中。說他「知其不可而為之」(〈憲問〉14.39),原來是一個守城門的人,朱熹引宋另一理學家胡寅的話,以為這話是譏諷孔子,「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這是凡事以理度人,豈知守城人其實是孔子的知音,一語點出當世儒者「知命守義」的精神。這也是孔子與其他隱逸者的分別。而晨門難道不是一種為人為己踏實的工作?朱熹自己不是也說過「勿以善小而不為」(《朱熹家訓》)?孔子在逝世之前兩年,在老家跟魯哀君的對話,頗能說明孔子的處境: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憲問〉18.3)
孔子得知齊國陳恆弒君,齋戒沐浴後請哀公出師,但伐齊與否,哀公反而叫這位國老去問季孫、仲孫、孟孫三桓。這是卸責,實情是也由不得他作主,權力在季氏手上。《左傳》哀公十四年,可參看:
甲午,齊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
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
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這段對話特別的是,孔子分析了勝算。孔子一直拒絕談論武事。昏庸的衛靈公問過這種問題,他答以「未之學也」,下文:「明日遂行。」(〈衛靈公〉18.1) 魯君久矣被季氏架空,只差沒有被弒。哀公的祖父昭公被逐,死在異鄕。哀公自己呢,十多年後同樣被三桓放逐,孔子雖不及見,何嘗不心知肚明?姑且盡一己言責而已。
然則孔子的發言,只是身處邊緣,是一種沒有實力的「空言」;無勢無權,他更說不上維護當權,他也從沒有天真地以為一言而音定。
4
孔子出仕,嚴格而言,其直系上司不是魯君,而是季桓子。夾谷之會,他為魯國贏得名譽、取回國土,《左傳》定公十年云:「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子相。」這個「相」,是指儐相,主持儀禮,並非後世的宰相。他設計「墮三都」,想還政於魯君,多少有無間道的意味,那是置身虎穴的「內爆」。兩大弟子子路和冉求,也先後爲季氏做事。毀三家城牆時,子路即為季氏宰。多年後冉求為季孫徵收田賦,助紂爲虐,孔子罵他「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先進〉11.16)老人家憤激異常,翻《左傳》、《國語》,原來事出有因。兩書所記略有不同,意思則一。《左傳》載季孫事前曾派冉求詢問孔子的意見。孔子先是說自己不懂,求問再三,才表示這樣做是貪得無厭,並不合禮。《左傳》寫:「弗聽」,主意其實已定。可見孔子始終處於邊陲的位置,從未真正進入權力核心。而這也正是孔子言說尷尬、微妙之處,用巴赫金的說法是:「在表述中,向心與離心兩種力量互相交錯」。
唐君毅講「人學」時曾提出語言裡有一種「啓發語言」,牟宗三說得更清楚, 那是科學語言、文學語言之外的第三種語言(heuristic language),儒家、道家講的道理,是理性,不是文學的情感語言,可又不是邏輯實證論者那種講法(《中國哲學十九講》。孔子並不下界定。《論語》裡,孔子講得最多的仁,那是環繞仁的各種角度,去接近,去領會。講得最好的,我以為還是回到自我的本體去:「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7.30)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12.1) 這是《莊子‧天下》篇所言「內聖」的最好註腳。今人或者厭惡這個「聖」字,古人可並非這樣理解。仁,是自我主宰,不假外求的。其後孟子再加發揮,乃成性善說,人之行善,實本性的發揚,不為名與利、不為天堂與贖罪,不為什麼。而性善,只是清晨的「微明」,或者「夜氣」,必須加以鞏固、培養、光大;否則就受後天惡劣環境所蔽而變壞。這在中西方倫理哲學裡獨樹一幟。
然而,行仁要通過待人接物方得以證立,這個自我要經過與他我交往、應答才完滿。「仁」,是「親也,從人,從二。」(《說文解字》)處理的是人與人對等的關係,這個關係,不是主客二元的「我與他」,而是「我與你」,互爲主體。我你在相輔共存的對話關係裡,互補、衝擊。猶太神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 提出「I-Thou」的關係,這是相對於「 I-It」而言。後者是一種視其他萬事萬物俱為我所用的「他者」;前者則並不以其他萬事萬物為客體,而視同獨立自主,跟自己一樣的個體。不過,布伯是神學家,他眼中的「你」,是上帝,我和你的關係即是人與神的關係,這種關係,在他筆下曖昧而神秘。梁漱溟則指出:儒家的精神是「互以對方為重」(《論中國傳統文化》)。
從這個角度看,無論形式上,以至思想形態上,把孔子的話語解讀成獨白型的金科玉律,既非實然,也非應然。漢朝時,《論語》或稱「記」、或稱「傳」,未入學官(貴族大學),但已備受推崇,是學子必讀之書,逐漸成為經典,孔子成為聖人。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述而〉7.34)又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而〉7.26)可沒有人把他的話當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先進〉11.10)庶幾可以表現哲人的寂寞。
在聖化的過程中,對話變成獨白,變成單一、封閉的真理。話語成為權威, 於是也產生另一種闡析權威的權威,傳統讀書人必須通過這些權威,才能親近權威的孔子。孔子變成了被塑造、被運用、受膜拜,又或者被打倒的客體。
孔子的道理,如仁,如禮,自有普遍的價值,也樂見其得以普遍實踐,但其站足點,是具體的、歷史的人生;它是獨特的,而不是抽象的思維。放眼世界,儒學要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有所貢獻,則正是這種獨特性,而不是普遍適用,越講越空洞的道理。入與人,地方與地方,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話尤其如此。你不能沒有自己的個性,可又不能不尊重別人的個性。單一、同流,泯除差異,這是自言自語。
唯有把《論語》讀作對話,則言說是流動的,在話語交流裡互動。這種話語,時髦地說,是文本(text)。把前因後果抹去,成為普世金句,以為自身具足,就變成固定了的作品(work),令活動中止,那是抽刀斷水。文本呢,並未獨立完成,必須聯繫、對應其他的話語。換言之,它有一種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它是活水,與其他匯流、撞擊,產生水花。當北宋的富弼表示對經典難以「貫徹曉了」,如果貫徹曉了是指要回到經典產生的時代去,不免是一種迷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它去而復返,卻也恆在流逝之中。無論昔日的權威如何懂得水性,他們看見的,已不可能是當年孔子所目睹同一的流水。後人聽到的,也只是他許多許多年前喟然而歎的迴響,而渾忘了我們看到水中孔子的倒映,似幻似真,亦幻亦真,那其實是今與古微妙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