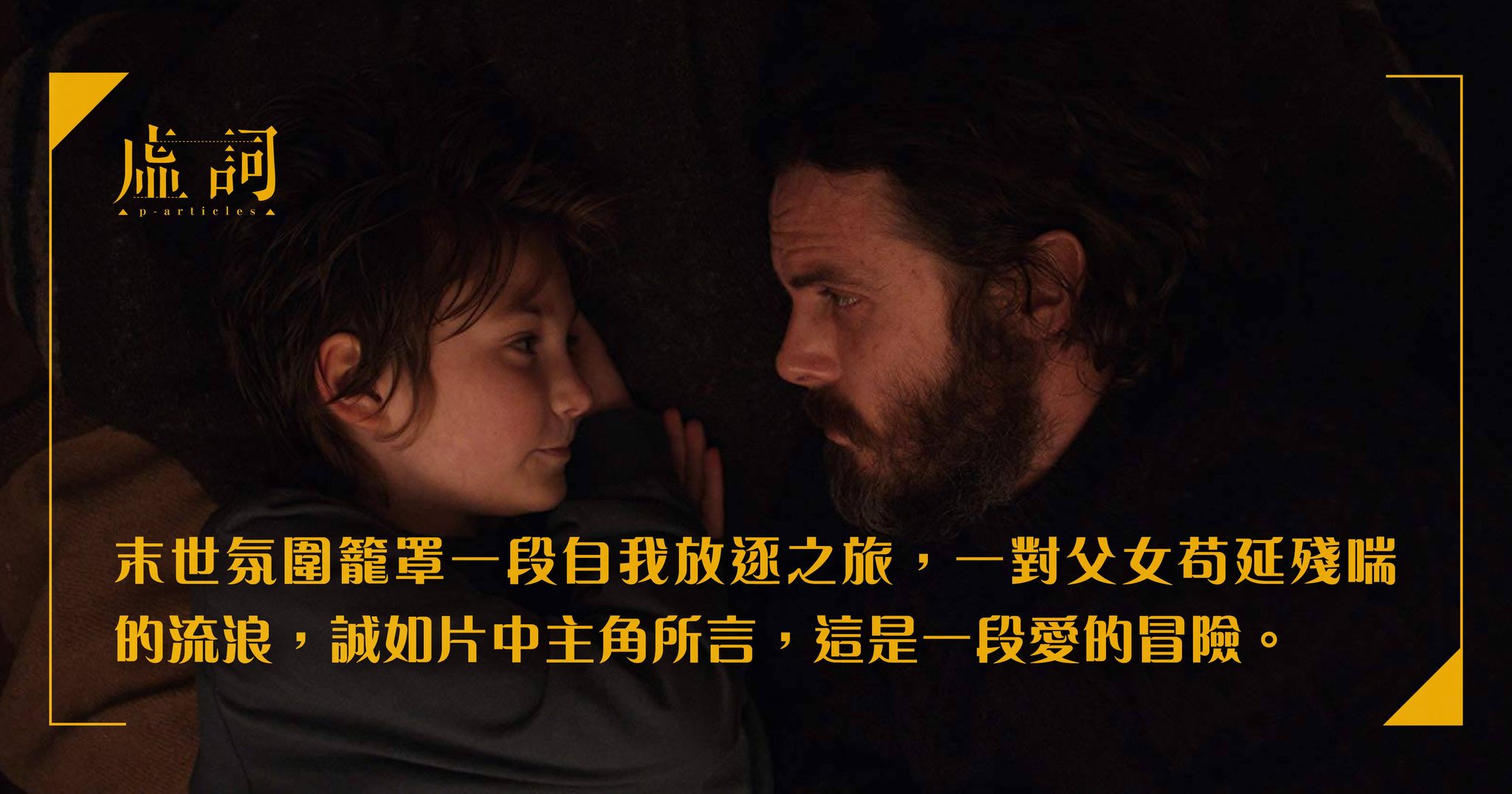鬼魅怪奇託深情———讀張少波《當隔世的繩斷了》
書評 | by 洪慧 | 2020-09-10
1997年,黃燦然編有《從本土出發香港青年詩人十五家》。他在序文中便指出,張少波多有「回望神州」之作。「張少波很多詩都是遊記,尤其是大陸遊記:對一個龐大而陌生的祖國的好奇,對生活其中的人民(他的陌生的同胞)的感觸,在某些情況下是懷著一種同情──也是少年人的家國情懷。」 黃燦然之說固然妥當,但這裡亦可以稍作補充。張少波也不是一味祖國山河壯闊。譬如〈遊北京大學被拒〉的政治取態已是很好的反証。再如〈吐魯番漢卒乾屍〉亦與一般庸俗左派香港詩人書寫祖國的角度大有不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