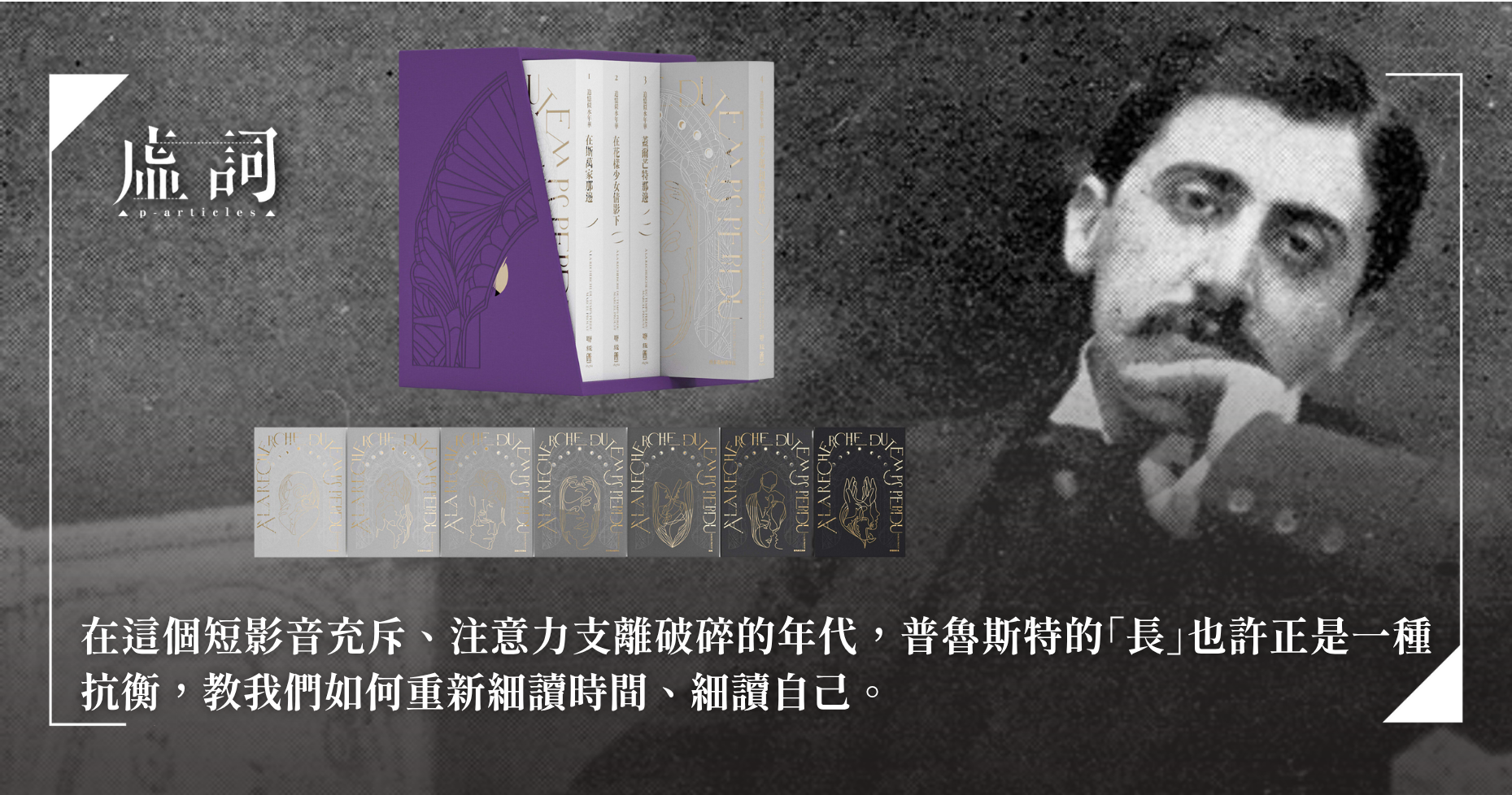【新書】《追憶似水年華》林德祐導讀——〈無眠者的一千零一夜:普魯斯特如何追憶似水年華?〉
書序 | by 林德祐 | 2025-11-17
法國十七世紀道德箴言家拉侯希福可(La Rochefoucauld)曾說:「真正的愛情就像鬼魂一樣,眾人談論,然而真正見過者,少矣!」他又說:「太陽與死亡都無法直視。」這兩段箴言都令人聯想起普魯斯特:眾人皆能繪聲繪影道出瑪德蓮糕點與茶杯裡的風暴,但讀過《追憶似水年華》者少矣,彷彿這套經典也名列無法直視之行列。是因為「生命太短,普魯斯特太長」?然而,在這個短影音充斥、注意力支離破碎的年代,普魯斯特的「長」也許正是一種抗衡,教我們如何重新細讀時間、細讀自己。
讀者若能跨越「普魯斯特太長」的魔咒,他必然能夠發現,這幾千頁的《追憶似水年華》足以改變一個人的思考,為生命傾注智慧的光彩、良善的特質、幽默的精神、超脫一切的豁達。心思細膩的讀者必然發現,這不僅是一部小說,更是普魯斯特打造的一座感受之機器,引導他以不同層次窺看這個世界的色彩、空間、聲音與情感。透過書中那上千位姿態各異的虛構人物,讀者將學會哭、學會笑、學會質疑和思考,這些人物雖然都出自一人之筆,卻各有靈魂,無法被混為一談。讀者可以在繁複的人際交流中窺見虛榮、愚昧、瘋狂、庸俗、投機和嫉妒等人性百態,也因而確認──即便我們身處一個或許已被神遺忘的時代,文學依然是人類通往超越的形式。
這也說明了,儘管世界不斷變動,普魯斯特卻在全球幾乎獲得一致的推崇。他彷彿成為某種宗教,擁有來自各地的忠實信徒。這些信徒之間甚至還能細分出不同的「教派」,各有詮釋與偏好;但儘管立場分歧,他們至少有一項共識:普魯斯特是當代最靈敏的「地震儀」,能偵測性別議題的強度、探測社會變遷的幅度,並測繪人類存在困境的深度。與他比肩的作家/作品寥寥無幾,也許只有莎士比亞、巴爾札克,或《一千零一夜》。
這位作家,在一個世紀前默默地開始發表他那綿延不絕的鉅作,到了二十一世紀,他早已召喚來自世界各地的信徒,吸引了無數熱情的讀者,以破解羅塞塔石碑般的專注與執著,解讀他的手稿。如今普魯斯特聲名遠播,影響力遍及全球,但成功絕非偶然,能衡量這場創作歷程是何等漫長的堅持與毅力的,或許只有普魯斯特自己……
◆寫作規劃
一開始,普魯斯特在眾人眼中是個怪異分子,特異獨行。他恆常失眠,天生怕冷,穿著古怪,文友笑他裹著一層又一層的毛皮大衣,看起來像洋蔥。除了打扮奇特,普魯斯特還很擅長逢迎恭維。他身段柔軟,聲音細膩,不惜扭曲自己真正意圖打進上流社交圈,讓《費加洛報》接受他那些專欄文章。社交圈對他的觀感就是一位異想天開的花花公子。然而有誰料想到?這位穿梭社交圈,個性游移不定的奇特分子,日後將徹底顛覆現代小說藝術的形式。
事實上,普魯斯特的一切所作所為,無意間為他自己建立起一套有利於創作的生活規畫。首先,他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廣泛汲取素材──從高級妓院到騎師俱樂部,從貧民區與娼館到外省鄉下,從貴族沙龍到金融圈,從藝術家工作室、音樂會、中產階級家庭,一直到諾曼第的度假勝地。他彷彿以自身為探針,深入社會各階層的紋理。如果我們要為普魯斯特的人生劃分階段,或許可以稱這段時期為他的「輕浮時期」──在繁華中觀察,在遊歷中記錄。接下來,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年間,他逐漸進入自我禁閉的時期,幾乎完全隱居於自己的房間。他開始梳理這段「輕浮歲月」中累積的大量素材,並將之轉化為創作的原礦。此時的他,過著極為嚴謹的生活:靠藥物與療法紓解慢性病痛,必須服用安眠藥入睡,而一旦醒來,便立刻投入寫作。他的作息顛倒,晝伏夜出,唯一陪伴他的是一位性情純樸的女管家──賽萊斯特.阿爾巴雷(Céleste Albaret)。這位天真質樸的女子甚至一度不知道拿破崙和波拿巴其實是同一個人。
作家經常在生活與創作之間徘徊,究竟要當一個投入社會大膽開創,把人生當作一幅壁畫經營的作家?還是要像福樓拜那樣以隱士、苦行僧之姿投入創作?但普魯斯特似乎在兩者之間找到平衡。他穿梭在社交圈,先是四處收集,然後創作;先是觀察,接著以文字再生活一遍;先是生活,接著再大量書寫。他憑直覺知道,過去的時光會成為日後最大的財富,為他的創作保留許多驚喜。他睿智的地方在於,在出發「追憶」之前,已經積累了大量的失落時光,待他重現。他清楚知道,在追憶似水年華之前,首先必須撿拾這些散落在暗夜中的失落時光。
話雖如此,如果認為普魯斯特早已擬定寫作計畫,刻意每日下午五點出門,與上流社會交際,只為等待時機成熟後開始建構他的「大教堂」,這樣的看法並不正確。這位文青、記者、沉迷於上流社會的花花公子,在著手長篇巨作之前,早已持續投入寫作。他出版過短篇集《歡樂與時光》(Les Plaisirs et les jours),創作了許多細緻傳神的仿作,亦曾翻譯英國藝評家魯斯金(John Ruskin)的作品,並撰寫多篇文章、一本未竟小說《尚.桑德伊》(Jean Santeuil),以及一篇後來編為《駁聖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的散刊文章。
◆氣喘與長句子書寫
普魯斯特自幼氣喘,飽受胸悶之苦。雖然文學史上不乏氣喘作家,但他或許是最能揭示「呼吸匱乏」與「情感匱乏」之間微妙關係的人。不須閱讀佛洛伊德,他早已察覺自己的氣喘,其實是一種向媽媽「討拍」的方式,用來檢驗媽媽對他的偏愛,間接索取晚安之吻。總之,氣喘主導了他的生活,同時也影響了他許多癖好。有趣的是,普魯斯特的氣喘似乎與他的書寫風格密切相關。他呼吸困難,卻經營出篇幅遼闊的文字,只要數數小說中頻繁出現的「但是」(mais)、「就像」(comme)或「可能是……也有可能是」(soit... soit...)等連接詞,就能發現他那些長句子像是一個喘不過氣的人,渴望大口的呼吸;又像快溺水的人拚命游向遙不可及的岸邊,彷彿普魯斯特透過長句子寄託了肺部缺乏的氣息與寬廣。相對地,那些肺活量佳的作家,如海明威、莫泊桑、斯湯達爾則偏愛寫短句。
氣喘使普魯斯特對周遭環境變得格外敏感,尤其是空間的感知,形成他獨特的「呼吸地理學」。寫給友人的信中不乏這種病理式的提問:「蒙梭公園周圍的氣喘患者比聖拉薩車站多嗎?」「里沃利街該怎麼呼吸?」「春天搭火車好嗎?」這種對空間的細膩感受深刻影響了他對世界的觀察。
事實上,氣喘拓展了普魯斯特對外界的注意力,讓他特別敏銳於香水、廚房的味道,甚至能分辨灰塵濃度與空氣品質。從這個角度看,氣喘成了他的繆斯,一個感官的培養皿,使他的小說書寫更加細膩。普魯斯特的父親和弟弟都是醫師,他自己也因病閱讀了大量關於支氣管和花粉的書籍,甚至不禁思考,氣喘是否反而拯救了他,免於遭受其他更致命卻無益的病痛折磨。
◆哀悼與解放
普魯斯特真正投入創作,應追溯至一九○八年。當時,他的母親珍妮.維爾(Jeanne Weil)去世已三年。對這位與母親情感深厚的兒子而言,哀悼是一場痛徹心扉的試煉,他甚至曾動過自殺的念頭。但他很快振作,因為他知道,一旦死去,「媽媽」的記憶也將隨之消逝。
然而,這場喪母之痛同時也是一次解放。普魯斯特終於得以言說一切,包含那始終難以啟齒的祕密──他的同性戀傾向。他開始築構那座名為《追憶似水年華》的「大教堂」,一磚一瓦皆來自記憶:童年、瑪德蓮、晚安之吻、性倒錯、嫉妒、幻滅、時間的重現……這些主題早已深植於他的想像之中。唯有經歷失去與哀慟,他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也才能開始書寫。母親之死雖然讓他悲痛難解,卻也成為他創作上最決絕的推力。唯有摯愛的人遠去,我們方能與自己展開最誠實的對話。
而且,與聖伯夫的爭論之中,普魯斯特已經擬出了一個完美的策略。對他而言,藝術家擁有兩個「自我」:第一個是他的「社會自我」,這也是聖伯夫所關注的那一面,另一個則是作為藝術家的自我。這個二分法是有利於他的創作的:普魯斯特可以是一個附庸風雅、追求時髦,攀附上流社會之輩,但這形象對於創作偉大作品的普魯斯特並不影響,甚至可以更加絕對:既然「深層自我」僅僅是為自己而存在,那麼就不必像聖伯夫那樣以偵探之姿去挖掘這個徘徊於罪惡、野心和虛榮之間的「社會自我」。換言之,普魯斯特可以是性倒錯,可以是同性戀,但我們並不特別就此評斷,更不必將同性戀視為主題來理解《追憶似水年華》。
然而,那時的普魯斯特對於他想寫的書,仍只有模糊的概念。長久以來,他一直是一位「沒有作品的作家」,持續在各種可能性之間徘徊:是要寫一部《駁聖伯夫》?還是一篇論述福樓拜或波特萊爾風格的散文?還是,一部小說?但又是哪一種類型的小說?至少對他而言,那種自傳體小說或短篇小說的時代已經過去。他需要創造一種全新的形式,一種既能擺脫象徵主義,也能超越自然主義的形式。他要讓聖日耳曼街區的公爵夫人們明白,這位長年穿梭於沙龍之間、醉心於收集貴族家譜的普魯斯特,並非出於迷戀她們,而只是為了蒐集素材。貴族圈子誤以為他是一位仰慕者、攀附者;但事實上,普魯斯特更像是一位冷靜的特派記者,甚至是一位新世紀的諾亞,正準備將這些即將在洪流中滅絕的物種,一一送上他的文學方舟。
一天,普魯斯特的友人史特勞斯夫人(Mme Straus,蓋爾芒特封君夫人原型之一)送給他四本精裝筆記本,來自當時知名的 Kirby Beard 精品店。這四本筆記本後來成為普魯斯特死後最重要的遺物。史特勞斯夫人鼓勵他持續書寫,雖然她的動機和許多貴婦一樣,是希望普魯斯特創作以她們為原型的詩歌或小說。
筆記本數量逐漸增多,普魯斯特甚至給每本筆記本取了奇特的名字。這些空白筆記本很快被他塗改重寫的文字填滿,頁邊還貼上許多小紙條和延伸的卷紙,攤開來宛如一把手風琴,最長的一本超過一公尺,現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可查 Gallica.fr)。普魯斯特的管家兼祕書負責將這些文字打字整理。就這樣,時間的「大教堂」從層層疊疊的語句中逐漸顯現。普魯斯特原本只打算寫兩卷,卻最終完成了七卷。
◆「我」的書寫
特別的是,普魯斯特以「我」開始寫他的小說。但這個「我」並不是他自己,「我」指的是一位名為「馬塞爾」的敘述者,雖然這個人物有許多特徵都讓人聯想到普魯斯特本人,但他既不是氣喘病患者,也不是性倒錯者。這個虛構人物將貫穿整部小說,並不斷自問是否能成為一位作家。這樣的書寫策略成為後來許多作家的典範:普魯斯特發明了「我」,這個「我」讓他可以暢所欲言,袒露心聲,無所顧慮,這正是寫作遊戲的目的。此外,我們也可以說,與《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不同,《追憶似水年華》是一本快樂結局的小說,因為敘述者最終達成了自己的目的。
其實敘述者只是一面鏡子,隨著小說的進展,映現出所有的事物:沒落的貴族、反猶分子、猶太人、性倒錯者、中產階級、飯店經理、經營妓院的人、外交官、音樂家、畫家、貼身男僕、女同性戀,也包括一些真實人物(那不勒斯的女王、德雷福斯上尉……)。一開始,敘述者睡下,結尾時,他醒來。這段時間內,普魯斯特扮演了《天方夜譚》中不斷講故事以求緩刑的莎赫札德,而時間則是殘酷的蘇丹。普魯斯特用敘述重溫他那一千零一夜般的失眠經歷,創造出如夢似幻、魍魎鬼魅般的人物:夏呂斯、斯萬、奧黛特、艾貝婷、姬貝特、奧莉安、布洛克、法蘭斯娃、聖盧、諾普瓦、哈瑟兒、威圖漢夫婦等。他們構成了一座驚奇動物園,一部非「人間喜劇」,揉合了精緻與殘酷,幽默與悲情,勇於一探究竟的讀者,將變得更深思熟慮,也能更清晰地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出版風波
然而普魯斯特的稿件並非立刻被接受,首先是編輯的問題,他們完全無法理解這份總共七百一十二頁、不分章節,且多次塗抹修改的初稿想表達什麼。奧蘭朵夫出版社的社長安布羅(Alfred Humblot)收到《在斯萬家那邊》(Du côté de chez Swann)的手稿後寫道:「不知是不是我理解出了問題,但我不明白,為何會有人對描述一位先生在床上翻身入睡的三十頁內容感興趣。」另一家出版社法斯凱爾(Fasquelle)也因為同樣的原因撤回了出版提案。沒有人能夠相信,這位社交記者真如他朋友們所說的那樣,天才橫溢。出版社聘請的審閱者實在無法認同這些「四處流竄的句子」,儘管審閱者肯定作者「超凡的智力」,但最終他還是拒絕推薦這部作品。
在所有出版社的誤判之中,最有名的或許是紀德的拒絕。當時紀德是《新法蘭西評論》(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的主編,他因為手稿中一個難以理解的隱喻而否定了這份作品。幾經波折,《在斯萬家那邊》由格拉瑟(Grasset)出版社出版,還是「作者自費」,然而,普魯斯特並未因此氣餒,因為他的目標本是出版,而非立即被廣泛閱讀。後來,事情有了轉圜:紀德感到懊悔,寫了一封道歉信,最終普魯斯特獲得加利瑪(Gallimard)出版社的接受,而該社憑藉《在花樣少女倩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獲得了創社以來第一個龔固爾文學獎。
後來,賈克.里維埃(Jacques Rivière)加入加利瑪,自一九一九年起擔任《新法蘭西評論》主編。里維埃是一位細膩又謹慎的編輯,博學、優雅、低調、充滿機智與靈敏的感受力:他才是普魯斯特最理想的編輯。里維埃真心敬佩普魯斯特,對他的作品給予極高評價。這位當時最傑出的法國期刊編輯成了《追憶似水年華》的重要推手,也陪伴普魯斯特直到他生命最後的時光。
至此,這部唯一重要的作品終於能夠向前推進,銳不可擋。一部開篇的卷宗,然後第二卷,接著是《蓋爾芒特那邊》(Du côté de chez Guermantes)。普魯斯特令巴黎文壇驚豔。這位低調的野心家,寫信遠多於說話的沉默者,臉色蠟黃的氣喘病患,竟能脫穎而出,成為矚目的文學巨匠?很快地,他克服重重障礙,著手建造屬於自己的宏偉「大教堂」。儘管仍處草稿階段,整體輪廓已然清晰:主體矗立,雕像與繁複裝飾漸次浮現。此時的普魯斯特已找到方向,除非死亡,否則無人能將他阻擋。
◆艾貝婷系列
無人能將他阻擋。然而,愛情的突如其來打亂了原本穩定而有節奏的步伐。對普魯斯特而言,愛情雖是反覆思索的主題,卻極少以正面的姿態出現。在他筆下,愛情往往只帶來焦慮與痛苦,是一種缺乏自我價值的情感──只有在失落與匱乏時才會被深切地感受到,而這種感受,往往是出自嫉妒。在《追憶似水年華》中,愛情的論述多半消極:「我們之所以愛上一個人,是因為我們無法不去愛。」普魯斯特對愛情的剖析大致如一:人因幻想走入愛情,因倦怠而悄然離開。然而,在現實中,愛情卻打亂了這部龐大文學機器的精密運轉。製造這場混亂的,是一位名叫阿弗雷德.阿戈斯蒂內利(Alfred Agostinelli)的人。
在普魯斯特眼中,阿弗雷德是一位迷人的男子,機智聰慧,蓄鬍、戴著皮革鴨舌帽,照片中的他身穿飛行員制服、挺胸而立。普魯斯特在卡堡的「海堤」上初見他,立刻被這位身上帶著機械氣味的年輕人吸引。當時飛行的時代初來到,而阿弗雷德正渴望翱翔天際。他不久便進入「先生」的服務,與妻子一同住進奧斯曼大道一○二號。儘管女管家賽萊斯特否認,但根據多位權威傳記作者,阿弗雷德正是《女囚》中艾貝婷的原型。對此,普魯斯特曾說:「一把鎖需要十把鑰匙」──角色從不只對應一人。無論如何,這位「男囚」終究逃離了。他加入昂蒂布的航空俱樂部,最終在戰前墜海身亡。普魯斯特因而陷入絕望。這段生命經驗最終在《追憶似水年華》中轉化為藝術,演變為「艾貝婷系列」的情感核心,在「失落的時光」與「重現的時光」之間悄然發酵、蔓延開來。
如果沒有這場悲劇,普魯斯特或許就會有時間完成他的作品。但如果沒有這場悲劇,我們或許就讀不到這部愛情小說,對任何曾經經歷過心碎的人來說,這是一部必讀之作,小說家莎岡(Françoise Sagan)就推薦所有失戀的讀者應多服用幾帖《消失的艾貝婷》(Albertine disparue),彷彿在普魯斯特的小說中看到了圖書療法的療效。
總之,普魯斯特確實完成他的工作,但遠遠還未結束,他的人物還需要他,他不能將這些人物留在未定的狀態中。到了生命晚期,普魯斯特已是形容枯槁,完全依賴藥物:特瑞諾、巴比妥酸鹽、腎上腺素、鴉片、嗎啡、純咖啡因。為了能夠入睡,為了能夠呼吸,保持清醒,他衰敗的身體對任何藥物已是來者不拒,而他的精神也對過往的回憶來者不拒,必須繼續收集一些已經陷落在過去、越來越不可觸及的回憶,讓過去與現在結合成有意義的片段。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病榻上一番掙扎之後,普魯斯特在黎明時去世。他沒有時間重讀、修改或增補自己的作品(普魯斯特寫作方式通常是事後增添、層層堆砌上去的),他的手稿上充斥著「重寫」(à réécrire)、「挪移」(à placer ailleurs)、「調整」(à changer)等寫給自己的指示。最後,是他的弟弟和里維爾耐心的整理之下,才讓普魯斯特的遺稿得以出版,而這個版本也在普魯斯特學者們不斷的努力而持續被修正,成為今日普遍譯者所依據的原文。聯經新譯本所依據的法文版是收錄在加利瑪的Folio叢書,該叢書依據的就是法國最具權威的書系七星叢書(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編定的版本,註解詳盡,極富參考價值。
這七冊的《追憶似水年華》之中,前面四冊是在作者生前出版,而後面幾冊是作者身後,由專家學者依據手稿進行文本重建而出版的,因此文中依舊充滿許多未定的細節,導致某些內容在不同冊之間產生了矛盾之處,比方說,第四冊曾描寫主角與艾貝婷熱戀時的情節,兩人經常上演難分難捨的送別場景,搭乘車輛往返於巴爾貝克與帕爾鎮之間。然而到了第六冊,主角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卻將目的地寫成了「安卡鎮」而非「帕爾鎮」。這種地點上的不一致,或許反映了記憶的不確定與變異,也可能是普魯斯特有意為之,用以展現回憶與現實之間微妙而模糊的界線。因此,法國的出版社通常會邀請普學專家為文本進行專業的註解,挑出這類細節,聯經新譯本也加入了註解,除了有助於還原普魯斯特創作歷程,也讓讀者得以更清晰地理解文本中的歷史、文化與語言脈絡。
◆普魯斯特星球
如今,普魯斯特星球上住著成千上百個人物,每個人物有著自己的身體、自己的故事和祕密,讀者總能在某個片段中,發現一個與他相似的人物。社會風俗已經改變,社會階級早已發生變化,語言也隨時間而演變,昔日的鄉村物換星移可能變成一座死城,但普魯斯特早已設想過這些變遷與流轉,因為一切如同似水年華終將消逝無蹤。那些人物見證的時代可以遠去,然而普魯斯特留下來的這些文字引領我們重探那個時代,更重要的是,讓我們發現,我們與這座星球的人物並無不同。文學中的一些典型人物是恆久流傳的,莫里哀或巴爾札克筆下的人物永垂不朽:高老頭、吝嗇鬼阿爾巴貢、偽君子達爾杜弗,而普魯斯特也創造了一些永不過時的典型人物,斯萬、夏呂斯、奧黛特等等。這些人型不會隨著時間而衰老:他們逃脫了時間的束縛。
普魯斯特的人物既是寫實產物也是風格產物,而且由於他的人物總是被某種執念所困擾,他們也是精神產物。首先,多年的觀察、紀錄和往來成為普魯斯特塑造這些人物的成分,這些虛構人物自然有真實人物作為原型,就像林布蘭油畫中的哲學家或馬內《奧林匹亞》畫中的裸女,肯定有模特兒為他們擺姿勢。其次,這些人物都是經過風格化的處理,因為他們是透過文學手法再現的,就像畢卡索對人物進行的繪畫處理,透過視角重構賦予了他們全新的立體感,每個面向甚至可以彼此矛盾。這些人物似乎總被某種執念纏繞著,那是因為他們來自潛意識,來自夢境的世界。他們的形象纏繞著我們,就像他們最初糾纏著他們的創造者。我們這個急促匆忙的時代,一切只求即時溝通,與藝術溝通背道而馳,在普魯斯特的世界中,我們找到了一個被遺忘的能力──夢的力量。
正因為這些人物承載著時間的印記,因為他們會變化,因為我們目睹著他們老去而且這種衰老亦令我們感到痛苦,這些人物才得以超脫時間。或者說,正是透過描繪時尚的變易不居,普魯斯特才逃脫了二十世紀許多叱吒風雲但轉眼又消逝的文學潮流。這些小說中的人物隨著時間的積累不斷深入,無論是在語言上還是現實上,世界不斷在變化,他們的形象卻不會消殞磨損。
在普魯斯特過世前,他早期的小說已經被譯成西班牙文與英文。重要的翻譯推手包括英譯者 C. K. Scott Moncrieff,他的《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使普魯斯特進入英語世界的主流視野;以及西班牙文詩人兼學者 Pedro Salinas,他的譯本推動普魯斯特在西語文化圈的流傳。雖然當時已有不少讀者直接閱讀法文原著,但翻譯無疑是衡量作品普及度的重要指標。自一九二七年《追憶似水年華》全卷問世後,各種譯本紛紛湧現,未曾間斷。普魯斯特的作品不再只屬於精通法語、熱愛法國文化的知識菁英,而是邁向全球,成為今日我們所認識的世界級文學巨擘。
如今,在世界各地的書店中,《追憶似水年華》的譯本無所不在。幾乎每個國家的讀者都能以自己的母語閱讀普魯斯特。透過翻譯,普魯斯特的作品跨越語言與文化的疆界,抵達他從未想過的地方。他本人不曾真正掌握任何外語,如今卻被譯成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語言。這樣驚人的傳播與作品地理版圖的擴張,無疑是對一位藝術家最崇高的致敬。
此外,另一個展現其文學地位的現象是:《追憶似水年華》在許多語言中出現了多次重新翻譯的情況。例如,英譯版書名《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最初是由 C. K. Scott Moncrieff 在一九二○年代首次英譯《追憶似水年華》時採用的,靈感來自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第三十首的詩行。隨著學界對普魯斯特原文理解更深入,後來的譯者認為這個標題過於含糊,未能直接反映法文原名的意涵,從一九九○年代開始,新的英譯本逐漸採用更貼近原文意思的標題:In Search of Lost Time。這個譯名更精確地傳達了作品主題,也更容易為現代讀者理解。
以日本為例,普魯斯特作品在日本的翻譯歷史悠久。早在一九二三年,《明星》雜誌以〈看她沉睡〉為題,刊登了《女囚》一書的節錄譯文。一九五五年,由六位學者與作家組成的團隊首次推出《追憶似水年華》的完整日文譯本。此後,這部翻譯工作陸續展開,其中有兩部完整的《追憶似水年華》譯本:一是井上究一郎於一九七三年至一九八八年間完成的版本(另有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修訂版),二是鈴木道彥於一九九六年至二○○一年間完成,並於二○○六至二○○七年間修訂的版本。最近一次的完整翻譯則由吉川一義負責,歷經多年,終於在二○一九年全部問世,而這已是日本第四度翻譯《追憶似水年華》。這些例子都顯示後世對普魯斯特風格的探索從未停歇,對其作品的理解也持續進行。普魯斯特已被奉為經典作家,是每個人一生中反覆閱讀的作者,而且往往是透過不同的語言版本。他的作品不僅跨越時間,也跨越語言與文化疆界,成為無數譯者與讀者一生反覆對話的經典。閱讀普魯斯特、翻譯普魯斯特,是一項永無止境的挑戰,而來自世界各地的譯者,正是這項偉大任務的見證者。
◆閱讀建議
如果要認真閱讀《追憶似水年華》,最好分四次進行。首先,在青春時期,花樣年華時,不妨先讀一些片段,畢竟你對這本書所蘊含的真理只是一種直覺的理解。然後,第二次閱讀,你可以試著更深入閱讀,尤其如果你已經開始意識到文學在生命中的重要性時。隨後,當你初次體驗到愛情帶來的悲傷時,你更能夠在斯萬的嫉妒、夏呂斯的衰老,或是艾貝婷的相關篇章中獲得一種深度和撫慰的力量,那是前兩次閱讀所無法讓你領略的。最後,第四次閱讀,也就是生命晚期的閱讀,將是最具決定性的,因為人到了暮年,像是洗盡鉛華,所有的虛榮或亟欲征服的目標都顯露出真相,人從而獲得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