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評論人,及其邊緣的浪漫——訪張歷君談《文學的外邊》
也斯當年留下「香港的故事,為甚麼這麼難說?」一問;陳冠中則回應其實不太難說,反正「甚麼都沒有發生」,並指出香港有時更可以成為一種方法。在定位的問題上,香港似乎總是曖昧難分。事過境遷,站於當下視點的我們,可以從何回應?張歷君的最新文學評論選集《文學的外邊》便嘗試回應這個問題,他從自身的成長經歷和版圖建構出一個香港,並以香港文學、二十世紀華文文學和世界文學等三個領域的評論文章,展示這二十年來穿針引線編織而成、屬於自己的文學圖景,以及對認同的反思和理解。
我所看見的香港
隨著書名而來的遼闊感,讓我們一再思索文學的可能性,並想起香港文學一直以來的邊緣性,但更核心的問題是:「何謂外邊(outside)?」張歷君解釋,概念是來自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外邊思維》以及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相關討論,他們關於「語言的外在」的思考促成了此書首篇的寫作緣起。2016年的香港文學節,他以講評人身分回應三位學者的研究成果,分別關於法國文學、南來作家和翻譯政治,而他在這三條截然不同的線索中看出隱約的連繫,便以「外邊」的框架展開對話,並進一步結合柄谷行人的「視差視野」(parallax view),重新理解「香港作為方法」的深意。
有趣的是,「外邊」的思考並非僅是顯露於張歷君近年的學術成果,其源頭可回溯至高中時代。因為外邊,我們得以趨近他者,張歷君早年對前衛藝術的追求可說是香港的混雜性的反映。「當時時髦的是現代派和外國作品,最初我是看卡夫卡(Franz Kafka)的,剛好進念二十面體上演《審判卡夫卡之拍案驚奇》,我和朋友因此接觸到前衛劇場。眾所周知,進念的改編作品糅合不少香港元素,這意味著我吸收到的歐陸理論或現代作品都存有香港的脈絡,那些思考也成為此書的關鍵之一,即所謂香港作為方法。」
在進念所結下的因緣,最後交織出一個文藝網絡,漸漸形成一個屬於他的香港。他想起就讀本科時,讀到傅柯與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軼事:兩位法國理論大家素未謀面,卻默默關注對方的著作,並以評論文章回應想像之中的對方,形成一種沉默的友誼,後人將那些文章輯成小書,成為法國理論界的佳話。張歷君暗忖,《文學的外邊》其實也算是一本友誼之書:「我和不同人存在著不同性質和層次的友誼,沒有這些關係的話,是不可能形成這些思考和書寫的。況且,評論原是對既有文本的回應,所以對我來說,我本來無意去定義香港,但香港就是這個層面的友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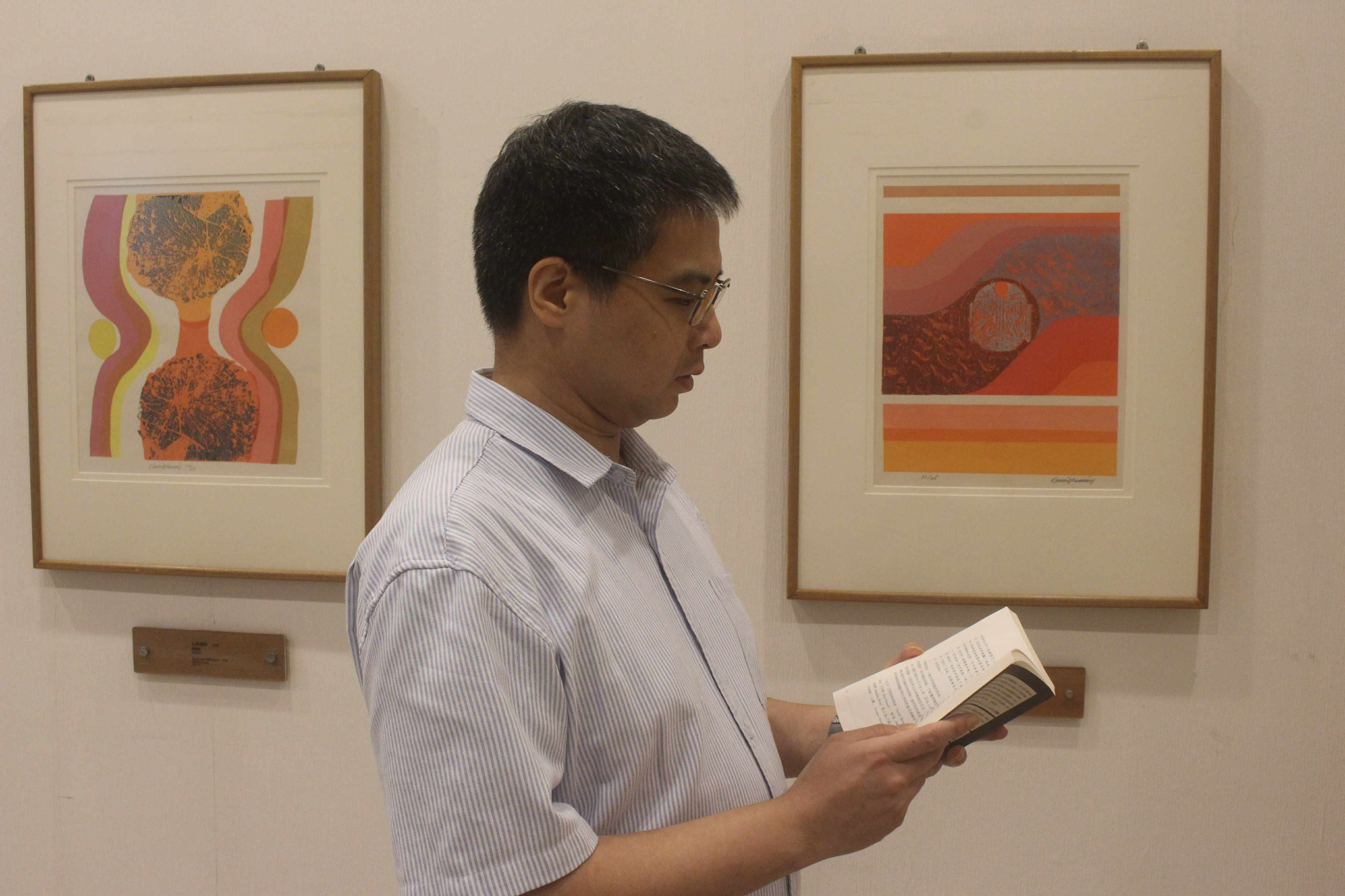
但當我們討論香港,彷彿總要圍繞大環境而談,張歷君卻特別指出:「並非所有內容需要與香港有關。香港,有時是一種從這地生產出來的思考方式,這反而可能更加掌握到何謂香港。以往大眾討論香港,大多談及政治和經濟,或如王德威老師所說,談及電影和娛樂工業,然後才談到文學。但我再提出『香港作為方法』的時候,希望可以將這些論述拉回到文學藝術層面,因為它對香港有著重要的貢獻和價值。」因此,張歷君發現自己一直處理的是「外邊」的主題,便以此為全書的線索,重新組織2002年至2023年的文章。
教曉我畫鬼腳的老師們
除了評論文章,全書特別耀眼的是附錄的筆談〈波德萊爾與我們〉,當中揭示了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對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的研究是如何奠定張歷君的方法論,也令人聯想到「漫遊者」(Flâneur)確實與「外邊」有些幽微的關係。張歷君坦言,張旭東與魏文生所譯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是啟蒙關鍵,「這本書初版於1989年,是當時極具影響力、為數不多的本雅明作品中譯,所以幾乎是必讀的。」波特萊爾提出的「通感」(correspondances)作為象徵主義的起點,天才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 則以「通靈人」(seer)來繼承,這成為張歷君研究香港詩人馬覺的關鍵線索。他解釋道:「蘭波說詩人必須陷入迷狂,這個觀點被德勒茲用以理解何謂外在/外邊,而通靈人其實也隱含著對外邊的思考。語言的內在理應與書寫和說話有關,但他偏偏要求詩人打亂所有感官,從語言裡聽到音樂、看見顏色,這便會觸碰到語言的外在——這正是由波德萊爾的通感延伸而來的。」
不論在張歷君的中大講課上,抑或文章中,不難發現他很強調年份、文學事件的發生及歷史現場,他將這種強調時空座標的歷史思維再次歸根於《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對於本科中文系的人而言,這本書是頗突破性,且令人震驚的,也不像傳統的作家研究。全書先談波希米亞人,卻沒有傳統地先溯源談波希米亞王國以及後來法國的浪蕩藝術家和文人;他首先討論的竟是馬克思(Karl Marx)筆下的『職業密謀家』。學界後來受冷戰意識形態影響,一般會將現代派與左翼對立起來。但本雅明卻在他的波特萊爾(1821-1867)研究論文開端,先大談馬克思(1818-1883)相關的歷史分析。神奇的是我們漸漸會被他說服。」本雅明並沒有在此書系統說明其研究方法,僅是展演一番手藝,張歷君認為這是本雅明獨特之處:「他不走知人論世的方向,也不大談時代的重要脈絡,而是從不同角度和層次慢慢重組作家的寫作脈絡,刷新你對作家的理解,標示著其實作家的背景是很多元的。」
這種不以作家生平為主導的研究方法,其實張歷君在上一本著作《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已有實踐。當時李歐梵老師點出了一道非常細微的問題:瞿秋白留俄期間,還有甚麼其他國家的革命分子同在莫斯科取經?這令他突破了寫作瓶頸期,並開啟了日後對二十世紀文化理論和思想史的跨文化探索;這次《文學的外邊》收錄了二十年來的文學評論,李歐梵則認為他以不同理論將世界名家重新連結,令我們看見「發人所未發的洞見」。對此,張歷君憶起老師十年前在中大開設名為「人文重構」的跨學科課程,開拓了人文學科的可能性,「他認為人文學科的包袱是過於專業化,以致很多研究走入死胡同,就如歷史本來就無法以學科來定義。我常常說歷史現場,當然我們無法完全還原它,但我所強調的是,某些思考、創作、社會活動,甚至文化模式得以出現的條件或語境,其實不可能以學科來界定。只有去連結那些你以為無關係的層面,才能真正理解到它們的出現。」
張歷君形容李歐梵以批評引導思考是傳授著一種技藝,他再憶起本科時跟隨的黃繼持老師經常問學生:「你是否硬套西方理論?中國現代作家與西方理論有何關係?」他表示這些問題雖然很折磨人,「但如果單純套用理論,你便會跳過當中的語境網絡。假設你如畫鬼腳般,把那些理論在歷史意義上的語境連結到研究對象,重新畫出那條連結的線,就等於勾勒出一個複雜的歷史連繫和網絡,而最後從中抽取出來的,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他強調這種思維是由上一輩傳授,與小思老師曾在課上提起的「網狀追蹤法」異曲同工,皆是注重追尋不同作家和思想家背景的關連。
多年的研究,像是一場場偵探遊戲,張歷君認為這正是比較文學研究的魅力,「如上述本雅明的論述路徑,你作為讀者追隨線索,就如推理小說一樣回到案發現場找出蛛絲馬跡,然後重組案發過程。你需要想像,發揮小說家的想像力和直覺,從一些表面上無關的東西找出背後或周邊的隱含關聯,看出一個多層次、不同迴路結合起來的世界——那個重組過程,往往是一種創作過程。」
格格不入與不合時宜
在筆談中,張歷君亦提到香港文學與全球都會的關係,就如波特萊爾和巴黎的關係,詩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感到格格不入,但伴隨而來的疏離感反而讓香港得以成為抒情的題材。他表示身為同代人,處於同樣的氛圍下,文學評論人與詩人共同擁有某些詮釋的可能,亦會感到格格不入。「正如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說的同時代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覺得自己的思考不合時宜,這才是深刻的同代性。近來洛楓的《不合時宜的群像:書寫理論的獨行者》與郭詩詠的《差異與連結》都是從這概念延伸開來,我認為我們這兩三輩的香港文學人都隱隱約約地共同分享著這格格不入的感受。」
格格不入,是本雅明用以區分波特萊爾與「漫遊者」的標籤。張歷君解釋,波特萊爾始終不會將城市化為自己的詩意想像,並最後融入其中,而是敏銳地感受到自己與城市的速度格格不入,在異化的商品世界裡販賣自己的抒情詩而感到憂鬱。他轉而談及當下香港:「沒有人會反對香港是一個商品世界,現時更是一個晚期資本主義時代,即使商品模式已經改變,但其根本的異化狀態始終沒有解決。所以當我們選擇以現代派詩歌去回應時代,這回應就如波特萊爾的狀態,很明確地看見整個商品世界的異化。」
不與時代完全契合的人,才有能力去審視它,那麼在當下的全球與本地語境中,我們如何延伸「香港作為方法」的思考?我們現時又站於怎樣的外邊,看著怎樣的視角?張歷君感嘆:「回想我當初扮文青的九十年代,對比現今的香港,當中的文化模式已有很大轉變。九七前後我們常說混雜性(hybridity),或者香港是一個in-between的狀態等等,這種(非)認同的模式近乎是天經地義的。後來到了當代全球化的成熟階段,香港作為一個全球城市,處於不同民族國家之間,我們對傳統的單一身份認同和二元對立的冷戰意識形態形成了獨特的反思。當下,我們開始不知如何命名這個時代,有人稱新冷戰,有人稱是貿易戰之後,某些單一身份認同和二元對立的思考模式再次佔據主導地位。當我們從當下回望過往,便會發現香港九十年代邊緣混雜的(非)認同模式其實很前衛,並非我們以往想像的那麼主流。」
正是這種深植於香港經驗的格格不入,驅使張歷君選擇移動起來,尋找其他視角來理解它,以柄谷行人的「視差視野」理論打開了一個批判的空間,重新反思香港與他者之間的關係。他表示這正是重提「香港作為方法」的意義所在,發現「香港過往建立起來的思考方法,其實是對當下的一種批判性的警醒。」
評論者未完成的實驗
從博論《瞿秋白與跨文化現代性》的個案研究到評論集《文學的外邊》,張歷君表示兩者的寫作時間有所重疊,是處於並行的狀態,而後者更多是自我批判的過程,「以傅柯的理解而言,真正的批判是反思自己思考和發言的位置和得以成立的條件。」他察覺到格格不入的感受是源於時代的錯位:「從成長過程產生的視角,在不知不覺間變得有點邊緣,很過時。雖說過時,但它隱含著本雅明式的反思——十九世紀的時尚在本雅明的時代全部變得不合時宜,他正是因此重新發掘這段歷史的地層。時尚和過時之間的錯位關係,形成了反思和批評的起點。」
談到新近研究,他重回到魯迅、本雅明與俄國前衛藝術的關係上,延續本科時的興趣,也有意為張東蓀和魯迅的案例出版著作,而這些都是為了回答他最念茲在茲的中國現代性,那條始終被人質疑的問題:「為何用西方文化理論去談中國現代文學?」他把問題再次導向創作人與評論人的區別,「這種跨文化性質的東西,不可從單一地區來討論。評論人的責任是重新將創作者的某些直覺打開,正如本雅明所說的譯者的任務,譯本並非要跟貼原作,而是要把原作帶到另一個境界——純粹語言(pure language)和死後生命(afterlife)。」
確實,本雅明肯定過文學批評是作品死後生命的一種,更指浪漫主義者全心投入於這種工作,又對文學作品的生命比一般人更具洞察力。回想張歷君參與和編校的《我的二十世紀:李歐梵回憶錄》,李氏在後記提到「可惜目前自甘居於邊緣的人也不多了」,然而如《文學的外邊》的書腰「抽象的深情」一句,這又何嘗不是一種邊緣的浪漫。他仍然立足邊緣的本土,但不限於本土地謹守評論人的任務,繼續思考全球語境下的香港是如何得以作為一種方法。

